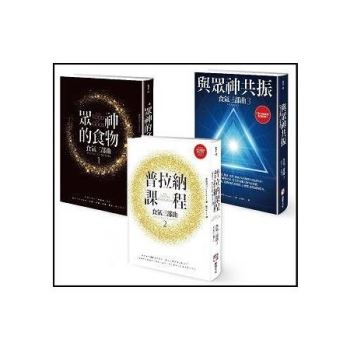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147回直木賞得獎作品
◆日本當代文壇備受期待的才女作家
◆桐野夏生:「不可多得的短篇佳作。」
◆已改編電視劇,由廣末涼子、成海璃子、高梨臨、木村多江、倉科佳奈等重量級女星擔綱演出
所謂「犯罪」,不過是恰好打開了惡意的開關
仁志野町的小偷
律子是我最要好的同學,有天我卻發現她媽媽是鄰居們口耳相傳的小偷……
石蕗南地區的縱火
老家對面的消防隊失火了,猛然想起以前在二樓換衣服時有個消防員跟我四目相接……
美彌谷社區的逃亡者
陽次帶著我一起逃走了,我最後一眼看到的是母親一動也不動的身體……
芹葉大學的夢想與殺人
老師的屍體被發現了。是雄大殺的吧?我能一清二楚地想像,就彷彿命案發生時我也在現場……
君本家的綁票
嬰兒車呢?不好,我一定是把嬰兒車留在店裡面了!咲良,你到底在哪裡?
《沒有鑰匙的夢》是辻村深月產後創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描寫五位生活在地方小城的女性為追尋夢想而誤入歧途的故事。辻村深月素來十分擅長描寫青年在思春期的微妙心情,此番卻將成年女性的所思所想與生活之艱辛刻畫得細緻入微,殊為可貴。
名人推薦語
陳雪、湯舒雯、黃麗群、楊佳嫻、劉梓潔聯名推薦
該獎項入圍作品向來以長篇為主,本屆可謂殺出一部不可多得的短篇佳作。像辻村這樣描寫當今時代,探究慘淡現實的年輕女作家,值得嘉許。──直木獎評審委員小說家桐野夏生
「真想像日劇裡的女主角一樣生活啊」,誰都有過的嚮往,在辻村深月那裡,清一色的女性敘事者共同訴說的,卻仍是作為「配角」的心情。在竊案、縱火案、殺人案、綁架案……的掩護下,一篇篇推理小說的起手式後,就此被牽連進去、不得不做出的種種回應,決定了女性作為一種配角,邊坡滑動式的、沒有選擇餘地的寫實人生。然而在那裡,處處是針灸一樣準確的細節、穿刺著微不可見的孔洞、正祕密地發著熱,隔離問診間袒露的心事那樣,妳我都可能留下的病例──如果能被這樣溫柔而坦誠地執過手、把過脈,紀錄下來,就算不做女主角,好像也沒有什麼關係了吧?或許也就像一場沒有鑰匙的夢,正是唯有配角才看得見的、人生的真相。──作家湯舒雯
五個短篇,五種身為女性的試煉。《沒有鑰匙的夢》書寫少女、大學女生、母親和職業女性,在人生不同境遇中,因為羞恥而終止的信賴,因為自尊而製作的祕密,因為純真魯莽而無法斷捨的親密。對於愛的渴望,使她們背負罪與罰,在惘然中重新看見自己。──詩人楊佳嫻
這五個短篇裡尋常女子的故事,與其說是犯罪與惡意,不如說是生命中的崩落與鬆脫吧。辻村深月精準地抓住了女性生命的破洞與缺口,以現實故事餵養與填補,將小城小事化為深刻的人性切片。──作家、導演劉梓潔


 2014/07/22
2014/07/22 2014/07/19
2014/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