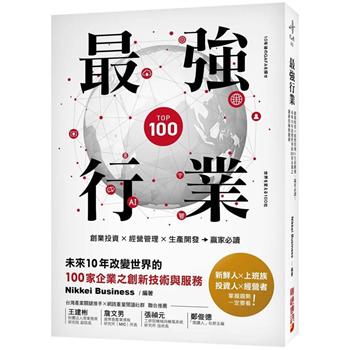從出道開始到《惡人》,耗費十年心血撰寫,
集結吉田修一所有精華的必讀傑作!
東京、大阪、首爾,以及只存在記憶中的城市──
儘管躊躇、擔憂、恐懼、憤怒,那些失落的人們,仍然渴求著希望與平靜。
把心遺落在「那裡」之後,剩下的是否只有……寂寞?
獨自離家到東京的主角「我」,一邊工作,一邊寫著以自己為藍本的真實小說。
某日,由於故鄉的哥哥突然來訪,「我」因而想起年少時曾在廢棄的軍艦島擔任導覽的回憶,也想起了颱風時和哥哥一起朝大海大叫的夜晚……
峭壁般的高牆、密集聳立的高樓廢墟,「除了天空什麼也沒有」,居民離去後便孤伶伶漂流在海中的島嶼,一如逃離故鄉的「我」,除了過去還有著什麼?
零下五度的首爾,來自日本的女子與韓國的男子,隔著同一片玻璃想起了曾經感受過的幸福。
大阪的夜晚街頭,出身同鄉的男子們面臨結婚與否的現實和理想,開始嚮往原本以為再平凡不過的事。
遺忘昔日理想的OL,因為公司的年輕後輩而重拾希望,有了再度凝望藍天的快樂。
深夜,和二十年前的自己一邊散步、一邊對話的男人,在日常風景中找回了年少的過往。
總是會有某個地方,我們無法忘懷;總是會有某個記憶的片段,再次喚醒我們熟悉的感受。從東京、大阪,到首爾或某個不知名的城市,人們總是在尋找心中那個「尚未遺失的角落」、那個能讓自己感到安心平靜的所在。
十則描繪城市x人生風景的失落物語,從異鄉到故鄉,從逃離漠視到流淚面對,吉田以輕盈的文字,鮮明地刻畫出我們內心那最初、最純粹的情感一瞬。
作者簡介:
吉田修一(Yoshida Shuichi)
一九六八年生於日本長崎縣,畢業於法政大學經營學系。一九九七年以《最後的兒子》勇奪第八十四屆文學界新人賞,正式踏入文壇。二○○二年以《同棲生活》榮獲第十五屆山本周五郎賞,並以《公園生活》榮獲第一百二十七屆芥川賞。二○○七年以《惡人》榮獲大佛次郎賞、每日出版文化賞。
譯者簡介:
劉姿君
台大農經系畢業,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課程修畢。曾任職於日商及出版社,現為專職譯者。譯有《樹屋》、《府城的美味時光:台南安閑園的飯桌》等書。
章節試閱
被取消的城市導覽
有一個男人在車站前禁止停放腳踏車的區域,大大方方地剪腳踏車的鎖。要剪斷鐵絲製的鎖,他手上那把老虎鉗似乎太小了。即使如此,他仍然很有耐性,一次又一次不斷地剪。車站前行人很多,居酒屋和電玩中心的霓虹燈也把附近照得很亮,偶爾有行人皺著眉頭瞪著他經過,但沒有任何人停下來。
我會注意他,是因為他的側臉和我哥很像。不過我很快就看清楚他不是哥哥,原本準備直接經過,卻看到他手上的老虎鉗。我假裝找腳踏車,繼續觀察他的行動。時間並不是深夜,他也沒有避人耳目的樣子。假如是小偷,應該不會這麼光明正大吧?看了一陣子,就開始覺得他咬牙使勁剪鐵絲的樣子,像是弄丟了鑰匙而左右為難的腳踏車主人。他沒有備份鑰匙嗎?我一邊替他擔這個不必要的心,一邊繼續專注地看著。男子的背都汗濕了。這時候,啪嘁一聲,鐵絲鎖斷了,就連在旁邊看的我都鬆了一口氣。男子跨上腳踏車,騎車離去。
我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覺得心裡不太舒服。會不會他就是小偷,為了不讓別人注意,才裝作光明正大的樣子?小偷總不可能故意做出小偷的樣子。偽裝,就是因為扮得像真的才叫作偽裝。
一回到房間,剛才還躺在地上的哥哥已不見蹤影,可能又跑到車站前的三溫暖去了。哥哥兩天前突然從我們長崎老家來東京找我,結果他什麼事也不做,就只待在房裡無所事事。我去羽田機場接人,在出境大廳見到幾年不見的哥哥,他還是老樣子,才跟他在一起半天,就再一次見識到他的懶散。那天,正好是當地的廟會,從車站前的人行道開始,一路都是身穿同樣短外褂的男女,跟著小小的神轎走。哥哥想超前,一個看來平日對上司鞠躬哈腰的中年男子,大概是因為一夥人都穿同樣的短外褂壯了膽,大吼:「喂,這位老兄,你趕什麼趕啊!」哥哥只好跟在他們後面走。
「沒想到東京也有廟會啊……」哥哥這麼說。
「全日本到處都有廟會啊。大家穿著同樣的短外褂,一副我最大的樣子……」我回答後,抬頭看神轎。
「幸好穿的是短外褂,要是讓這種人穿上軍服,那還得了。」哥哥愉快地笑著。
廟會這些人在澡堂前向左轉,路總算通暢了,但這下換腳踏車叮鈴鈴地朝我們按鈴。哥哥讓了路,腳踏車不耐煩地超了過去。哥哥笑著說:「我也在肩上裝個鈴好了。」
我先帶哥哥回公寓,傍晚去上班。再回來的時候,已經晚上十點多了。我買了「炸雞塊便當」和啤酒回來當錯過的晚餐,結果無聊到拿香菸燒自己小腿毛的哥哥,居然一臉想吃的樣子看著便當。我沒想到哥哥什麼都沒吃在等,所以只買了一個便當。
「便當你自己去買啦。」
我告訴他便當店的地點,結果他竟然裝大方,說「我又不餓」,卻還是一直盯著我的筷子。
我轉過去背對他。我知道哥哥把坐墊捲起來當枕頭,身子一歪就躺在地上。因為房間很小,懶惰的哥哥身軀顯得異常巨大。
過了一陣子,他又吵著「至少會有個泡麵吧?有吧?吐司也可以……有吧?」開始把小小廚房的櫃子乒乒乓乓地又開又關。
我覺得好煩,最後只好出去買哥哥的便當。
眼看著哥哥這樣自甘墮落,就深深感到媽媽、外婆,當然還有我,過去太寵哥哥了。哥哥不去工作,每天就是晾在老家小屋裡,沒有一個人去問他:你為什麼不工作?有一次,我要外婆去問,外婆說:「那就像問雲朵說:『你為什麼在天上飄?』一樣。」根本不理我。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說明哥哥的懶散,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可以說「反正都要小便……」一整天褲子的拉鍊都不拉。也可以說他是廣場上的一顆球,一顆孤伶伶地掉在廣場上的球,巴不得人家來踢。
我把買來的便當拿給他,大著膽子問:「你打算待多久?」哥哥淡淡一笑,回答:「我會待一陣子哦。一個月,或是半年……」
「不管是幾天還是幾個月,你想待在這裡都沒關係。可是,話先說在前面!你一整天什麼都不做爛在那裡,我可受不了。你來這裡又不工作的話,就馬上回去!而且我會打電話給媽媽……我說,這是個好機會,你在這邊也做點事吧!」
令人驚訝的是,哥哥竟然露出一本正經的樣子。
「說的也是……人的一生,要做什麼嫌太短,什麼都不做卻又嫌太長了。」
聽他說他的歪理時,我好想回他一句:那你去工作一天試試看啊!
「……對了,這是什麼便當?」
「幕之內便當。」
結果我說出口的,也就只有這樣而已。
幾年前,我接到警察的電話,是在我來東京的前一週左右,電話裡說哥哥受傷了,要我立刻趕到市內的醫院。我一時慌張,沒問原因就掛了電話,向正在佛壇前折衣服的外婆報告完,就去看貼在牆上的公車時刻表。我想當時外婆應該認為這是緊急狀況,就開口說「叫計程車吧」。在計程車上,外婆問我哥哥怎麼受傷的?一心以為是車禍的我老實回答:「我沒問……」她後來大概是想起我沒問原因就掛了電話,還有閒工夫去查公車時刻表的樣子,就以為哥哥的傷只是輕傷,從半路上開始,計程車每跳一次表她就嘖一聲。
我們一被帶進病房,外婆立刻收起她小家子氣的態度,因為哥哥的臉腫成了兩倍大。血雖然已經擦乾淨了,但腫起的眼部塗了黃色的消毒水,覆蓋在傷口上的紗布滲血,鼻子插管,額頭和脖子的青筋血管也浮起來,好像有血蛭吸在上面一樣。外婆一個失神,跌坐在鐵椅上。
據出現在病房的警官說,哥哥本來和兩名女子在市內打保齡球,回暗暗的停車場取車時,在那裡被好幾個男人圍毆。那些人躲在車子的暗處埋伏等著我哥。依哥哥的作風,想必是對打出全倒的女子又親又抱、讓人家坐在他膝頭填記分表吧。哥哥露骨的舉動就連我這個弟弟都看不下去了,更何況是外人,而且是一群男人一起打保齡球,看在眼裡肯定不是滋味。
我想哥哥在被那群人包圍的瞬間,一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道了歉。哥哥就是會盡可能息事寧人。
臉腫得那麼厲害,後腦勺又縫了三針,可見得打了很久。臉挨了打,跌倒在地,被又踢又推,被拖行之後又被踹,我簡直可以看見這段期間哥哥任憑宰割、靜待結束的樣子。
兄弟打架也一樣。不管我以多麼不講理的理由打人,哥哥都任我打到我心裡發毛,被他那個樣子嚇到的我,又哭著打他。小孩子打架,當然是哭的那一方輸。
住院第四天,哥哥總算能說話了。他招手要我到床邊坐下,痛苦地按著肚子忍著笑,把我猜想到的事情經過詳細告訴我。
「……然後啊,那時候他們的表情實在太精彩了。一邊打我,臉上卻是吃了酸梅的表情,一副隨時都會哭出來的樣子,拚命打過來。那時候我大概已經滿臉是血了吧,拿著球棒跑過來的那個看到我的臉嚇到,一邊哇哇大叫,一邊打我的背。叫的明明應該是我才對嘛……哈哈!」
哥哥不是逞強不認輸,而是打從心裡笑出來,那樣子和小時候一樣讓我心裡發毛。
哥哥臉紅通通地從車站前的三溫暖回來的時候,我正在重讀自己寫的小說。主角是一個名叫「夏瀨」的二十四歲青年,吉子和吉子的母親也以真名出場。這應該是部結局圓滿的戀愛小說,取名為「夏瀨」的男主角,是個令人氣急敗壞、得意忘形的傢伙。
「不泡個澡,就不算過一天啊。還有水柱按摩池和泡泡池,很舒服哦。」哥哥心情極佳,我不理他,帶著我看了一半的小說正要進廁所,「你剛才去過車站前的腳踏車停車場對不對?」哥哥說。
「你怎麼知道的?」
「我從麥當勞看得到。你去幹嘛?」
我應了聲「沒幹嘛」,進了廁所。廁所門後傳來哥哥討好的聲音:「我今天也可以睡床嗎?」我怒吼般回「可以」,就打開我的稿紙,坐在馬桶上。
……他照常和吉子的母親一起等她回來。快九點的時候,「今天是星期六,再等也不會回來吧,別再拖了,趕快吃一吃吧。」伯母叫看著電視的夏瀨。正要進擺好晚餐的三坪房間時,她說:「你要喝啤酒的話,就從冰箱拿過來。」等他一進廚房,又說:「也順便幫我拿個玻璃杯。」
餐桌上,火鍋咕嘟咕嘟煮開了。
「吉子還不回來嗎?」
夏瀨邊倒啤酒邊問,吉子的母親停下攪動鍋子的筷子,打量他,嘆道:「真是不中用。」
正好是電視開始播《世界不思議發現!》的時間,所以夏瀨打開三坪房的小電視,把鍋裡的雞肉撈到小碟子上。
「今天是馬丘比丘的特集哦。」
「馬丘比……?」
「馬丘比丘。印加帝國的遺跡。等一下這個猜謎節目會……」
「真是的……所以我說你不中用。好好一個年輕人,星期六晚上竟然跑來這裡看猜謎節目,還看得很高興。」
伯母說完,往自己的杯裡倒啤酒。
「還好啊,沒來這裡我也是在自己住的地方看……」
「所以重點不在那裡呀,我說的是……真是的,既然是男孩子,就要像個男孩子,堅持到底。為什麼放吉子到處去玩?」
「我們又沒有在一起……」
「所以奇怪就是奇怪在這裡呀!」
伯母照例發完牢騷,說著「味道有點淡,加點這個吧」,把醬油瓶遞給夏瀨,看他筷子只要稍有停頓,就夾東夾西,把蔥、白菜丟進他的盤子裡。
鍋裡的東西都吃得差不多的時候,連黑柳徹子都答錯的一題關於古代飲食的問題,夏瀨猜對了。伯母大肆稱讚:「哎喲,滿厲害的嘛!」開始收拾兩人的餐具。
「你也不笨嘛。」
「關於滅絕的文明,我是有點研究。」
「吉子也真是的……何必去追那個有妻有子的建築師,趕快跟你在一起不就好了。」
「沒辦法啊。感情的事,局外人再怎麼說也沒有用……」
「你也真傻,你不說誰說啊。」
儘管心裡認為的確沒錯,但夏瀨也只是說聲「謝謝招待」道了謝,把剩下的啤酒喝完……
大概是奇怪我怎麼關在廁所裡那麼久吧,哥哥突然敲廁所的門,問:「你在幹嘛?吃壞肚子了?」我回答他沒事。「你還好嗎?」他擔心地問。
「我要先睡囉。」
「……」
「我關燈囉。」
「你很煩欸!我在上廁所,不要跟我說話啦!」
哥哥嘴裡唸唸有辭,從廁所前離開。
我寫的小說不是虛構的。吉子她們真的就住在車站的另一邊,半年前分手之後,一到週末我還是會厚著臉皮去玩。小說裡寫的全都是事實。只是,沒寫進這部小說裡的事情更多。就好像去葡萄園摘葡萄一樣,一直以來,我只摘沒有受傷的成熟葡萄。這樣算起來,就算寫的全都是事實,但到頭來還是不完整。如果不把每一分每一秒毫不遺漏地寫下來,結果還是假的。也許我現在做的,就是從完整的現實中摘取幾串,把假的留給明天。
……吉子是以派遺人員的身分來到夏瀨上班的船公司的。公司舉辦了歡迎會,歡迎包括她在內的幾名派遣人員,雖然說會後是夏瀨約她續攤,但卻是吉子誘導他主動的。後來,吉子半年的派遣契約結束,調派到一家建設公司。
夏瀨從來不覺得吉子愛上了自己,只是她也不介意夏瀨單方面喜歡她,像這樣毫不客氣地去她家,她也不曾抱怨過一句。伯母倒是似乎多少對夏瀨寄予同情,偶爾會罵女兒:「討厭就討厭,好好跟人家說清楚呀」,但吉子卻認為「討厭、討厭的一直說,說到後來一定會變成喜歡的!」好像把自己和建築師的事重疊在一起了。
結果,《世界不思議發現!》夏瀨只答對一題就關掉電視了。早就已經收拾好的伯母說:「反正你明天也是一早就來吧?要回去太麻煩,不如留下來過夜吧。」開始把棉被從壁櫃裡搬出來。夏瀨趕緊拒絕:「不了、不用了!不能這麼麻煩伯母……」伯母取笑:「還跟我客氣呢,都已經麻煩我這麼多了。」
這時候,門開了,吉子回來了。她一副沮喪不已的樣子,劈頭就看著她母親的臉問:「媽,有沒有我的電話?」
「怎麼了?」
「他沒來。」
「所以我不是告訴過妳了嗎。別肖想別人的丈夫。」
「可是……」
吉子臉上有擦過淚的痕跡,夏瀨插嘴對她說:「他沒有手機喔?」她看看鋪好的被子又看看夏瀨,嗤笑道:「幹嘛?終於要在我家過夜了?」
「不、不是的!是伯母她……」
吉子根本不在意夏瀨的藉口,一副下定決心的樣子,突然就說:「我去看看!」
「去?去哪裡?」
「就是他家呀!我去看看他怎麼樣,我很擔心……」
「妳這孩子也真傻,這時候他一定是被妻子和孩子圍繞著,開心的呢!」
「我又沒有說要闖進他家!我只是去看看……」
夏瀨邊綁枕頭套,邊看著爭執的母女。
「我要去!」「不准去!」的對答來來回回持續了一陣子,母親用力抓住堅持要出門的女兒的手。
「妳沒有權利破壞別人的家庭!」
「我就是不要!我絕對不要這樣結束!」
「太難看了!」
伯母正要甩吉子巴掌的時候,夏瀨再也忍耐不住,站起來大叫:「伯母!妳就讓她去吧!」
吉子甩開母親的手,從玄關出去了。
結果那天晚上,吉子沒有回來。伯母為了調整心情喝起白蘭地,夏瀨一直陪她陪到十二點多。
「假如說,是你跟她約了卻沒出現,你覺得她會擔心你嗎?」
「……」
「看著你呀,我就覺得可憐。假如你出了車禍還是怎樣的,突然走了,那時候她要是連一滴眼淚也沒流的話,你怎麼辦呀?」
「不會啦……」
吉子的母親一喝醉,就會說起賣掉位於葛飾的房子的事。她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賣掉居住多年的房子,買了這間新的公寓大樓,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
用文件夾夾好稿子,沒上廁所卻也沖了馬桶。房間裡燈沒關,但哥哥在床上一臉嚴肅地睡著了。哥哥在東京這間套房裡,讓我有種非常不可思議的感覺。不是突兀,而是更沉重的感覺。哥哥坐在便當前的樣子,簡直就像被砍掉了手腳一樣,而現在睡在床上的神情,乍看會讓我覺得他好像在瞧不起人,但其實可能已經死了。
我盡可能不發出聲響,收拾了桌子,從壁櫃裡拿出毯子和枕頭,然後關了燈。不過話說回來,待在這個房間裡的哥哥,顯得非常不自由。
哥哥來到我這裡,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了。我連日加班到很晚,所以我們幾乎沒有說上幾句話。哥哥照樣整天在這個房間裡混。下班回來,一看到哥哥中午和晚上吃的兩餐份的便當空盒擺在桌上,讓人不想罵人也難。
我工作累得半死回到家,連沖澡的力氣都沒有,拿鬆開的領帶蓋住眼睛躺在地板上,就聽見哥哥問:「對了,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幹嘛?」
「沒有,就覺得你的工作好像很辛苦。」
「沒有工作不辛苦的。」
我自己也覺得這樣講很酸,便立刻又補了一句:「我是在船公司上班。」
「哦,船公司……你從小就喜歡坐船嘛……」
「是船公司的總務。每天都在書桌前整理文件。」
「可是偶爾也會坐船吧?」
「坐個頭啦!只有剛進公司時去參觀過一次而已。」
我拿掉遮住眼睛的領帶,趁勢爬起來。進了浴室,邊調水溫,邊想起浮現在家鄉港口的白色防坡堤。
無論任何理由,一律禁止在港內游泳。而我會把這些規定拋在腦後,從繫在岸上的船跳進港裡游到防波堤。不過有時候「幸丸號」的船主幸田先生看到我,會要我幫他把船清乾淨然後給我零用錢。打從搬到外婆家那時起,我和哥哥總穿著媽媽選的時髦童裝,但嘴巴又不甜不討人喜歡,鎮上幾乎沒有人會跟我們說話,唯有「幸丸號」的幸田先生不把鎮上的默契放在心上。
港裡只有幸田先生以幫釣客開船出海作為生計。除了幸田先生,別的人也有漁船,但幸田先生在市內的釣具行和電話簿上以個人名義刊登廣告,獨占了所有的生意。
來找幸田先生的釣客,幾乎都是要到軍艦島的人,「幸丸號」會一一行駛到被稱為丸、電影院下、棧橋、泳池下等等景點。
軍艦島是位於我們所住的港口外十公里的海面上的一座產煤的島,最盛時期包括礦工和其家人在內,總共有五千多人住在那裡,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地底下有深達數百公尺的礦區,地面上是容納五千人的高樓公寓,整座島呈立體結構,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人工島。可是,昭和四十九年(西元一九七四年)礦坑封閉後,便成為一座完全無人的廢墟之島。因為外貌和軍艦「土佐」相似,所以叫作軍艦島,但其實端島才是正式的島名。從名字就知道,在發現煤礦之前,並不是什麼重要的島。
搭「幸丸號」靠近軍艦島,為了防堵巨浪而包圍島嶼四周的防波堤,令人想起難攻不克的孤島要塞。島內腐朽無人的高樓公寓林立,裡面還有大正時期實驗性建造的九層與七層建築。若是沒有軍艦島,那就是一幅碧海藍天的祥和風景,但因為這座浮在那裡的水泥島,便散發出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殺伐之氣。
被取消的城市導覽
有一個男人在車站前禁止停放腳踏車的區域,大大方方地剪腳踏車的鎖。要剪斷鐵絲製的鎖,他手上那把老虎鉗似乎太小了。即使如此,他仍然很有耐性,一次又一次不斷地剪。車站前行人很多,居酒屋和電玩中心的霓虹燈也把附近照得很亮,偶爾有行人皺著眉頭瞪著他經過,但沒有任何人停下來。
我會注意他,是因為他的側臉和我哥很像。不過我很快就看清楚他不是哥哥,原本準備直接經過,卻看到他手上的老虎鉗。我假裝找腳踏車,繼續觀察他的行動。時間並不是深夜,他也沒有避人耳目的樣子。假如是小偷,應該不會這麼光明正大吧...
目錄
日日春
零下五度
颱風過後
深夜兩點的男子
乳牙
那些人
大阪幽微
24 Pieces
燈塔
被取消的城市導覽
日日春
零下五度
颱風過後
深夜兩點的男子
乳牙
那些人
大阪幽微
24 Pieces
燈塔
被取消的城市導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