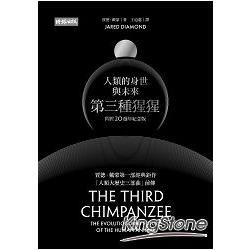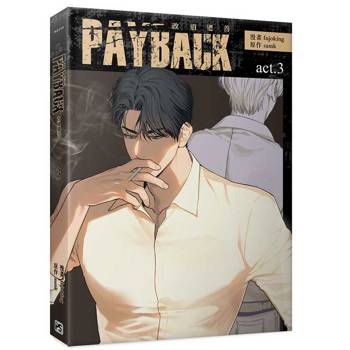賈德.戴蒙第一部經典鉅作
「人類大歷史三部曲」前傳
榮獲英國科普書獎、《洛杉磯時報》科普書獎
「人類大歷史三部曲」前傳
榮獲英國科普書獎、《洛杉磯時報》科普書獎
在自然界,人類與黑猩猩極為接近,基因之差異不及2%。人與黑猩猩應屬同一類目,因而稱人類是「第三種黑猩猩」絕不為過。但人類是如何變成世界的征服者,進而掠奪、霸佔世上大部分的資源?
《第三種猩猩》是人類的自然史與興亡史,賈德・戴蒙援引深入紐幾內亞部落的實際經歷,充分演繹人類的生命循環、人類地理學、人類對環境的衝擊以及人類的動物面向等。本書分為五大篇章:
• PART 1「不過是另一種大型哺乳類罷了」:涵蓋數百萬年的人類演化史,直到一萬年前農業興起前夕。討論保存在考古紀錄與生化紀錄中的證據,並解答在人類與黑猩猩的2%基因差異中,何者是讓人類得以演化大躍進的關鍵。
• PART 2「奇異的生命循環」:探討有關人類獨特文化發展之生命循換特徵的變化。人類在嬰兒斷奶後仍繼續餵食(其他哺乳類讓雛兒自行覓食)、大多數父親與母親一樣會照顧嬰幼兒、女性會經歷更年期⋯⋯凡此種種我們習以為常,卻是人類最背離祖先之處。
• PART 3「人為萬物之靈」:探討一般認為使人異乎禽獸的文化特徵,例如語言、藝術、技術與農業。但事實上,此文化特徵也包括人類紀錄上的汙點,例如嗑藥。
• PART 4「世界征服者」:探討人類的兩個陰暗特徵——仇殺外族之傾向與對環境日漸加速的破壞。看似是人類的「不良演進」,但實則均來自我們的動物原形。
• PART 5「日中則仄」:大量毀滅物種、過度開發環境並非工業革命後才有的新鮮事。不僅動物界有許多具體而微的案例,先民也非想像中重視生態倫理,能與自然界和諧共處的一群人。
戴蒙逐一檢視人類進化之過程,論證「人類是不折不扣的動物」之見解,從而對人類社會之重大議題,如兩性關係、族群關係、生態問題等,都有重要且不落於凡俗的睿見。
《第三種猩猩》是賈德・戴蒙第一部經典鉅作,作為「人類大歷史三部曲」的前傳,成書至今業已二十多年,但書中論述竟絲毫不受時空所限。是否無法擺脫動物原形竟是人類之宿命?我們面臨當前的生態困境與無止盡的鬥爭,最終是否仍將走上自毀之路?
閱讀本書除能反思「人類乃萬物之靈」此言之狂妄,更將重新界定「文化」與「道德」之定義。
名人推薦
《第三種猩猩》是賈德.戴蒙第一部最重要、也最精采的作品,從兩性議題、族群關係到生態問題,都有重要的見地;更是戴蒙首次觸及人類史之新面貌與原始部落故事,其後方於「人類大歷史三部曲」——《槍炮、病菌與鋼鐵》、《大崩壞》、《昨日世界》——做出更完整的論述。本書可說是三部曲的前傳。-|||生物人類學者/本書譯者 王道還|||
精彩!戴蒙以博物學家的敏銳眼光與哲學家的巧思來研究人類的行為和起源。-|||《感官之旅》作者 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
本書絕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哈佛大學教授、《生物圈的未來》作者 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
一本人人必讀的經典之作。看了本書,我們才得以明瞭身為人類的意義。-|||史丹佛大學教授、《人類的演化》作者 保羅.埃力克Paul R. Ehrlich|||
機趣橫生,風格聳動。在作者的刺激下,我們不由得開始思考演化之謎——我們從何而來?之後又將走向何方?-|||《紐約時報書評》|||
演化生物學與人類學的鉅作,充滿精闢之論。-|||科克斯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