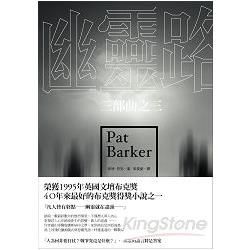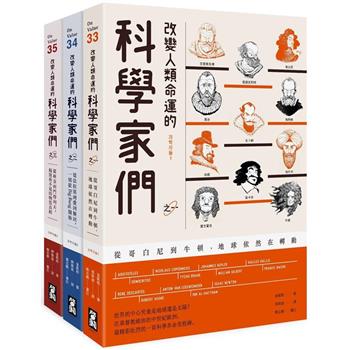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榮獲1995年英國文壇布克獎★
40年來最好的布克獎得獎小說之一
40年來最好的布克獎得獎小說之一
「重生」三部曲完結篇,《幽靈路》,人物及戰爭都將走向終點
如同《愛麗絲夢遊仙境》,整個王國已經瘋了
軍醫瑞佛斯因病中之夢,回憶起駐軍美拉尼西海島過往
竟與當前的一戰戰場遙相呼應
這場戰爭瘋了.所有戰爭瘋了!
薩松坦承歸建前在病床邊見到鬼魂質問為何不回戰場
普萊爾歸建後每日堅持第一人稱書寫日記與死神對抗
瑞佛斯在一場熱病中回憶過去部隊駐紮美拉尼西亞時
見識到殘忍卻合法的獵頭儀式與各種惡靈咒語
「白人在場,幽靈害怕─」在場的白人是誰?
凡人皆有終點──
為何人類仍要戰爭?戰爭究竟是什麼?
答案竟在幽靈的語言之中
本作描寫一戰最終數月的慘烈情景,不僅潛入軍人內心,
探討人心在絕境產生的質變、做人的意義──
為何非要打仗?戰爭究竟是什麼
英國女作家派特.巴克神乎奇技地將這部描寫一次大戰英國士兵三部曲的傑作
拉出一戰戰線,
藉由軍醫瑞佛斯病中之夢回憶駐紮美拉尼西亞目睹的的獵頭祭儀
與普萊爾在法國前線以第一人稱書寫的大兵日記並行對照。
更以「白人和幽靈」的設定,洞悉戰爭本質,令人嘆觀止
作者以血肉野性的筆法,直鑽被戰爭摧殘的人心
一本令讀者幽幽難忘的無價小說,為一戰經典文學三部曲畫下完美句點。
【謹以《重生三部曲》中文版面世.見證第一次世界大戰100週年紀念】
書評
敘事功力強勁而寫實,能從置身事外的人性觀點關注主題,觀察之眼毫不畏縮,直鑽被戰爭摧殘的人心。整體營造出一本令讀者幽幽難以忘懷的無價之小說,以本書為大家應讀的三部曲畫下句點。── 《愛爾蘭時報》
有人或許認為,一次大戰的苦海早已寫得人盡皆知了,巴克仍能喚回驚人的血淚史,證明這一類的書籍仍值得創作。──《獨立報》
巴克的才情深廣度與想像滿載的理解力在小說界罕見,創作本書的成就卓越,獲獎實至名歸。── 《每日電訊報》
由於虛實揉合得巧妙,巴克得以擴展其揮灑的空間,創作時能兼顧權威與想像,書寫出能與一次大戰經典文學並駕齊驅的三部曲鉅著。全力推薦。──《觀察者雜誌》
勇氣、仁慈、殘酷、偽善等種種本質,人心在絕境產生的質變,做人的意義何在,這些主題在書中有最深刻而中肯的探討,是巴克至今著墨最深的一部。──《週日獨立報》
令人嘆為觀止。故事充實過癮。情節綿密,文筆優美,結構巧奪天工,內容溫婉、恐怖、逗趣。讀完之後,歷歷在目的故事與戰事繼續存活在想像世界當中。──《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巴克不僅自己潛入軍人的內心,更帶領讀者重遊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亂世。──《週日電訊報》
巴克的筆法有一種血肉野性…………將普萊爾描繪成既嚇人又驚魂未定,奇特的心理融合良知、壓抑、性暴力解放,令人難忘。本書壓抑戰時情緒以製造張力,同時容許讀者歡笑哀傷,我讀到最後熱淚成行。──《觀察報》
劇力超絕的鉅著,值得力薦給巴克至今最廣大的讀者群。我深信「重生三部曲」將獲得各界推崇為二十世紀末英國小說界少數真傑作之一。──強納森.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