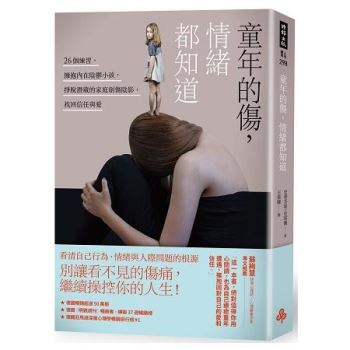一場離奇的舞廳大火,一夕帶走四十二條人命
以及一個女子四十年的自由……
以及一個女子四十年的自由……
是誰放的火?
改編自真實事件。見證真相的代價
「鄉村黑色文學」大師丹尼爾.伍卓
繼提名奧斯卡最佳影片《冰封之心》原著小說六年後全新力作
★美國亞馬遜書店當月選書&年度百大編輯選書
★《堪薩斯星報》年度最佳小說。《洛杉磯時報》書卷獎決選
★金獎導演李安最推崇的美國大師。《與魔鬼共騎》原著小說作者
一九二九年密蘇里州西檯鎮一場舞廳大火,帶走了四十二條人命,包括女僕奧瑪的妹妹茹比,也在這場大火中喪生。造成大火意外的肇事者是誰?誰是縱火者?是附近浪蕩的吉普賽人?還是舞池中翩翩起舞惹人嫉妒的新婚夫妻?四十年後,當奧瑪的孫子問起當年大火事故,時隔多年,奧瑪說出了她埋藏心中許久的祕密……
改編自真實事件,全書以精簡的篇幅描寫一場火難在小鎮無盡地悄悄蔓延。四十二條人命不是災禍的結束,作者透過一名女僕為主角,親眼見證長達四十年地方小鎮各人家業的灰飛煙滅。讀罷讓人不寒而慄。世人皆善忘,丹尼爾.伍卓不愧美國大師,他不以寬容或慈悲來撫慰讀者,而是要世人記住眾人犯的罪,並因此格外珍惜人性的單純。
書評
「輕薄短小不失人性光輝……《野火》的價值也在於其亮眼的筆調,精準的字句與近乎《聖經》韻律的對話比比皆是……更進一步證明伍卓是值得珍愛的作家。」──《西雅圖時報》
「若有人發起請願行動,呼籲將伍卓先生列入美國現世文學巨擘之林,我必會欣然聯署。伍卓筆下的往昔能傳達凱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普立茲獎得主,美國小說家)特有的苛愛,喧鬧中見幽默的詮釋法可媲美查爾斯‧波帝斯(Charles Portis),迂迴轉折而優美的語句則是他個人專屬的特色。」──《華爾街日報》
「對於初次閱讀伍卓作品的讀者而言,《野火》是絕佳的入門書,也是一份歡迎再讀幾本的邀請函。全文雖短小……卻能詳述幾代恩仇……是值得一讀的佳作。伍卓的敘述自始至終不慍不火,將過去詮釋得比現代更親切,以更不寬容的眼光看待過去。」── 國家廣播電臺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