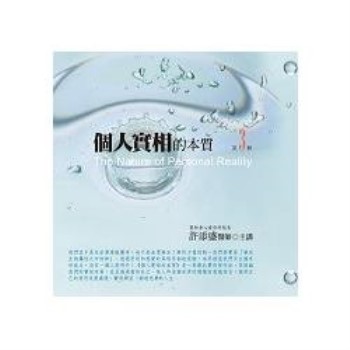My Dear Art
忽然,在別人的眼中,我是個「藝術收藏者」,這個名稱讓我覺得很不習慣,每回被人如此稱呼的時候總會讓我尷尬地笑著,不知如何回應,也許是這些年來固定在《典藏投資》雜誌寫了一些我對藝術收藏看法的關係。其實比較多的時候我分享的是一個把藝術帶回自己生活中的平常人觀點,若是真的仔細來看這些分享,真是慚愧,其中沒有太多嚴謹的學術性,也沒有可以分析推算的投資前瞻性。一轉眼寫了那麼多年了,最大的收穫是與許多觀點相近的人成為了朋友。生活四周還是有許多人喜愛把藝術放在生活裡,也感受到跟我相似的喜悅,這就是物以類聚的原因吧。
說實在話,真實的生活裡不順遂的事情大過於期待,這個想法往往都因為來自於:自己對於生活的期待與真實的生活之間的差距所致,面對這些差距我們都可以在各種文化資訊上的閱讀與思考裡得到一些紓解與安慰。所謂文化上的閱讀是依每個人的渴望而定,對我來說:文學、音樂、美術以及電影是最親近的,特別是美術裡的世界,更是我從少年到現在,不憑藉目的性陪伴我最久的一個愛好了。當我開始入世地明白藝術品是可以買回家之後,人生從此有了較大的改變。我開始把打動自己的藝術品搬回家、放在我的生活裡,當我面對現實生活感到疲乏、感到無力或感到挫折時,總是先放下現實世界的自己,走進藝術的裡面,用另一個感官、思維和價值去自由地放開自己。面對經濟能力可及之內帶回家的藝術品,我珍惜的認為自己只是「暫時」的保管者,此刻自己可以如此近距離去閱讀它、感受它,並且延伸閱讀跟它相關的文章、書本,這是我熱衷不疲的事情,這也讓我擁有另一個世界,去換個腦袋、換個心情,並且讓我有充足的能量再回到真實的生活裡。就這樣把藝術的閱讀頻繁得像吃飯、睡覺、呼吸般,圍繞在日常生活中,如今已經很難從我的生命裡拿開了。
到了中年以後,才更清晰了解到這個世界一直不停地在改變,過往你熟悉的事情,和你以為不容易改變的事物,都隨著時間漸漸地與你習慣的預期想像產生差異,也許是世界改變了或是你自己也靜靜地變化了;過去依然凝結在過去,而現在世界與自己已經帶著不同面貌的存在著和變化著。然而這些改變都應該是好的,如果你願意用開放的心去面對這個世界,面對自己。透過自己在藝術與時代的對照,我始終相信改變是必然的,我們無需感嘆,只有行動,開始啟程去擴展閱讀,如同陪伴在身邊的藝術作品一樣,它們如時光凝固在那裡,但是它還有更深的意味值得你用你的生命經歷去對照與閱讀,同時間,在藝術的國土裡不斷地去尋找更新的觀念、更新的邏輯與見解的作品,藝術品可貴的就是透過另一個生命觀看世界的感想,來挑戰你或者開拓你。體會一個比凡胎之軀有限生命更大的世界。
優遊藝術世界對我來說是一件幸福與不可測之事,這樣的形容有一點像在探險吧,與一個你以為知道但是又充滿著不可測的世界之間的關係。是的,藝術是不可測的,即使是一張掛在自己家中牆上多年,來自大半個世紀前某位藝術家的創作,隨著自己在生活中對著它的重複對望,以及相關的延伸閱讀,最重要的是與自己生命成長歷練上的對照;一件耐人尋味的藝術品,它總是會隨著你的演變而有不同思考的延伸。同時在收藏上也可以隨著自己經歷的痕跡,拼構出屬於自己生命品味的藝術風貌,它能對照著你生命的成長。對照實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也非常耐人尋味。每一回我發現自己面對著掛在自己家裡的作品,沈浸在發呆、閱讀,或者無目的的思考中,看到自己是如此自由與知足,看到自己原來一點都不寂寞,因為藝術就在不遠處,也在我的心裡,它在我的昨日、也在我的明天,非常親密而忠誠的陪伴著我。
套句流行語,感恩太煽情,稱藝術為親愛的不為過,my dear art。
生命的風景
在你的生命中,總有幾首音樂放在心裡面,偶爾想起感動依舊,在你的生命中也許有幾個閱讀過的畫作閉上眼睛仍會想起,也可能在你生命中有幾本書始終念念不忘,影響了你的生活選擇,或許是幾部電影,在你生命中也許有幾個人與你相遇,因此念念不忘,在我們的生命中經歷了無數個風景,有些已經遺忘了,有些卻變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從事音樂工作那麼久,我總想如果有一個作品已經被別人的生命接納成為他的風景,有就足夠了。在我的生命之中美術與音樂都是如此的重要,經常感動於某位元音樂人的作品某位元藝術家創作的畫作。
吳冠中先生一直是我所佩服的藝術家,他一生致力於美術創作都是來自於自己身體力行生命的經歷,特別是在風景的創作上,幾乎可以閱讀得到在那清雅的村屋、遠山、靜雪、大樹、河流畫面結構中,每一筆都是屬於吳先生對於這個世界的好奇、探索、嚮往與眷戀。在作品中對生命的熱愛都誠懇的留在一筆一筆畫作裡。看著他描述的風景彷佛看得到他對生命的熱情,是如此沉靜而有力量,經得起時光流覽歷久而彌新,縱然大都是輕描淡寫的遠觀描繪,卻更勝濃彩重筆的渲泄作態,不賣弄學術姿態亦不歌功奉迎,全以樸素的本心和藝術的本資。吳冠中先生絕對是二十世紀亞洲最重要的美術大師,憑著深厚人文情懷和跨越東西方美學的新眼界與創作力,以生命的全部去創作實踐,不慕虛榮財富,即使早已在國際藝術拍賣紀錄上過了千萬元紀錄,吳先生不為所動儉樸自約,生前仍將手中創作捐給贈美術館,這與近幾年來藝術家急於與西方藝術仲介商合作,送畫去倫敦拍賣抬價是完成不同的價值觀與自我認知。其一生的執著情懷與藝術上的成就,已促使得各大美術館爭相收藏吳先生作品為榮,在藝術界吳先生作品流動更為稀少珍貴,吳冠中先生的藝術成就已明確留在美術史上的定位,這氣節也讓我想起了音樂界裡的一位朋友──吳彤先生。
吳彤老師一直以音樂來書寫著屬於他的生活經歷,民樂世家出身的他,有這深厚的國樂基礎,大學時期叛逆期組織過搖滾樂團「輪回樂團」,他那少有嘹亮寬闊能架禦金屬搖滾的嗓音讓當時的樂壇驚為天人,這段叛逆搖滾經驗更使得吳彤有了對自己生命與音樂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刻與遼闊的認知,一次長時間閉關思考後在一場北京大雪中出關,音樂上的跨界成了吳彤先生很重要的追求與實踐。無論是中西文化上,或是音樂與美術、文學、電影等不同性質文化之間的跨界。他精通創作,吳彤先生近十年來藉與馬友友先生與絲路計畫,更是致力於與國際不同音樂人做跨界音樂合作,試著讓全世界聽到屬於他出生和成長的審美與文化,透過音樂來描述著他的感想,描述著他的觀察和思考。
因為蘇富比的邀約,促成我把兩位吳先生各自在美術與音樂上的成就,試著做了一次跨界對話的試驗,非常幸運的立即得到了許多文藝圈人士的支援,對與吳冠中先生景仰己久的吳彤老師,也在重新閱讀吳先生的文章與作品後,進行了一次跨界創作,〈遠山〉一曲是吳彤先生對吳冠中先生致意的全新創作,平靜而委婉易懂,東方的笙與西方的鋼琴對話,全曲依吳冠中先生南方出生北方長居、大江南北行走寫生,一個時代的眼光都在遠觀的眼界裡進行,彩筆換成樂符溫柔又細膩的描寫。生命的風景之中有太多細微處是值得被書寫的,村屋、遠山、靜雪、大樹、河流以笙的筆觸委婉又遼闊行進,如蜿蜒河流生命所走過之處都是一道風景。這是一次從文藝上的實驗與分享,不久,〈遠山〉一曲在音樂網站上架後再以連接線分享。蘇富比也將在春拍圖錄中,特別精裝吳冠中先生晝作與吳彤先生音樂的限量圖錄,與文藝支持者分享。
江蕙裡的常玉
我幾乎快要忘記了一件事,若不是那天某位畫廊的負責人與朋友介紹我時提起了這件事,我幾乎都不再想起過。當他跟一位來自內地年輕藏家說起我曾把常玉的畫作照片放入江蕙專輯裡的塵封往事,我才又想起:是的,我曾幹過這件事。
這是我在收藏藝術近十年後的一次把工作與愛好的小小跨越,沒有任何利益驅使,只是一次有感而發的行為。最近江蕙因為做了人生最後一輪演唱會的決定後,始料未及的造成萬人空巷爭相搶票,進而演變成幾乎脫序的社會事件。恰好我在台北目睹整個過程,看著媒體藉機作文大肆宣揚,更刺激了群眾的焦急而產生一些過激脫序的行為。整個台灣陷入了新聞媒體找梗、人群集體杯弓蛇影的演出,沸沸騰騰的循環衍生。我猜想那些天的江蕙應該只能安靜的在家裡焦急著,以她的性格除了督促身邊的工作人員以外,面對這樣的台灣特色也別無方法。選擇沉默以對,這就是江蕙性格一部分,這也是屬於一個時代台灣人特有的一種性情。
話說回來,為什麼我把常玉和江蕙放在一起聯想?可能跟我一直以來喜歡透過閱讀,然後自娛自樂的對照歷史、把讀來的資訊與自己對藝術品的感受做延伸聯想有關係吧!江蕙向來都唱著閩南語歌曲,足足半個世紀已然成了傳奇。檢閱台灣閩南語歌曲的歷史與過程,除了因為時代變遷音樂人原創的部分以外,早年曾經有為數不少的日本演歌翻唱曲,因此閩南語歌一直未放在文化現象中的主流上,如今真把閩南語歌唱成了跨越族群、共識成一個時代的印象,連國語歌都望塵莫及。從文化角度看歷史,其實有前例:好好的藝術家透過文化上的個人才華而成日後人們對一個時代記憶的方式。我重讀蘇利文教授著作《二十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中所提的美術歷史演進,當年華人南方藝術家受到西方印象派影響,有許多西化的變革,其實都來自於日本的觀點再轉換,若真把那個時代的華人繪畫,放在同一平台上去檢驗,在那用西方已成型的概念,間接模仿造句的藝術家大有人在,就如同今日一些當代藝術局面,然而並不全然如此,少數能精準利用當時西方藝術上的言彙,並且不故作東方的情調姿態,於是留下了不朽創作的華人藝術家,常玉應該是第一人了。而在華語流行樂裡面江蕙演藝成就也有著相近的特質。在她所演唱中的閩南語歌曲中,即使有許多是屬於上個世代老歌或是來自他國文化的東洋演歌翻唱曲,可是江蕙都能自自然然變成屬於她自己的音樂,這絕對與一個人的生命本質有關係吧。
在藝術道路上,有的時候過度固執與堅持會讓自己故步自封,然而客觀自制下的堅持卻有可能讓自己走出自己的路,常玉是如此、江蕙在音樂上也是如此,這是我對這兩人最相似之處的感想。其實他們都是有缺點、有脾氣的平凡人,看過許多對於常玉的描述:傲慢、自由、不拘。而在他的畫作裡,卻看得到那還有細微、謹慎的靈魂,這一點是我所知道的江蕙異曲同工,她生活單調規矩,縱然功成名就,內心仍深守微言慎行的惶恐,只要面對演唱時,都把唱一首歌當成一次新的創作,嚴肅以待。我還記得二十年前第一次與江蕙合作時,確實讓我苦惱了好長一陣子,除了知道她的性格並非表面的瀟灑以外,另外我從來沒做過閩南語歌曲也是一大主因。還好,我少年成長在台南,南台灣還是或多或少有些熟悉。在那個年代的氣氛、成長過程裡,透過回想與閱讀資料的對照,我也慢慢理解並分析已成型的閩南語歌曲文化,有時哪些是屬於原創,有哪些是屬於歷史原因,和從東洋來的審美;也常思考日本演歌為什麼那麼合適貼近閩南語歌曲呢?
直到當我有機會去日本旅行,並且閱讀日本近代史的書籍,才明白日本演歌看似一個傳統,其實除了自己地域性的民謠以外,也是透過時間包容了屬於外來朝鮮移民歌謠的影響,形成了現在的東洋演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統。只是當它轉移到當時原創還不興盛的台灣音樂市場後,填上閩南語歌詞放在台灣人的口中,當時大部分人演唱均以模仿接近原唱為最高標準,只有江蕙不然,她既不循他人的標準模仿,也不做表現主義的張揚改變,她選擇屬於自己的成長經驗,屬於自己面對每一首歌的感受與審美,每一次演唱都是一次誠懇的創作;這也造成歌如人的風景,看似小家碧玉拘謹,卻有著勇敢磊落的大氣。以前我總覺得江蕙的演唱經驗造成她順手拈來的能力,是她天生的才華,但後來才明白:演唱也是一種創作,只有忠於自己生命的創作才能有好作品。這點呼應在常玉先生的創作上也是如此,雖然他大半生生活在巴黎,然而屬於華人的靈魂卻一直誠實的反應在作品中。在他非常熟練使用西方顏料和審美觀的表象下,仍看得出屬於華人文化中雅而節制的審美,以及自重的靈魂。
這也造成那年忽然厭惡起常態的唱片包裝方式:總是把明星精挑細選矯情的沙龍照,當作唯一包裝材料,因此決定把我心中氣息相近兩位藝術家做一聯想,把常玉的畫作編入了江蕙新專輯的包裝中。當然,我不任性,事前偷偷做了一些調查,我發現許多收藏常玉作品的收藏家們,都喜歡聽江蕙的歌!這不是巧合,是呼應我的推理,一切都在冥冥之中,一切都是靈犀相通吧。在江蕙的同意之下,和常玉收藏家與藝術圈朋友的支持協助下順利完成了這件事。我還記得記者發表會時,我特意買了一張常玉的限量海報送給了江蕙,為這件事情告了一個段落。在那個案子之後,我開始過著每月北京、台北的雙城生活,而江蕙也平穩的發展自己的演唱事業,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合作。雖然從此不再殷勤聯繫,只是偶爾在臉書與微博上私信問好。那天在新聞看到她自己宣讀在演唱會後停止半世紀的演唱生涯時,我沒有特別的感傷,反而替她高興。因為我知道唱歌對她來講永遠是一件非常嚴謹的事件,過了半世紀這樣的人生後,她也該有更多的時間,回到自己的生活了。
| FindBook |
有 14 項符合
一個人的收藏的圖書 |
 |
一個人的收藏 作者:姚謙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8-2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一個人的收藏
姚謙講美學、看藝術、談生活
用收藏品與自己生活交織出生命時光
一本思考收藏與人生的書寫
收藏絕對是一種個人品味的呈現!私人的收藏往往反應出了一個人最深沉內在的思考,思考中包含了審美觀、存在感與價值觀等等。
我喜歡一些小小的觸動和聯想,很快地領會了一套自得其樂的邏輯:不受別人的價值去決定我的收藏,總是另闢別徑去發掘藝術與收藏的樂趣。
在自得其樂的自我小收藏裡,沒有大富大貴的自我期許,那些小小的藝術品累積交錯掛在客廳、房間、樓梯間、走廊甚至衛生間,都成了我的親人,跟著我閱讀過的書籍,一起記錄著我的生活,添滿我生活中點滴喜樂……
這些藝術品的經歷,它們進入到我的生命,形成我內心的變化,經驗我們生命最有價值的事。原來自己一點都不寂寞,因為藝術就在不遠處,也在我的心裡,它在我的昨日、也在我的明天,非常親密而忠誠的陪伴著我。
在收藏的生活中,閱讀著那個時代、那些地方藝術家們的作品,感受著他們是如何在時代洪流中安身立命,去理解為什麼藝術觀點至今深刻影響我們的那一個世代。看見生命的各自美好,收藏著生命的風景。
作者簡介:
姚謙
姚謙,從事音樂創作三十餘年,歷任台灣EMI、Virgin、Sony唱片公司總經理,期間成功打造無數巨星,風潮襲捲亞洲不斷、更影響台灣無數的音樂創作者,其原創歌詞不僅膾炙人口,更在廣大歌迷心中留下深刻記憶,作品在亞洲華語流行榜上獲獎無數,奠定了華人流行音樂界中作詞大師的地位。
在音樂之外,長久以來更涉足於藝術收藏領域,姚謙擁有既深且廣的藝術品收藏資歷,更於兩岸三地知名媒體發表評論,其評論亦在許多藝術相關媒體間轉載與引用,在收藏領域中,其豐富的心得與看法正在兩岸三地漸漸形成一股影響的力量。
TOP
章節試閱
My Dear Art
忽然,在別人的眼中,我是個「藝術收藏者」,這個名稱讓我覺得很不習慣,每回被人如此稱呼的時候總會讓我尷尬地笑著,不知如何回應,也許是這些年來固定在《典藏投資》雜誌寫了一些我對藝術收藏看法的關係。其實比較多的時候我分享的是一個把藝術帶回自己生活中的平常人觀點,若是真的仔細來看這些分享,真是慚愧,其中沒有太多嚴謹的學術性,也沒有可以分析推算的投資前瞻性。一轉眼寫了那麼多年了,最大的收穫是與許多觀點相近的人成為了朋友。生活四周還是有許多人喜愛把藝術放在生活裡,也感受到跟我相似的喜悅,這就是物...
忽然,在別人的眼中,我是個「藝術收藏者」,這個名稱讓我覺得很不習慣,每回被人如此稱呼的時候總會讓我尷尬地笑著,不知如何回應,也許是這些年來固定在《典藏投資》雜誌寫了一些我對藝術收藏看法的關係。其實比較多的時候我分享的是一個把藝術帶回自己生活中的平常人觀點,若是真的仔細來看這些分享,真是慚愧,其中沒有太多嚴謹的學術性,也沒有可以分析推算的投資前瞻性。一轉眼寫了那麼多年了,最大的收穫是與許多觀點相近的人成為了朋友。生活四周還是有許多人喜愛把藝術放在生活裡,也感受到跟我相似的喜悅,這就是物...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一個人的收藏
──姚謙
我想,每一個人的一生都在收藏;收藏記憶、收藏情感、收藏某些與自己經歷或想法對照過的物質。小時候收集郵票、書籤、看過的戲票、讀過的書、聽過的卡帶、CD,和現在儲存在硬盤裡的文章、影片與音樂,當然也包括重複回頭看的照片:那些自己拍攝的風景與人,還有別人拍攝眼中的你。收藏這個動作,彷彿是每個生命都戒不掉的習慣,只是它表現得隱性或隱性而已,因為它可以從某個角度對自己證實自己存在過的痕跡。
我也不例外,生活中也不刻意的收藏一些事物,因此收藏得廣、隨興,沒有太多主動的目的,絕大多都...
──姚謙
我想,每一個人的一生都在收藏;收藏記憶、收藏情感、收藏某些與自己經歷或想法對照過的物質。小時候收集郵票、書籤、看過的戲票、讀過的書、聽過的卡帶、CD,和現在儲存在硬盤裡的文章、影片與音樂,當然也包括重複回頭看的照片:那些自己拍攝的風景與人,還有別人拍攝眼中的你。收藏這個動作,彷彿是每個生命都戒不掉的習慣,只是它表現得隱性或隱性而已,因為它可以從某個角度對自己證實自己存在過的痕跡。
我也不例外,生活中也不刻意的收藏一些事物,因此收藏得廣、隨興,沒有太多主動的目的,絕大多都...
»看全部
TOP
目錄
輯一 My Dear Art
My Dear Art
生命的風景
收藏的意義
去美術館
一位令人安心的朋友
與生活共構收藏
收藏的各自美好
寄蜉蝣於天地
任性一下,再解
無人風景
吟阿嬤的歌
孟東籬與三十歲藝術家的作品
陌生的激盪
說著時間故事的人
小收藏
收藏說
收藏印象
江蕙裡的常玉
人生戲劇
藝術的抒情
動人的主題
「腦與眼」的鑑賞力漫談
大城小記
都在被遺忘
財富以外的視野與胸襟
安薩克力戀人
「收藏」方法論
找出收藏的樂趣
烏利.希克的捐贈
圖像啟示錄
印象派愛情
重返台灣
輯二 幸福,雷諾瓦
我的美術史...
My Dear Art
生命的風景
收藏的意義
去美術館
一位令人安心的朋友
與生活共構收藏
收藏的各自美好
寄蜉蝣於天地
任性一下,再解
無人風景
吟阿嬤的歌
孟東籬與三十歲藝術家的作品
陌生的激盪
說著時間故事的人
小收藏
收藏說
收藏印象
江蕙裡的常玉
人生戲劇
藝術的抒情
動人的主題
「腦與眼」的鑑賞力漫談
大城小記
都在被遺忘
財富以外的視野與胸襟
安薩克力戀人
「收藏」方法論
找出收藏的樂趣
烏利.希克的捐贈
圖像啟示錄
印象派愛情
重返台灣
輯二 幸福,雷諾瓦
我的美術史...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姚謙
-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8-26 ISBN/ISSN:978957136322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