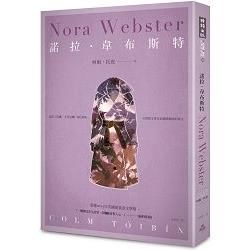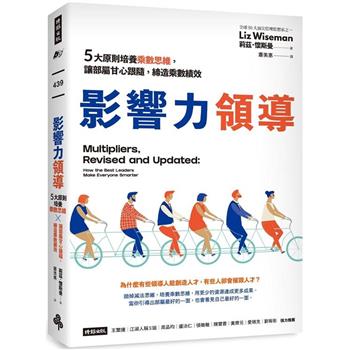「一個失去所愛的惡魔……」
年輕的寡婦,四個孩子的母親
破碎的家庭如何走出悲傷?
嚴厲的諾拉能否找回內心寧靜?
《布魯克林》作者柯姆‧托賓最新長篇小說
年少喪父的親身經歷,歷經十四年書寫完成
托賓更召喚出他創作生涯中最心酸駭人的場景
讀者將發現諾拉‧韋布斯特不為人知的内心世界
本書是托賓最悲傷的悼念之作,獻給母親與愛爾蘭
「一個寡母求生故事,卻能觸動普世人心。」─珍妮佛.伊根,《時間裡的癡人》
「令人痛徹心扉的小說,出自正在巔峰狀態的作家之手。」──《今日美國報》
★ 榮登全球30餘國暢銷榜,歐巴馬年度選書、亞馬遜百大編輯選書
★ 榮獲2015年英國霍桑登文學獎,柯斯達文學獎、佛立歐文學獎決選
諾拉.韋布斯特是個年輕的寡婦。個性剛烈的她,直到遇見丈夫墨利斯才將她從沉悶的人生中解救出來。在丈夫因為一種長期且痛苦的疾病去世後,諾拉的生活又回到婚前那般可怕壓抑的氣氛裡。獨力扶養四個孩子,經濟拮据,她不得不考慮賣掉房子。在她生活的小社區裡,沒有任何隱私可言,鄰居的打探,即使是出自好意,卻造成她更加沈浸在痛苦中,悲愴將她變回嚴厲的母親、難纏的鄰人,令旁人無所適從。唯獨在唱歌的時候.有著媲美母親生前一般動人的歌喉,偶爾帶來一些明亮色彩。只不過,唱歌雖然帶來了希望與快樂,卻也帶來罪惡感。因為諾拉執著地相信,唯有抵抗一切快樂的事物,她才能在思念裡留住墨利斯……
本書是托賓回憶年少時喪父的經歷,前後歷時十四年完成,成為他創作生涯中情感最壓抑也最澎湃的巔峰傑作。極端內斂的筆下,依舊描寫尋常日子,卻道盡人情冷暖。諾拉‧韋布斯特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祕密,你以為無法感同身受的悲愴,結果竟是如此打動人心。這名除了亡夫之外,不讓人輕易靠近、性格火爆又帶點驕傲,如優雅刺蝟般的剛毅女子,絕對是托賓創作生涯中塑造最出色、形象最強烈鮮明,最有距離感、神祕,卻也令人最難以忘懷的人物。
「本書出自於作者失去父親的親身經歷。一般人認為諾拉即是托賓母親的化身。評論家們也認定,作者書寫寡婦的重生,實則為近代愛爾蘭多舛的命運立傳。」──紀大偉,摘自總導讀「國族、性別、托賓小說的含蓄美學」(全文收錄於書中)
得獎記錄
二○一五年英國霍桑登文學獎
入圍柯斯達文學獎決選│佛立歐文學獎決選
書評
◎以作者的第八本小說而言,本書之難度直逼高空鋼索……原本是稀鬆平常的寡母求生存故事,在柯姆‧托賓極端內斂的筆下道盡人情冷暖,成了一部精彩亮麗、情節簡練俐落的小說,讓尋常的日子貼近玄奇境界……諾拉‧韋布斯特不為人所知之處多得是,而這份神祕感使得她的重生更能觸動普世人心。-《時間裡的痴人》作者珍妮佛.伊根,《紐約時報》書評
◎引人入勝……發人深省……比包法利夫人多一份省思,少一份自毀,最後遠比註定悲劇收場的安娜‧卡列尼娜更適合當母親,也沒有安娜的誇張造作。諾拉令人難忘之程度絕對與兩者不分軒輊,而且可信度遠比兩者高。針對本書多言無益,只會破壞大師級的難忘小說。
─美國國家廣播電臺
◎新作仍可說是托賓的巔峰之作。托賓以簡樸的力道表現寡婦喪夫的痛楚,你以為你無法感同身受的悲愴,結果竟是如此打動人心。─《觀察家》年度小說
◎與托賓備受好評的《布魯克林》堪稱完美的姊妹作……在描繪愛爾蘭鄉村小鎮的同時,融合了諷示和鄉愁。精巧且引人入勝。─《週日泰晤士報》年度小說
◎這部作品中托賓完美展現了如何嚴謹地鋪陳故事,並且貼近觀察人情世故。─《每日電訊報》年度小說
◎精細雕琢之作。今日少有作家能像托賓,有勇氣描寫生活如同日常而不加矯飾,卻仍深深感動我們。─《衛報》年度小說
◎《諾拉‧韋布斯特》出自文筆處於巔峰狀態的作家之手,是一部人性特寫的傑作,優美而大膽。─《紐約時報》
◎悄悄鑽進讀者的心,讓讀者自由揮灑想像力。─《今日美國報》
◎《諾拉‧韋布斯特》即可能是完美小說的典範……行文找不到特技和噱頭,只感受得到溫情與敏銳的省思,而這正是柯姆‧托賓高明之處……大家稱呼托賓為優美作家,是因為大家不知該如何定位筆法如此精妙、同理心如此簡明的高手。有些奧妙是無法以批評來解密的。托賓不只是優美作家,他是偉大作家。 -《洛杉磯時報》
◎鉅細靡遺……托賓的慢版行文開創出處處閃亮美景。-《紐約客》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