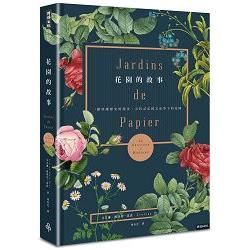圖書名稱:花園的故事
‡‡‡ 走一趟穿梭歷史的花園漫步 ‡‡‡
花園──這個充滿聲響、香氣和動感的地方,能夠讓人獨處,讓人享受到充滿安全感的自由,花園的沿革充分反映出人類文明中藝術文化、自然科學、社會學、人類學、科技、神話、文學、美學等諸多面向的演變和影響。
從聖經裡的樂土「伊甸園」到風行歐洲的英式園林,我們穿梭樹木花草間瀏覽花園的歷史,挖掘花園的源起和多元面貌。
‡‡‡ 一起拜訪法國文豪筆下的祕密花園 ‡‡‡
從12世紀開始,花園變成藝術和文學的主題,是屬於作者想像的向量空間,在小說裡扮演不凡的角色。作家們以文字打造了他們的花園──私密的微型宇宙。花園為我們揭開作家的想像,和其寫作藝術的獨特形式;而當我們翻頁時,這世界的本質會從書頁間自行流露。
從盧梭到普魯斯特、從莒哈絲到喬治‧桑、從柯蕾特到莫迪亞諾,花園同時如現實的再現和想像的鏡子,一個充滿奇想和詩意的空間。它向我們述說幸福。它向我們述說我們自己。
作者簡介
艾芙琳‧博洛克─達諾 Évelyne Bloch-Dano
傳記作家、隨筆作家,其作品屢屢獲獎、被翻譯,在她的作品之中,傳記作品特別受到注目,例如:《左拉夫人》(Madame Zola,1997,Elle雜誌讀者大獎)、《普魯斯特夫人》(Madame Proust,2004,勒諾多隨筆文學獎〔Prix Renaudot de l’essai〕)、《喬治‧桑最後的愛》(Le Dernier amour de George Sand,2010)、《蔬菜的傳奇歷史》(La Fabuleuse Histoire des légumes,2008,布拉齊耶美味文學獎〔Prix Brazier de l’essai gourmand〕)或敘事作品《尚佩雷門》(Porte de Champerret,2013)。
譯者簡介
周伶芝
中法翻譯、文字工作者、劇場編創、戲劇顧問、《PAR表演藝術雜誌》特約撰稿、《藝術收藏+設計雜誌》特約撰稿、劇場美學與創作相關講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