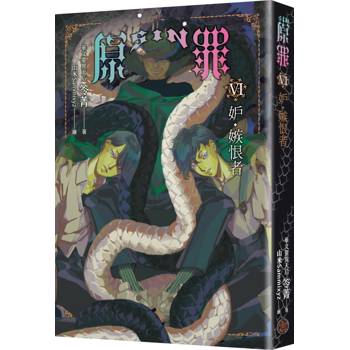一部西方經書如何被引用、誤讀,最後據為己用?
一場宣教行動如何觸動滿漢族群問題、華洋民族意識?
信仰如何成為狂熱,終於燃燒中國大半江山?
一場宣教行動如何觸動滿漢族群問題、華洋民族意識?
信仰如何成為狂熱,終於燃燒中國大半江山?
史景遷敘事史學登峰造極之作
魔幻手法鉤勒出波瀾壯闊史詩
恪守史料,布局奇絕,敘事精妙,文筆流暢
──漢學巨擘史景遷作品 經典重現──
洪秀全在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三年間建立的太平天國,造成兩千五百萬人喪生,經濟損失不計其數,大清國一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財力幾乎盡耗於此,斲傷大清元氣。史景遷並無意寫一本太平天國全史,而是想通過提供一個排比有序的歷史脈絡,來瞭解洪秀全的內心世界,去追索他的行為邏輯。史景遷在試圖追尋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熱情時,也在思索:有些人堅信自己身負使命,要讓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為之讚歎」,極少計算後果,而這是否就是歷史的大苦痛?
史景遷的論述重心在於爬梳洪秀全本人的心靈世界如何受到聖經的啟示,真摯相信能在塵世締造人間天堂,而這種認知更與當時中國華南動盪的時代脈絡合拍,最後竟造成無數生靈的塗炭,逼使清廷窮十年之力來鎮壓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太平天國》展現了類似《魔戒》的磅礡史詩氣魄,史景遷以他那迷人的蒙太奇寫作手法,打破了線性時間和僵固空間的制約,游移於歷史與小說之間,因此成為西方漢學界關於史學方法論爭辯的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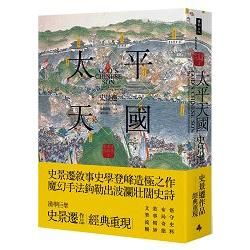
 2021/02/04
2021/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