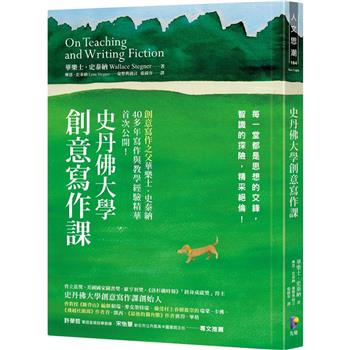「以前的人無法好好形容它,所以稱呼這為神……」
選擇自己的生存之道,正是人生的不可思議
選擇自己的生存之道,正是人生的不可思議
十八個月漫長等待,芭娜娜最新長篇小說
──寫在父親離世之後──
「我藉著書寫忘掉悲傷,每天專心一意地寫……
希望這部小說是照亮漫長黑暗的光。」
一本讓失去至愛的人重新感受被愛的奇蹟小說
守護著神聖山丘的小村莊,一個被遺棄的小女嬰,如何找到與生俱來的愛?
「妳最大的優點,就是知道真正的幸福價值。」
小幹是海邊撿回來的棄嬰,在一座緊靠著古墳的山丘村落裡,沒有血緣關係的外公和爸媽將她呵護長大,大家都喚她是「來自海裡的幸福種子」。小幹偶而也會疑惑大家口中的幸福是什麼。某天,從小一起在村子裡長大的野村,妻子離世後回到村子來,買下小幹家後頭的一棟宅院。此時,村裡卻不斷傳出嚇人的神祕事件──山丘出現兔子屍體,小幹也不停夢見死去親友……後面房子究竟發生過什麼事?這是古墳的詛咒?或者是神靈的主意?出生就失去一切、一無所有的小幹,何處是她的歸屬?誰又來守護野村先生呢?
花床,不只是文字的魔法,是抵禦誘惑、痛苦、不幸的「回復空間」
一旦你做好決定,生命需要的東西就在那裡,無須汲汲營營──
好像躺在鮮花床上午睡的生活。醒來後,彷彿新生。
因為真正的療癒從來不是輕飄飄的,是要拚了命換來的。
◎日本原封大野舞插畫書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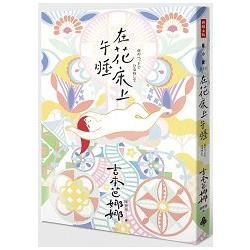
 2020/03/19
2020/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