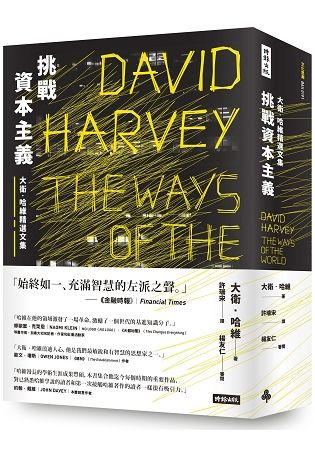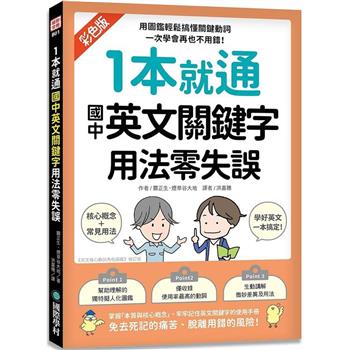我們可以繼續走資本主義這條路嗎?
抑或我們必須直搗問題的根源,
控制或消除資本無止境積累的衝動?
抑或我們必須直搗問題的根源,
控制或消除資本無止境積累的衝動?
親歷一九七○年代巴爾的摩的騷亂、絕望和公義失衡,如今躋身當代傑出批評家的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作豐富,影響廣泛深遠。大衛.哈維長年以來投身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戰線,站在當代各項議題的前線,以其獨具的觀點和廣闊的視野開闢論述疆界。
身為一名不受教條主義束縛的馬克思主義者,大衛.哈維以其創造力、洞察力與見解深具轉化價值(transformative value)著稱。《挑戰資本主義:大衛.哈維精選文集》收錄了大衛.哈維將近五十年思想旅程中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佳作,其中可見大衛.哈維開啟了馬克思主義與地理空間的重疊思考,將空間維度納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之中,結合馬克思方法論和地理分析的獨特理路,將城市視為可利用的重要權力基地。
本書先以簡要的引言說明哈維的研究方法和主題如何適用於理解中國眼下的發展,然後向讀者展示哈維結合馬克思方法和地理分析的獨特學說是如何形成的。此外更針對現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形成與運作提出精闢見解與批評,其巨筆囊括了當今全球若干首要議題:新帝國主義的形成、金融市場危機、牛津罷工運動的挫敗、巴黎興建聖心堂的歷史真相、後現代境況的意義……經由這些深具洞見的文章,我們看到大衛.哈維如何致力利用馬克思學說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現象,進而持續探索,最終成為全球頂尖的馬克思學說闡述者。
如前言作者約翰.戴維(John Davey)所言,「哈維漫長的學術生涯成果豐碩,本書集合他迄今每個時期的重要作品,對已熟悉哈維學說的讀者和第一次接觸哈維著作的讀者一樣很有吸引力。」
本書特色
☆集結大衛.哈維將近五十年學術生涯不同時期的十一篇最具里程碑意義的文章。
☆獨立主題,全局串聯,呈現大衛.哈維的洞見與批評方法。
☆探討資本主義當代、歷史及未來情狀,分擊資本主義的假面糖衣。
☆透過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及其對地理空間影響的解析與批判,重構社會階級和馬克思主義方法。
☆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楊友仁審閱。
好評推薦
「終如一、充滿智慧的左派之聲。」──《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哈維在他的領域激發了一場革命,激勵了一個世代的基進知識分子。」──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NO LOGO》、《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等書作者、加拿大知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
「大衛.哈維啟迪人心,他是我們最敏銳和有智慧的思想家之一。」──歐文.瓊斯(Owen Jones),《建制》(The Establishment)作者
「哈維漫長的學術生涯成果豐碩,本書集合他迄今每個時期的重要作品,對已熟悉哈維學說的讀者和第一次接觸哈維著作的讀者一樣很有吸引力。」──約翰.戴維(John Davey),本書前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