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兇手內心
這不是好萊塢版本的故事。它沒有被裹上漂亮的包裝或改造成「藝術」。這是事件發生的真正樣貌。若真要說,它比我所描寫的情景還要糟糕惡劣。
正如我以前慣常做的一樣,我得想像自己就是兇手。
我不知道她會是誰,但我已準備好要殺人。就是現在。
我太太整晚丟下我,和她的幾位閨蜜去參加一家食品保鮮盒公司辨的晚會。也許這無關緊要;畢竟,我們一直都在吵架,而且,幾乎是整天吵。不過,我還是覺得很鬱悶。我受不了了,再也不願意被她那樣對待。說不定她是出去和別的男人約會,就像我第一任太太一樣。她得到她想要的東西,不過下場就是在浴缸裡,臉朝下、嘴裡被嘔吐出來的東西給噎住。真是活該,誰叫她那樣對待我。我們的兩個小孩只好送給我的親戚照顧。那是另一件讓我煩躁不安的事,好像是我不好,無能照顧他們。
我獨自一人坐著看電視、喝了兩手啤酒,然後五分之一瓶葡萄酒。但我仍然覺得心情惡劣,愈來愈低迷。我還想喝啤酒或是喝點其他什麼。幾點了?九點半,或許。我起身開車到靠近販賣部的超商,又買了一手麋鹿頭(Moose Head)啤酒。然後,我開車到裝甲路(Armour Road),就坐在那裡喝啤酒,想辦法把心事理出個頭緒。
我坐在這裡愈久,就愈感到沮喪。我獨自在這裡,依靠著自己的妻子過活,他們都是她的朋友,沒有人是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小孩也不在身邊。你知道,我本來是海軍,以為前途能順利發展,但是並沒有。又是一個沒出路的工作。我不知道要做什麼。也許我應該乖乖回家等待,然後等她回來時和她攤牌,把事情做個解決。我一時百感交集,真的好想立刻找個人聊聊,但是周遭沒有半個人。見鬼! 居然沒認識半個人可以讓我傾訴心事。
四周一片漆黑。天色讓人開始感覺……有點誘人。一到夜晚,我就感覺特別興奮。黑暗使得我變成神祕客。黑暗使我變得無所不能。
我當時在基地的北邊,車子停在路旁,依然喝著啤酒,就在走過放養水牛的圈欄時看見了她。狗屎,那些水牛受到的待遇比我還好。
她剛剛越過馬路,正沿著路邊慢跑,單獨一個人,即使天色已經全黑。她很高,而且真的很漂亮,大約二十歲左右,有著褐色的金髮,綁著一條長辮。在月光的照耀下,她的額頭閃爍著汗珠。呦,非常漂亮。她穿著一件紅色T恤,胸前掛著金色的海軍陸戰隊徽章,紅色小短褲賣弄著誘人的屁股,使她的腿看起來就像永遠在邁步前進似的。身上連幾克多餘的肥肉都沒有。那些海軍陸戰隊的女兵身材維持得真好,這全靠平常操練有方。不像海軍的女兵,如果給她們一點機會,她們可能會鞭打普通男人的屁股。
我看著她欣賞了一陣子,她的乳房隨著跑步的韻律上下彈動。我想要出去和她一起跑,也許可以找個話題聊聊。但我知道自己的身材無法和她相比。此外,我醉得一塌糊塗。也許我該開車經過,邀她上車,載她回她的兵營,藉這個方式和她說話。
但是,我退一步想,她怎麼可能會理我? 說不定她正要去和海軍陸戰隊那些高大強壯的大兵約會?長得這麼嬌俏的女孩一定自認很了不起,根本就不屑理我。不管我怎麼說,她就是不會理我。已經一整天沒有人理我了,這輩子從來就沒有人理我。
不過,我不願意再容忍這些狗屎了,今晚絕不再容忍。不管我想要什麼東西,就非拿到手不可;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母狗一定得和我打交道,不管她喜不喜歡。
我發動汽車,往她所在的位置靠近,頭探出副駕駛座的車窗,大聲呼喊:「對不起! 你知道要回到基地的另一邊有多遠嗎?」
她似乎一點都不害怕;我猜這是因為車上有基地的貼紙,再加上她可能認為身為海軍陸戰隊成員,應該能夠照顧自己。
她停下腳步,往車子走過來,很信任我的樣子,微微喘著氣。她湊近副駕駛座的車窗,手往後指,回答我大約五公里,然後笑得好美,又轉身慢跑。
我知道這是我唯一的機會,再過一秒她就會消失不見。因此我打開車門,跳出去,然後追上她。我從後方給她重重一擊,她手腳不穩,然後我抓住她。當她了解大難臨頭時,有幾分氣喘吁吁,設法躲開我。即便以女孩子來說她算是高大健壯,但我還是比她高了快三十公分,而且一定比她重四十五公斤以上。我緊緊抓住她,用力重擊她的頭部側面,一定讓她滿眼金星。即使如此,她仍然拼命掙扎,想要逃開。好吧,她得付出代價;沒有母狗可以那樣對待我。
「不要碰我! 走開!」她大聲尖叫。我必須打昏她,才可以把她抓上車。我又用重拳攻擊她,她腳步搖晃快站立不住,然後我抓緊她,把她塞進副駕駛座。
就在那時,我看見兩名男子往這邊慢跑過來。他們大聲吼叫。我急速發動道奇車的引擎,沒命地逃走。
我知道我必須遠離基地;這是首要的事。因此我直奔靠近基地電影院的大門:那是唯一在這時間仍開放通行的大門。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就是從這道門進來的。我抱她坐直,讓她看起來像是我的約會伴侶。她的頭靠在我肩膀上,真的很浪漫似的。在黑暗中這一招頗能奏效,衛兵甚至一點反應也沒有,隨便就讓我們通過。
出了基地,我們行駛在海軍路(Navy Road)上,她甦醒了過來,又開始大聲尖叫。她威脅說,如果我不放她走,就要叫警察。
沒有人敢那樣子對我說話。現在大權握在我手裡,哪裡還輪得到她討價還價的餘地。是老子操他媽的掌控了一切,不是她。所以我一隻手放開方向盤,用力摑她幾巴掌。這才讓她閉嘴。
我知道不能帶她回家。我老婆可能已經回來了,要怎麼跟她解釋我到底在幹什麼?我需要有一個地方,和這隻新母狗單獨相處,不會受到干擾。我需要一個舒適的地方。我熟悉的地方。我可以為所欲為的地方,沒有別人打擾。我想到了一個主意。
我開到道路的盡頭,右轉進入愛德蒙•歐吉爾公園(Edmund Orgill Park)。我以為她又要醒過來,所以又用力揍她的頭幾拳。我驅車經過籃球場、洗手間,往公園的另一端開過去,來到了湖邊。我把車停在岸邊,關掉引擎。現在,我們終於單獨在一起了。
我揪住她的襯衫,使勁把她拉出車外。她像是處在半昏迷狀態,一邊呻吟著。她眼睛周圍有一道傷口,鮮血從鼻子與嘴巴流出來。當我終於把她拖出車子,按倒在地,她又掙扎著想站起來。這隻母狗仍然想反抗我。所以我撲向她頭部:有點像是騎上去,又重重掌摑她幾下。
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樹,枝葉繁茂,讓我覺得溫暖舒適又浪漫。她現在歸我管。我可以對她為所欲為。我撕開她身上的衣物:耐吉跑鞋,然後是她性感的海軍陸戰隊T恤,接下來是小短褲及藍色腰帶。她不再用力掙扎。她不再抗拒。我把她剝個精光,連她的短襪也脫掉。她還是想逃,但已無能為力。我掌控了一切。我可以決定這隻母狗的生死,還有死法。一切由我作主。今晚,我真有兩下子。
我一邊用前臂壓住她的脖子,讓她安靜,一邊開始撫弄她的乳房:左邊的這一只。但這不過是個開始。我要讓這隻母狗嚐嚐她從來不曾領教過的滋味。
我四處張望,站了一會兒,然後從這棵樹折下一根樹枝:大約七十到九十公分長。這很困難,因為那樹枝幾乎有五公分粗。折斷處的枝頭很尖銳,就像箭或矛。
她像是剛才昏死過去,但又大聲尖叫起來。她的眼神因病苦而狂野。老天,這麼多血,我打賭她是處女。這隻母狗在懊惱中逕自大聲尖叫。
這就是所有踐踏過我的女人的下場,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所有讓我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的下場。向生命乾杯!換別人來嚐嚐痛苦的滋味!現在她停止掙扎了。
等這陣狂亂平息之後,我開始冷靜下來。我往後靠,俯視著她。
她完全安靜不動。她的身體蒼白,看起來空蕩蕩,就像有什麼東西已經離她而去。我知道她終於死了。然後,好久以來第一次,我感覺整個人甦醒過來。
這就是所謂設身處地去了解受害者和加害者兩方:雙方如何互動。這就是你花了數小時在監獄聆聽囚犯的真實故事所得到的東西。從他們身上得到這些資料後,你就可以開始拼湊這些零碎的材料。然後命案本身就會開始對你說話。雖然聽起來可怕,但若想有效破解案情,你就非得這樣做不可。
我把這個技巧描述給不久之前訪問我的一位記者聽,她說:「這種事我做夢也想像不到!」
我回答:「或許吧,不過假如我們不希望命案常常發生,最好能仔細思考這樣的事。」
如果你能了解(不是以某種學院、知識性的方式,而是以一種發自內心深處、根據經驗的方
式),那麼我們或許就可以開始好好發揮一番。
前面描述的是發生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深夜、七月十二日大清早的慘案,兇手做案時的內心歷程。那晚,海軍陸戰隊准下士蘇珊妮•瑪莉•柯林斯(Suzanne Marie Collins),一位能力出色、受人喜愛、活潑漂亮的十九歲女孩,死於靠近孟菲斯(Memphis)海軍航空基地的一處公園,就在田納西州米靈頓(Millington)的東北方。蘇珊妮身高約一百七十四公分,體重約五十三公斤,她在晚間十點過後離開營區去慢跑,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隔天早上點名同僚不見她蹤影,不久後在公園發現了遍體鱗傷的赤裸屍體。根據驗屍報告,致死原因為遭人長時間勒住脖子、頭部遭鈍物所傷、身體有嚴重的內出血:一根樹枝的銳利尖角劇烈地戳入她的身體,從腹部的器官、肝臟、膈膜,一直到右肺部都被撕裂。她正在航空電子學校進行為期四個月的進修,原定十二日畢業,之後她將成為海軍陸戰隊第一批女性飛行員的一份子。
每次發表設身處地的犯罪描述總是讓我既痛心又難過,但是,若想從兇手的視角審視犯罪過程的話,就必須這麼做。另一方面,我也得從受害者的觀點看待整個經過,而這幾乎讓人無法忍受。但這也是我的工作:在成為維吉尼亞州匡提科(¬uantico)聯邦調查局學院行為科學部門(Behavioral Science division of the FBI Academy)第一位全職犯罪剖繪員之後,我替自己創造了這份工作。
通常,當我所屬的調查支援組(Investigative Support Unit)被邀請參與辦案時,負責提供行為剖繪和調查策略,以幫助警察逮捕不明行兇者。直至目前,我已經處理過一千一百多件這類的案子,但這次情況不同,警方來電時已經鎖定了一名嫌疑犯。他的名字是塞德利•艾萊(Sedley Alley),蓄鬍的二十九歲白人男性,來自肯塔基州的愛許蘭(Ashland),身高一百九十三公分,體重約一百公斤,是一家空調公司的工人,跟著他在海軍服役的妻子琳(Lynne)住在基地。警方在隔天早上就取得他的供詞,但他對事情經過的描述與我的版本多少有些不同。
海軍調查處的探員根據兩位男性慢跑者及基地大門守衛對汽車的描述而逮捕了他。艾萊告訴他們,他的妻子琳出門參加活動後,他感到非常沮喪。他在屋子裡喝了將近二十罐啤酒及一瓶葡萄酒,然後開著他那輛破舊的綠色水星(Mercury)廂型車到郵局販賣部附近的超商買更多的啤酒。
然後他漫無目的開著車,酒精使他愈來愈迷茫,直到他看見一名穿著海軍陸戰隊T恤與運動短褲的迷人女孩正慢跑著過馬路。他告訴警方他停下車,開始和她一起慢跑,隨便交談了幾句話。因為他剛才喝酒又抽菸,所以幾分鐘後就氣喘吁吁。他想要把他的心事告訴她,但是覺得她並不在乎,她不認識他,因此他就和她道別,開車離去。
根據他的敘述,由於酒醉,車子在路上迂迴地蛇行。他知道不應該開車的。然後他聽到重擊聲,感覺車子震動了一下,頓時明白他已經撞上她。
他把她抱進車子裡,要帶她去醫院,但他說她不停反抗,威脅要讓他因酒醉駕駛而遭逮捕。他駛離基地,前往愛德蒙•歐吉爾公園,在那裡停車,希望讓她安靜下來,並勸阻她不要報警。
但她繼續痛罵他,說他惹上大麻煩了。他大叫要她閉嘴。當她想下車時,他抓住她的襯衫,打開車門,並把她一道拉出去。她仍然大聲嚷著要叫警察抓他,並奮力逃脫。於是他撲向她,將她按倒在地,跨坐在她身上,防止她跑走。艾萊只是想要和她說話。
她仍然不斷試著掙脫(他形容為「扭動」)。在那當下,他「一瞬間失去了理智」,掌摑她的臉,
起先是一下,接著兩下或者更多。
他心裡一陣恐慌,知道假如她把他交給警方,就會很麻煩。他把她弄下車,心中盤算著該怎麼辦,然後回到車上去拿出一支黃色手把的螺絲起子,他要用它來發動這輛車子。當他回來時,他聽到有人在黑暗中奔跑。在恐慌中,他轉身過來,手臂向前猛擊,而碰巧就是握著螺絲起子的這隻手。結果他擊中了這名女孩,螺絲起子一定刺中了她並貫穿頭部側邊,因為她立刻癱倒在地。
這時候他不知如何是好。他該不該就此逃走,還是直接回到肯塔基州?他不知道。他決定必須讓她的死亡看起來像有其他原因,譬如遭到攻擊和強暴。不過,他沒有和她發生性關係(她的傷亡真的只是一件可怕的意外),所以他該怎麼做才能看起來像是一起強暴攻擊事件?
首先,他脫下她身上的衣服,然後抓住她的腳踝,將她的屍體拖離汽車,拉往湖岸邊,放置在一棵樹下。在這危急情況下,他手足無措、想捉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於是下意識折斷一根手邊的樹枝,然後翻轉屍體,將樹枝戳入她身體(他強調只戳了一次),讓她看起來像是遭到色狼攻擊。他跑回車上,倉促離開現場,往來時的相反方向離開公園。
亨利•漢克•威廉(Henry “Hank” Williams)是田納西州謝爾比郡(Shelby)的助理檢察官,試圖拼湊出事件全貌。威廉是我們這行最傑出的人才之一。他看起來氣勢宏偉,五官鮮明剛毅,眼神溫和但敏銳,四十歲出頭卻已有早生的白髮。他從沒看過這麼可怕的案件。
「我一看到檔案,就認為這一定是一樁死刑案,」威廉做出評論:「這起案件,我不打算接受認罪求情這一套。」
不過,他的問題在於:他必須對這樁野蠻的謀殺案提出犯罪動機的說明,讓陪審團可以了解。畢竟,有哪個精神正常的人會做出這麼可怕的事?
而那正是辯方盤算的切入要點。除了艾萊對「意外」死亡的說明外,他們又開始搬弄精神失常的論調。應辯方要求前來檢查兇嫌的精神科醫生似乎已表明艾萊患有多重人格障礙。很顯然,第一天海軍調查局探員偵訊他時,他忘了告訴他們,在蘇珊妮•柯林斯死亡的那個晚上,他分裂出三種人格:他自己;比莉,一個女性人格;與死神:騎著一匹馬,跟在艾萊和比莉駕駛的汽車旁邊。
威廉聯絡上特別探員哈洛•海耶斯(Harold Hayes),他是聯邦調查局孟菲斯調查站的剖繪協力人員。他向威廉描述色慾謀殺的概念,並提及我的同事洛伊•哈茲伍德(Roy Hazelwood)和我五年前替《聯邦調查局執法學報》(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所寫的一篇標題為〈色慾殺手〉(The Lust Murderer)的文章。
雖然在這些案子中,「色慾」是個常被誤用的字眼,不過這篇文章清楚描述了我們對這類連續殺人犯的研究,以及研究如何揭露出這些令人憎惡,並由操弄、支配及宰制所驅動的性犯罪。蘇珊妮•柯林斯之死似乎就是一起典型的性犯罪謀殺:一樁預謀的行動,由一名人格失序但仍具理智的人刻意所犯。即便他能分辨是非,卻仍無視道德規範,瘋狂行事。
威廉請我提出起訴兇手的策略建議,並想辦法讓陪審團中鮮少接觸邪惡的善良男女相信我的事件版本比被告所提供的更接近真相。
我必須做的第一件事,是向檢察當局說明我和我的部屬在打擊犯罪的這些年,從行為觀點所學習到的犯罪心理,以及過程中所付出的特殊代價。
我必須帶領他們一起進入我的黑暗之旅。
| FindBook |
有 18 項符合
破案神探二部曲:犯罪是天生邪惡還是後天塑造? FBI 探員側寫連續殺人魔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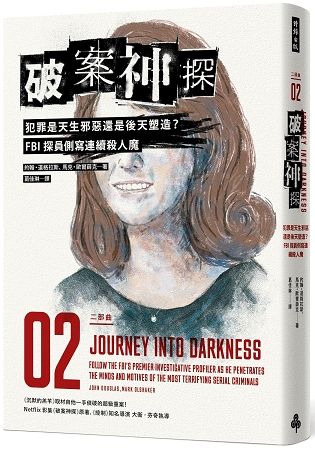 |
破案神探二部曲:犯罪是天生邪惡還是後天塑造?FBI探員側寫連續殺人魔【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出版日期:2017-09-26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破案神探二部曲:犯罪是天生邪惡還是後天塑造? FBI 探員側寫連續殺人魔
犯罪是天生邪惡還是後天塑造?
在心靈被黑暗覆蓋之前,他曾是我們之中的一份子……
《控制》知名導演 大衛.芬奇執導,影后莎莉.賽隆監製
Netflix改編影集10/13上線!
「我不知道她會是誰,
但我已準備好要殺人。
就是現在。」
‧ 犯罪人格是否真實存在?
‧ 兒童/青少年時期,我們就能預見未來犯罪的端倪?
‧ 犯罪者是否有改過自新、回歸社會的可能?
面對邪惡,站在第一線的FBI探員約翰.道格拉斯,使用「犯罪剖繪」走入犯罪者、受害者的內心,設身處地探觸他們的生活,帶領讀者展開一場黑暗之旅。想像自己是受害者,從受害者的恐懼與反應推及兇手性格;模擬兇手視角,理解他的犯案動機及手法特徵,串連起犯罪現場的細微線索。罪案會開始對你說話,行為證據將引領你找到嫌犯。
但除了逮捕罪犯、實踐正義,他所要搏鬥的,還包括這份特殊工作帶來的後續影響。親眼見證邪惡,黑暗就像擴散的毒霧,不知不覺滲入他的婚姻、家庭、身心,逐漸蔓延至他的人生。
對約翰.道格拉斯來說,二十五年的探員生涯,受害者的鮮血和家屬的淚水,每一天都真實上演。人所能做出最邪惡的事,超過你能想像的極限。本書不只是道格拉斯偵辦重大案件的紀實,更是執法者對正義、人的最終價值的深刻自白與省思。
作者簡介:
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
美國頂尖的罪犯人格側寫專家,任職美國聯邦調查局長達二十五年,也是現代罪犯調查分析的拓荒者。於調查局任職期間,首創「剖繪」緝兇專案小組,對連續殺人犯的做案手法及動機做系統研究,幫助美國及世界各地警察偵破許多重大刑案。
馬克.歐爾薛克Mark Olshaker
美國名電影製片人,同時著有多部極受好評的懸疑小說。1994年以《羅馬城》榮獲艾美獎。
作者其它著作
破案神探:FBI首位犯罪剖繪專家緝兇檔案(首部曲)
TOP
章節試閱
序曲:兇手內心
這不是好萊塢版本的故事。它沒有被裹上漂亮的包裝或改造成「藝術」。這是事件發生的真正樣貌。若真要說,它比我所描寫的情景還要糟糕惡劣。
正如我以前慣常做的一樣,我得想像自己就是兇手。
我不知道她會是誰,但我已準備好要殺人。就是現在。
我太太整晚丟下我,和她的幾位閨蜜去參加一家食品保鮮盒公司辨的晚會。也許這無關緊要;畢竟,我們一直都在吵架,而且,幾乎是整天吵。不過,我還是覺得很鬱悶。我受不了了,再也不願意被她那樣對待。說不定她是出去和別的男人約會,就像我第一任太太一樣。她得到她想要的東...
這不是好萊塢版本的故事。它沒有被裹上漂亮的包裝或改造成「藝術」。這是事件發生的真正樣貌。若真要說,它比我所描寫的情景還要糟糕惡劣。
正如我以前慣常做的一樣,我得想像自己就是兇手。
我不知道她會是誰,但我已準備好要殺人。就是現在。
我太太整晚丟下我,和她的幾位閨蜜去參加一家食品保鮮盒公司辨的晚會。也許這無關緊要;畢竟,我們一直都在吵架,而且,幾乎是整天吵。不過,我還是覺得很鬱悶。我受不了了,再也不願意被她那樣對待。說不定她是出去和別的男人約會,就像我第一任太太一樣。她得到她想要的東...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曲 兇手內心
第一章 黑暗之旅
第二章 謀殺背後的動機
第三章 陌生人的糖果
第四章 世間已無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物?
第五章 為了孩子們
第六章 反擊
第七章 藍蘇
第八章 一名海軍陸戰隊員之死
第九章 傑克和楚娣的熱忱奉獻
第十章 羔羊之血
第十一章 他們捉錯人了嗎?
第十二章 辛普森殺妻疑案
第十三章 罪與罰
第一章 黑暗之旅
第二章 謀殺背後的動機
第三章 陌生人的糖果
第四章 世間已無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物?
第五章 為了孩子們
第六章 反擊
第七章 藍蘇
第八章 一名海軍陸戰隊員之死
第九章 傑克和楚娣的熱忱奉獻
第十章 羔羊之血
第十一章 他們捉錯人了嗎?
第十二章 辛普森殺妻疑案
第十三章 罪與罰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約翰.道格拉斯、馬克.歐爾薛克 譯者: 葛佳琳
-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9-27 ISBN/ISSN:9789571371207
- 語言:繁體中文 適讀年齡:20歲以上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76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