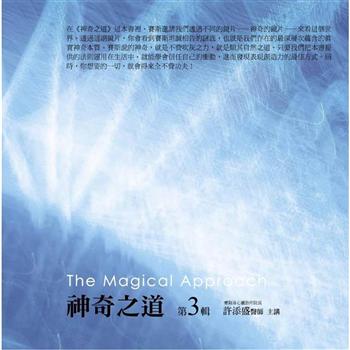生活越來越繁忙,世界越來越喧鬧,而哲學家越來越稀少了。
尤其在今天這個注重實用的時代,哲學的價值何在?
尤其在今天這個注重實用的時代,哲學的價值何在?
哲學之於人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本書以諸多面向探討哲學,從世界、存在、哲學與時代、人文精神、自我覺知、哲學的價值,用深入淺出的文字,帶大家思考哲學的相關議題,瞭解哲學本身就是生活。
作者提到現代人的信仰普遍失落,在商業化潮流席捲之下,影響了生活方式、精神生活、人際關係等。在此情形下,有精神追求的人往往感到困惑、苦悶、彷徨。而哲學一方面尋求信仰,另一方面又具有探索性質,深入瞭解,可能為處於困惑中的現代人提供適合自己的精神生活方式。
人為了生存,不得不注意實用,但如果停留於此,就與動物相去不遠。哲學關注的是人的精神生活,滿足的是人的精神需要,這恰恰體現了人的神性。而每個人需要哲學的程度,或說與哲學之關係密切的程度,則取決於他對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
本書對人生的諸多省思,希望能帶領讀者回應來自靈魂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