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帶你進入一場惡夢,再讓惡夢成真
最可怕的是,你將永遠醒不過來……
「驚人的出道作,像生存實境秀遇上戈馬克‧麥卡錫的《長路》。」──《出版人週刊》(星級書評)
★Goodreads.com 年度最佳科幻小說
★《末日之旅》作者加斯汀.克羅寧震撼推薦
十二名參賽者,一場沒有終點的生存遊戲,誰能成為最後贏家?
結婚剛屆滿三年,正猶豫要不要和丈夫生個孩子。即將踏入30歲大關,她希望能在成為母親前,好好經歷一場冒險,找回挑戰人生的動力。因緣際會之下,她化名「動物主」加入電視台製作的「絕處求生」真人生存實境秀。一共十二名參賽者被送往森林,就此與外界斷了聯繫。
奔走在荒廢的城鎮、野獸出沒的叢林,「動物主」必須對抗飢餓、負傷和逐漸崩潰的精神狀態。同為競爭對手又是共度難關的夥伴,彼此爭吵、背叛,卻往往不得已必須相互扶持。
眼見賽果難以預料,「動物主」卻又不小心和其他參賽者走丟,落得孤身一人的窘境,正當失去方向時,她察覺到有一名神祕男子緊緊跟隨:他究竟是節目組派來的臥底?還是另有什麼神祕陰謀?當這場恐怖競賽逐漸失控,節目中虛擬的惡夢已悄悄蔓延到真實世界,動物主又該如何回到心愛的丈夫身邊?
以遊戲為名的真實人性考驗
即將揭露每個參賽者,不為人知的黑暗過去
作者簡介:
亞歷珊卓‧奧莉華
Alexandra Oliva
生於紐約,成長於紐約。耶魯大學歷史系畢業。之後獲得新學院創意寫作碩士學位。現與丈夫居於大西洋西北地區。《最後生還者》是她的第一本小說。
網站:http://www.alexandraoliva.com/the-last-one/
譯者簡介:
王欣欣
在台北出生長大,譯有《隔壁那對夫妻》、《列車上的女孩》、《穿著PRADA的惡魔》、《夢想之城》、《忽然一陣敲門聲》、《再讓我說個故事好不好》、《我絕非虛構的美好七年》等作品。
網站:www.xinxintalk.com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極具想像力。探索人類理智在承受壓力時的極限展現。一部善於擺弄人心的心理懸疑小說。」──《末日之旅》作者加斯汀.柯羅寧(Justin Cronin)
「神經緊繃,真實地幾乎讓人無法承受。《最後生還者》是欲罷不能的閱讀體驗,並且極為逼真地召喚出人們背水一戰的求生本能。」──《10號艙房的女人》作者露絲‧魏爾(Ruth Ware)
「亞歷山卓‧奧莉薇亞的小說像《飢餓遊戲》一樣,讓人緊張地不停往下翻。」─《親愛的妹妹》作者羅莎蒙‧盧普頓(Rosamund Lupton)
「緊張、動人,而且聰明得要命……每一刻我都喜愛。」──《我會回來找妳》作者羅倫‧布克斯(Lauren Beukes)
媒體推薦:
「最後一百多頁,讀者會不斷猜想動物主到底能不能回家。」──《華盛頓郵報》
「動物主是讓人不想放下《最後生還者》的原因,她實際、意志堅強、魅力十足。」──《衛報》
「奧莉薇亞的後末日設定,巧妙地將作品核心以實境節目串聯,給我們一個扣人心弦的生還故事。」──《西雅圖時報》
「驚人的首部小說,像生存實境秀遇上戈馬克‧麥卡錫的《長路》。」──《出版人週刊》(星級書評)
名人推薦:「極具想像力。探索人類理智在承受壓力時的極限展現。一部善於擺弄人心的心理懸疑小說。」──《末日之旅》作者加斯汀.柯羅寧(Justin Cronin)
「神經緊繃,真實地幾乎讓人無法承受。《最後生還者》是欲罷不能的閱讀體驗,並且極為逼真地召喚出人們背水一戰的求生本能。」──《10號艙房的女人》作者露絲‧魏爾(Ruth Ware)
「亞歷山卓‧奧莉薇亞的小說像《飢餓遊戲》一樣,讓人緊張地不停往下翻。」─《親愛的妹妹》作者羅莎蒙‧盧普頓(Rosamund Lupton)
「緊張、動人,而且聰明得要命……每一刻我都喜愛。」──《我會回...
章節試閱
0.
製作小組裡第一個死的會是剪接師,但他目前還沒覺得身體有什麼不舒服。他沒出外景,只在節目開拍前去看過那片樹林,跟攝影師握過手。傳染看不出症狀。回來一個多星期了,現在他一個人坐在剪接室裡,感覺非常好。T恤上寫著:喝咖啡,搞創意出。凌亂工作桌上的主角是一台三十二吋的螢幕,按一個鍵,影像就跳出來。
片頭,主要工作人員名單。鏡頭匆匆瞥過樹葉、橡樹和楓樹,緊接是一個女人,她在報名表上說自己的膚色是「摩卡」,挺貼切。她有深色的眼睛,橘色運動服幾乎包不住的豐滿胸部,一頭黑髮捲得恰到好處。
接下來是山區全景,這是美國東北風景甚美的一處,盛夏時分綠意盎然。一隻兔子作出衝刺前的預備動作。一個年輕的白人男子,剃得青青的頭在陽光下閃著雲母般的光澤,接著鏡頭拉近,拍下他嚴肅的表情和銳利的藍眼睛。然後是一個嬌小的女子,帶著韓國口音,穿著藍格子襯衫,單膝跪地,拿著一把刀,眼望地下。在她身後有個禿頭的高個子,暗粉紅色皮膚,鬍渣看起來像一星期沒刮。鏡頭拉近。那女人正在剝兔皮。隨後另一個定格畫面,剛剛那個深膚色男人在這個畫面裡沒了鬍渣,棕黑色的眼睛正視攝影機,冷靜而有自信,表情彷彿在說:「我一定要贏」。
河。懸崖。灰色崖面上青苔點點。另一個白種男人,留著狂野的紅髮,緊抓崖壁。攝影師用調焦技巧隱去了綁在他身上的繩索,讓安全繩索看起來像一道鮭魚色的水痕。
下一個畫面定格在膚色髮色都淺的女子身上,棕色方框眼鏡後的綠眼睛很亮。不知道是因為她的笑容,還是因為她眼光避開攝影機的方式,總之剪接師很喜歡她,覺得比其他參賽者真誠。也許只是她比較會裝,但就算是這樣,他還是喜歡,他喜歡她,因為他也會假裝。節目至今拍攝了十天,他認為最佳人氣獎一定是她的,她是愛動物的金髮美女,也是求知若渴的學生,學習快又愛笑,有太多角度可以切入。要是他可以自己作主就好了。
剪接室門打開,一個高個子白人大步走進來,是節目製作人。他走到剪接師身後,湊過去看螢幕,剪接師全身都僵了起來。
製作人問:「你把動物主排在哪裡?」
「追蹤者後面,牧場主前面。」
製作人若有所思點點頭,退開一步。他穿著筆挺的藍襯衫,打著有圓點的黃領帶,以及牛仔褲。剪接師跟他皮膚一樣白,不過假如有太陽可曬就會變黑。剪接師的血統有點複雜,從小到大,一直不知道人種選項該怎麼選,上一次人口普查他選的是白種人。
製作人問:「那空軍佬呢?有沒有加上旗幟?」
剪接師轉過身來,背對螢幕,螢幕的光把黑頭髮照得像鋸齒狀的光環。「 你不是認真的吧?」
「非常認真。」製作人說。「最後面是誰?」
「還是木工妹,可是……」
「你得把她往前調。」
剪接師被打斷前要說的話就是「我會把她往前調」。為了重做片頭的參賽者介紹,他昨天的進度已經耽擱了,今天又要剪完本週最後一集,所以眼前肯定是漫漫長日,說不定還得加上漫漫長夜。他很不爽,轉回去面對螢幕。「我想把銀行家或黑醫生放到最後面去。」
「銀行家。」製作人說。「相信我。」他頓了一下,又問:「昨天的帶子你看了沒?」
一週三集,幾乎沒有什麼前置時間,跟直播差不多了。剪接師心想,這怎麼撐得下去。「只看了開頭半小時。」
製作人笑了,整齊的牙齒讓螢幕的光照得發黃。他說:「 我們挖到寶了。女侍者、動物主,還有,呃……」他彈彈指頭,想喚醒記憶,「牧場主。他們沒在時限內完成任務,而且看見……」他在空中比出兩個引號,「『屍體』的時候女侍者大抓狂,哭到喘不過氣。然後,動物主就兇她。」
剪接師不安地挪了挪位置,問:「動物主退賽了嗎?」他好失望,臉熱起來,他很期待能剪她勝利的片段,或是在總決賽中優雅落敗也行。她得亞軍的可能性比較高,因為追蹤者太強了。空軍佬腳踝受傷,影響戰力,但追蹤者非常穩定,知識豐富,身體強壯,看起來註定獲勝。剪接師的工作是要讓追蹤者的勝利看起來沒那麼理所當然,他打算以動物主為主要工具來達成任務。他喜歡剪他倆在一起的片段,用對比來創造藝術。
「不,她沒退賽。」製作人拍拍剪接師的肩膀。「但她表現得很刻薄。」
剪接師望向螢幕上溫柔的動物主,那雙綠眼睛裡滿是善意。他不喜歡這種轉折,轉得太硬,不自然。
製作人又說:「她朝女侍者吼,怪她害他們輸,有夠好看。雖然沒多久就道歉,可那又怎樣,沒用啦。你看了就知道。」
剪接師心想,再好的人也難免有崩潰的時候,畢竟本節目就是基於這個想法做出來的……要突破參賽者的心防。雖說這十二個人報名時以為重點在於求生,在於比賽,但那只是節目的一部份而已。他們連真正的節目名稱都不知道。他們以為這節目叫做《林中求生》(In The Woods),其實是《絕處求生》(In The Dark)。
「總之,重做的片頭得在中午前做好。」製作人說。
剪接師說:「我知道。」
「好,我只是要確認一下。」製作人彎起手指作出手槍狀,朝剪接師一射,轉身要走,卻又停下來,看了看螢幕。螢幕正要進入省電狀態,略微變暗,但動物主的臉隱約可見。「你看她,還在笑呢,真可憐,搞不清楚狀況。」他笑著走出門去,笑聲裡有憐憫也有開心。
剪接師轉回去面對電腦,動動滑鼠,讓動物主微笑的臉亮回來。在片頭名單剪完之前,他就會開始疲倦想睡,全身無力。明天凌晨,剪完本週最後一集,他會開始咳嗽。到了晚上,他會成為一個早期的感染者,疫情大爆發前的重要患者。專家會努力研究,可惜時間不夠。無論這病毒是什麼,它發動攻勢之前會先潛伏一會兒,先假裝隨和搭便車,然後突然掌握方向盤,駕車衝向懸崖。許多專家自己也染病。
製作人也會死,就在今天的五天之後。發作時,他會一個人在四千一百平方呎的家裡,奄奄一息,無人理會。垂死之際,他會無意識地舔自己鼻子流出來的血,因為嘴實在太乾了。那時候,首播週的三集都已播完,最後一集讓觀眾在突發事件的新聞快報間得到一點喘息,因為看這節目可以開心,不用思考。拍攝小組困在疫情最早也最猛烈的地區,動彈不得。製作單位雖想把每一個人都救出來,可是參賽者正在進行個人賽,分散得太開。原本的應變措施格局太小,在這種狀況下顧不週全。這就好像小孩子玩的萬花尺,筆隨著塑膠片走,會畫出一定的圖案,可是一旦滑開軌道,就亂了。能力不足加上驚慌失措,以致於大家都顧不得別人,只忙著自保。誰都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更不知道大環境會怎樣。誰都不知道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製作人死去之前,頂多就只知道:不對勁,出事了。
1.
小超市的門還在門框上,可是已經壞了,好像是被打爛的。我小心翼翼走進去,知道自己不是第一個來這裡覓食的人。一進門的地方,有盒雞蛋倒在地上,一打矮胖子(Humpty Dumptys)。碎得永遠拼不回原狀。店裡其他的東西也好不到哪裡去,貨架大多空了,剩下的也都東倒西歪。天花板角落有攝影機,我不看鏡頭,繼續往前走。一股臭味撲鼻而來,是腐敗的農產品、灑出來的奶製品、和沒電的冰箱。我還聞出另一種臭,但我專心覓食,盡力不去想它。
有包玉米片撒在兩條走道中間,有人一腳把本應成堆的玉米片踩成了碎屑,腳印很大,腳跟很明顯,是工作靴。應該是男人的。不是庫柏,他說他好幾年沒穿靴子了。有可能是胡立歐,我蹲下去拾起一片,如果還很新鮮,就表示他剛走沒多久。我用手指捏碎玉米片。變味了。這條線索沒有用。
我有點想吃它。小木屋之後我一直沒吃東西,生病之後就沒吃過,好幾天,甚至一星期了。我好餓,餓到沒了餓的感覺,餓到無法完全控制我的腿,一直絆到石頭和樹根。明明看見了,卻避不開。明明是要跨過去,腳趾頭卻硬是要撞上去,害我跌倒。
可是這裡有攝影機,我先生會看見我撿超市地上的玉米片吃。不值得。他們一定有準備別的。我扔下手裡的玉米片,努力站起來,這動作讓我頭暈。我停頓一下,抓到平衡,然後走過農產品的攤子。攤子上有幾十根爛掉的香蕉和疑似蘋果的棕色乾癟球狀物,看著我走過去。他們為營造氣氛,蹧蹋這麼多食物,讓深陷饑餓的我非常憤怒。
終於,底層架子的下面有東西閃了一下。我趴下去看,繫在頸上的指北針垂下去碰到了地板。我把它塞進外衣和運動內衣之間,發覺指北針上的藍點給磨到快看不見了。我好累,我得提醒自己這無所謂,只不過表示負責塗顏色的工讀生拿到的是便宜顏料。我壓低身子,看見架子底下躺著一罐花生醬。有道裂痕從瓶蓋延伸到標籤,消失在「有機」的「有」後面。我摸了摸瓶身上的裂痕,摸不出裂掉的感覺。他們留的居然是花生醬,我討厭花生醬。我把花生醬收進背包。
店裡的直立式冰櫃空了,只剩幾罐啤酒,我不喝啤酒。我想要的是水。身上的兩個運動水壺,一個空了,另一個只剩四分之一。也許有幾個人比我先到,他們沒忘記把「所有」水都燒開,沒有浪費好幾天的時間在林中嘔吐。無論留下腳印的是誰,無論是胡立歐、艾略特或是那個我不記得名字的亞洲宅男,總之他把好東西拿走了,只剩這個:瓶身有裂痕的花生醬。
整家店只有一個地方我還沒搜過,就是收銀台後面。我知道那裡有什麼等著我。我不想承認自己聞到了那股味道:腐肉加上動物糞便,還有一點甲醛。他們想讓我以為那是死人。
我用衣服摀住鼻子,走到收銀台旁邊。他們的道具屍體果然就在那裡,仰躺在收銀台後面。他們給這假人穿的是法蘭絨襯衫和工作褲。我隔著衣服呼吸,走到櫃檯後面,跨過屍體,這動作惹飛了一堆蒼蠅。這群蒼蠅的腳、翅膀和觸鬚碰到我的皮膚,我心跳加速,呼出的氣在眼鏡下緣形成一片霧。
只是又一場比賽而已,如此而已。
我看見地上有一包綜合口糧,抓起來就走,穿過蒼蠅群,跨過道具屍,走出壞掉的門。那門還發出嘎嘎聲,像在為我喝倒采。
我低聲罵:「幹。」雙手撐膝,閉上眼睛。髒話大概得剪掉,可是又怎樣,叫他們去死吧,罵髒話並不犯規。
我感覺有風,可是聞不到樹林的味道,鼻子裡全是道具屍體的臭味。第一具沒這麼臭,因為比較新鮮;小木屋和這次的都很臭,大概是想做成死了很久的樣子。我擤擤鼻子,心知這臭味至少會跟我好幾個小時。無論身體多麼需要卡路里,我都沒辦法在這味道散去之前吃東西。
我得繼續向前,跟這地方拉開距離。我對自己說,趕緊找水。可是腦子裡一直戳我的是另一個念頭:小木屋和屋裡的第二個道具屍體,裹在藍布裡的娃娃。那是個人賽階段的第一場比賽,現在已經像膠似的黏在我的意識裡,揮之不去了。
我對自己說,別去想它。沒有用。接下來好幾分鐘我還是在風中聽見那娃娃的哭聲。然後,夠了,我打開我的黑背包,把綜合口糧放進去,背起背包,用外套裡面超細纖維長袖T恤的袖子把眼鏡擦乾淨。
接下來就做我在小袋鼠離開後幾乎天天做的事:邊走邊找線索。我叫他小袋鼠,因為沒有一個攝影師會把名字告訴我們,而他每天清晨出現,讓我想起多年前在澳洲露營的事。那次露營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傑維斯灣旁的國家公園醒來,看見一隻灰棕色沼澤袋鼠坐在草地上,目不轉睛看著我,跟我距離不到五呎。那天我睡前沒卸隱形眼鏡,醒來眼睛很癢,但我清楚看見那隻小袋鼠臉頰上那道淺色的毛。牠好美。我對牠投以讚嘆的眼光,牠回我的卻是冷冷的打量,就像攝影機的鏡頭一樣。
他們當然不是非常像啦,人類的小袋鼠遠不如真的動物好看,而且剛起床的露營客看到他大喊:「袋鼠!」也不會把他嚇跑。但是小袋鼠攝影師總是最早到,最早把攝影機對準我的臉,而且不會說早安。他們把我們丟在團體營地時,也是他回來幫我們拍告解片段。他就像日出一樣可靠。可是個人賽到了第三天,太陽出來了,他沒有出現;太陽下山了,他還是沒來。
於是我心想,這一天終於來了。合約上說,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會受遠程監控,看不到攝影機。當時我早有心理準備,甚至有點期待,覺得明著拍不如暗著拍好。可是現在,我卻好希望小袋鼠從樹林裡走出來。
我不想再孤單一個人。
夏末午後的時光幽幽流逝。在我身邊的聲音很有層次:有我走路的聲音、啄木鳥啄樹的聲音,風吹樹葉的聲音。偶爾還有另一隻鳥加入,甜甜唱著:去,去,去,去皮,去。啄木鳥的聲音很好認,但這第二隻鳥就不知道是什麼了。我想象這鳥的樣子,來轉移對口渴的注意力。
應該體型很小,羽色鮮亮吧。我幻想出一隻不存在的鳥:比我拳頭小,鮮黃色的翅膀,藍色的頭和尾巴,腹部有餘燼似的圖案。當然,牠是公的,換作母鳥,就不會這麼鮮豔,而會是棕色的。鳥類通常都這樣。
這隻餘燼鳥唱完最後一聲,沉默下來,合聲少了牠,變得好單薄。口渴捲土重來,十分強烈,太陽穴都因為脫水而開始陣痛。我拿起運動水壺,它好輕,繫在瓶口的藍色方巾乾乾硬硬的。我知道我的身體不喝水也能撐好幾天,但嘴這麼乾太難受。我小心翼翼喝了一口,舔舔嘴唇,不放過半點殘餘的水氣。我舔到血的味道,用手一擦,大拇指沾上了一抹血。原來上唇裂了,不曉得裂多久了。
找水是當務之急。我已經走好幾小時了吧,現在的影子比剛離開超市時長了好多。路上經過幾間房子,可是沒有商店,也沒有標著藍色的東西。我還是聞得到假屍體的味道。
走路的時候,我一直試著去踩影子的膝蓋。那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用來轉移注意力。結果轉移得太成功,以致於經過信箱的時候差點錯過。這信箱做成了鱒魚的形狀,門牌號碼是彩色的木頭魚鱗。信箱旁邊是長長車道的入口,車道彎彎曲曲,兩旁有許多白色的橡樹和幾棵樺樹,我看不見房子,但它肯定存在,在車道盡頭。
我不想去。自從那幾個藍氣球帶我走進小木屋之後,我再也沒進過住宅。那屋子裡面也有好多藍色,燈光黯淡,有一隻泰迪熊盯著我看。
我辦不到。
妳需要水。他們不會重複使用同一個技倆。
我走上車道。每一步都沉重,踉踉蹌蹌。我的影子在右邊,我走過樹旁它就在樹幹上爬呀跳的,靈敏得很,和我相反。
很快我就看見一棟怪獸似的都鐸式建築,灰白色外牆極需重漆,四周雜草叢生,正是小時候我會當作鬼屋的那種地方。一輛紅色休旅車停在外面,擋在我視線和大門之間。我徒步太久,這輛休旅車簡直像是另一個世界的東西。他們說不許開車,而且這車不是藍色的,但它擺在這裡或許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我慢慢走向車子,也就是說,走向那房子。也許他們把水放在後車廂,那我就不用進屋了。休旅車上濺了泥,已經乾了,卻仍然堅持呈現之前液體的形狀,依然不是塵土,而是泥乾。它看起來像墨跡測驗,但我看不出任何東西。
去,去,去,去皮,去。我聽見鳥叫。
我的餘燼鳥回來了。我伸長脖子,想聽出牠在哪個方向,卻因此發覺了另一個聲音:潺潺流水。我鬆了好大一口氣,不用進屋了。信箱只是要引領我到溪邊而已。我本該自己聽見的,可是我太累又太渴,多虧鳥兒帶我把注意力從視覺轉到聽覺。我轉身循聲去找活水。那隻鳥又叫了一聲,我用唇語說「謝謝」,乾裂的嘴唇一陣刺痛。
返回原路找那條溪的時候,我想起媽媽,她也會認為我一定找得到線索。不過在她看來,指引並非來自製作人。我彷彿看見她坐在客廳裡抽菸,煙霧繚繞。我彷彿看見她在看電視,將我所有的成功詮釋為信仰的見證,而每一次失望則都是教訓。她總將我的經驗收編,當作是自己的,因為若沒有她就不會有我,而對她來說,這就夠了。
我也想起爸爸,在我們家旁邊的麵包店裡,拿試吃品和鄉下人的幽默招徠觀光客買麵包,企圖暫時忘記結褵三十年來渾身菸味的妻子。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正看著電視裡的我。
小溪出現了,就在車道東邊不遠處,非常小的溪。我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轉過去,心跳得好快,好想立刻用雙手捧那冰涼的水潤潤嘴唇。但我沒這麼做。我先把運動水壺裡的溫水喝掉……大約有半杯吧。或許我應該早點喝的,有些人為了省水搞到脫水而死。但那是在別的地方,在那種陽光能讓人脫皮的地方,不是這裡。
喝水後,我沿著溪往下游走,看看有沒有動物屍體之類的東西,不想再生一次病了。我慢慢走了大約十分鐘,盡可能讓自己離那屋子遠一點,然後在離溪二十呎的地方找到一塊空地,空地邊上倒著一棵樹。接下來的流程我都習慣了,先清出一塊地方來堆木頭。我把木頭分成四堆,比鉛筆細的放在最左邊,比手腕粗的放在最右邊。收集到夠燒幾小時的木頭,就挑出幾片乾燥的樺樹皮,削成火絨,放在一片堅固的樹皮上。
我從腰間扣環上解下打火棒,讓它落在曬傷長繭的髒手上。這組打火棒長得有點像是鑰匙和隨身碟被橘色的線串在一起。剛拿到的時候我真這麼想。那是第一天,第一場比賽後。我拿到它一半靠技巧,一半靠運氣。當時攝影機一直都在,一切都很刺激,一點都不無聊。
打火棒敲幾下,火絨就冒煙。我把火絨護在手裡吹,直到吹出火苗,然後把打火棒扣回原處,用雙手捧著火絨放到我的營地中央,添加更多火絨,把火燒旺。濃煙撲鼻。我先放上最細的樹枝,再放粗的,不到幾分鐘火就生好了。也許在鏡頭下它看起來不怎麼厲害,火燄只有一呎高,可是對我而言這就夠了,火不用大,夠熱就好。
我拿出背包裡的不鏽鋼杯,它有凹痕,還有點焦,可是依然堅固好用。我用它燒水,同時逼自己用手指頭挖一點花生醬來吃。這麼久沒進食,我以為再討厭的食物也會變得美味,可是它好難吃,很稠很鹹,黏在上顎,得用乾乾的舌頭硬舔下來。我想我這樣子一定很蠢,蠢得像狗。真後悔,填資料的時候應該假裝對花生過敏,那他們就不得不留別的東西給我。可是說不定他們會因此刪掉我,不選我參賽。假如沒選上,這時候我會在哪裡呢?現在真沒腦子想那麼多。
終於,水開了。我讓它再燒幾分鐘,讓微生物死光光,才用破破的外套袖子當隔熱手套,把鋼杯從火邊移開。水不滾了以後,我把開水倒進運動水壺,裝到三分之一的地方。
第二杯煮起來就快了。煮三杯正好一壺。我把水壺蓋緊,放進溪裡降溫。繫在壺上的藍色方巾隨波搖曳。第二壺裝滿,第一壺也就涼得差不多了。我讓杯子繼續煮水,拿起放涼的水壺喝了四盎司,把殘餘的花生醬沖下喉嚨,等幾分鐘,再喝四盎司,就這樣,分次把整壺水喝光。杯裡的水又滾了。我覺得腦膜補到水了,頭痛消退。這一切也許沒有必要,溪水很清,流動很快,直接喝說不定沒有問題。可是我不想冒險,因為上次就錯了。
兩個水壺都裝滿,我才想到還沒搭睡覺的窩,雲層很厚,好像要下雨,天色已暗,恐怕時間不多。腰痠背痛的我勉強站起來,從木頭堆裡挑出五根粗枝,由長到短,併攏靠在倒地的樹背風那一面,做出三角形的骨架,入口寬度僅夠我鑽進去。我從背包裡拿出一個黑色垃圾袋,這是泰勒的臨別禮物,我沒想到他會給我,但很感激。我把它攤開,蓋住骨架,然後抱一些落葉鋪在上面,腦子裡想到了求生要優先注意的事。
我聽說過三的法則。心態如果不好,可能三秒鐘就沒命;窒息死亡要三分鐘;暴露在寒冷中,只能活三小時;沒水喝的話,三天;餓死要三星期……還是三個月?不管,反正餓死是我最不需要擔心的事。雖然覺得虛弱,但我沒餓那麼久,頂多六、七天沒吃飯吧,頂多。至於寒冷,就算今晚下雨,也不會凍死我;就算沒有擋風遮雨的窩,我也只會濕濕慘慘,不至於有生命危險。
但我不想濕漉漉的,而且他們的手筆再大,也不可能在我窩裡裝攝影機,因為這是無中生有,剛剛搭出來的。我不斷抱起落葉往上堆,突然有隻狼蛛爬上袖子,嚇得我往後縮,動作太猛,頭好暈,有點靈魂出竅的感覺。這隻蜘蛛攀住我的二頭肌,我用另一隻手把牠彈開,看著他掉進窩旁的落葉堆上,鑽了進去。我發現我根本不在意,因為牠的毒還算溫和。手上的工作我沒有停,很快的,窩上堆了一呎厚的葉子,窩裡墊的更多。
我用一些帶著分支的枝葉壓在屋頂上,免得剛鋪好的葉子散落,然後轉身去顧火,火快滅了。我今晚有點魂不守舍,是那房子的緣故吧,我想我還有點驚魂未定。我一邊添柴,一邊審視剛搭好的窩。它矮矮的,亂亂的,看起來很隨便,到處都有岔出來的小樹枝。我以前總是小心翼翼慢慢搭窩,想要做得跟庫柏和艾咪一樣漂亮,現在卻只考慮功能性。不過說真的,這種窩看起來都差不多,唯一的例外是艾咪離開前大家合力建造的那一個。那是一間美麗的單坡屋,屋頂的樹枝密密交織,就像茅屋的屋頂似的,而且很大,容得下全部的人。蘭迪是自己不肯進來睡的。
我又喝了幾盎司水,坐在復燃的火邊,太陽已逝,月亮未明,火光搖曳,我右眼鏡片上髒了一塊,望出去有種光芒四射的效果。
又是一個獨處的夜。
0.
製作小組裡第一個死的會是剪接師,但他目前還沒覺得身體有什麼不舒服。他沒出外景,只在節目開拍前去看過那片樹林,跟攝影師握過手。傳染看不出症狀。回來一個多星期了,現在他一個人坐在剪接室裡,感覺非常好。T恤上寫著:喝咖啡,搞創意出。凌亂工作桌上的主角是一台三十二吋的螢幕,按一個鍵,影像就跳出來。
片頭,主要工作人員名單。鏡頭匆匆瞥過樹葉、橡樹和楓樹,緊接是一個女人,她在報名表上說自己的膚色是「摩卡」,挺貼切。她有深色的眼睛,橘色運動服幾乎包不住的豐滿胸部,一頭黑髮捲得恰到好處。
接下來是山區全景,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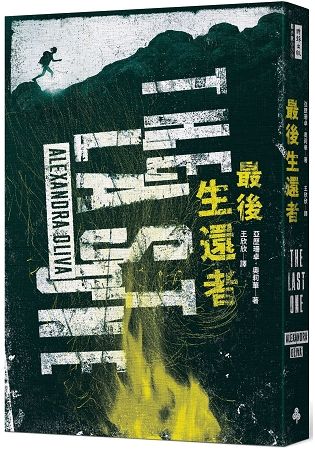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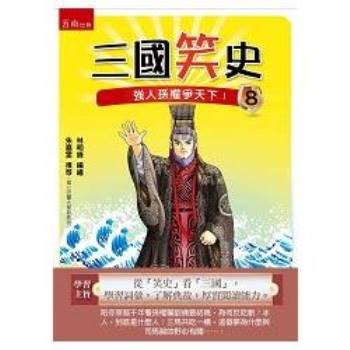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