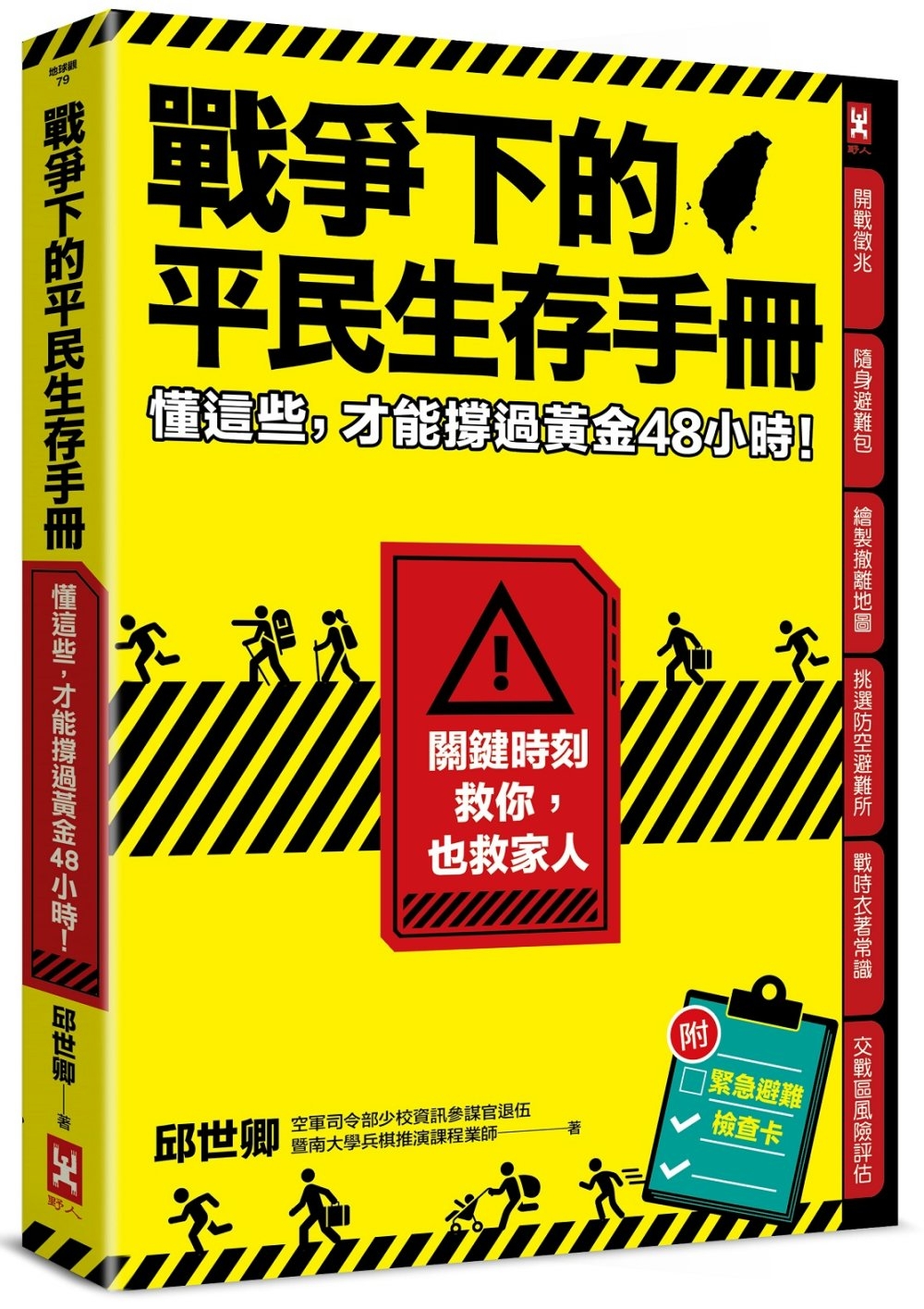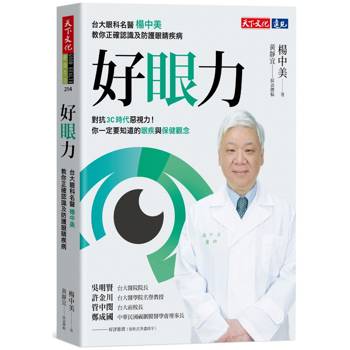白石一文詰問成人世代生存意義的長篇小說
直透成人心中難以言說的孤單與寂寞
直透成人心中難以言說的孤單與寂寞
給孤獨無依 孓然一生的大人們。
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其意義,難道沒有相互扶持的親人伴侶,人生就無法重新開始,也沒有辦法走自己的路。
其實每個人都是孤獨的。
不管是什麼樣的人,內心中央都是個空洞,
我總覺得,從中吹拂而過的一定是寂寞的風。
我們內心還是懷抱絕對性的孤獨,
無論與任何對象之間發生了什麼事,獲得何種救贖,
那孤獨也絕無痊癒的一天。
吹過人心中央空洞的寂寞之風。
我能明確感受到那陣風帶來的觸感。
看白石一文筆下最寂寞孤單的男人 高梨修一郎
如何在層層疊疊的窘境中,找尋生命的出口。
高梨修一郎自幼父母感情不睦,自父親偕同女友消失無蹤後,便隨著母親與妹妹篤子一同生活。某年元旦妹妹外出前往郵寄賀年卡的途中,不慎被德本京介的座車撞上,縱使無性命之憂,卻因此落下腿部的殘疾,而修一郎此生與德本興業的緣分羈絆與美千代母女間難以割捨的情感糾結自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