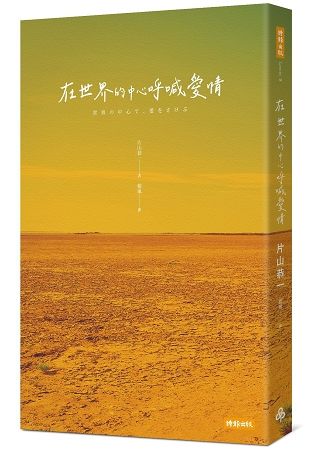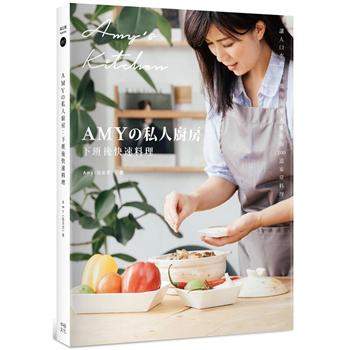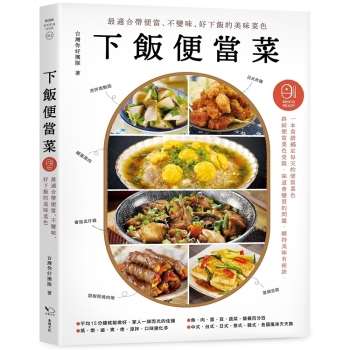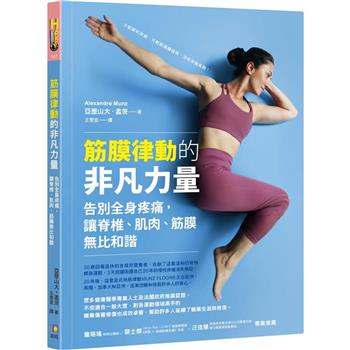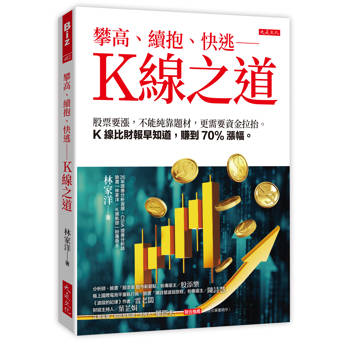日本純愛小說經典 三百五十萬銷售記錄
清新雋永的不朽青春物語
清新雋永的不朽青春物語
「時間的長短真的這麼重要嗎?」
和小朔在一起的時間,雖然短暫卻很幸福,我想再也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事了。我想自己一定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幸福吧!就連現在這一瞬間……這樣就夠了。記得我們不是說過嗎?現在存在於此的東西,就算死了之後也會永遠存在啊!─廣瀨亞紀
深深思念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不知不覺活在這世界的中心。
朔太郎為了幫助爺爺彌補年少時的遺憾,一同前去盜墓,只為了偷取爺爺初戀情人的骨灰。爺爺此生最大的盼望便是在百年之後,戀人終有機會再度重逢聚首。歉疚與遺憾,始終是爺爺一直以來心中長久以來難以抹滅彌補的傷痛。
而初中時自己投稿電台的惡作劇無意間竟也成了一個應驗的詛咒。多年之後,當面臨與爺爺相同的處境時,朔太郎該如何割捨這握在掌心的玻璃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