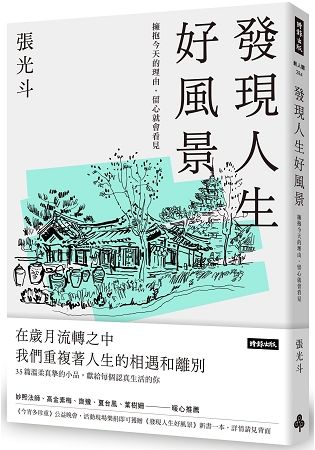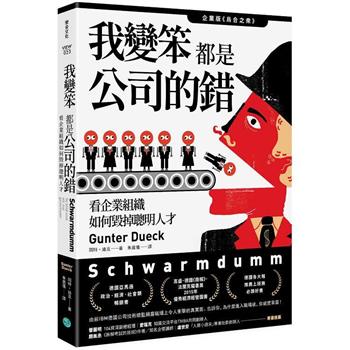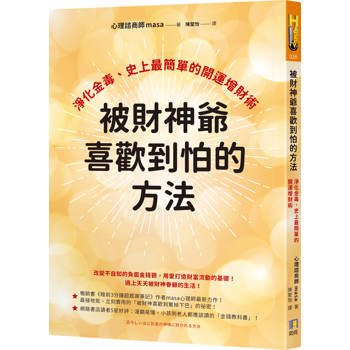圖書名稱:發現人生好風景
在歲月流轉之中,我們重複著人生的相遇和離別。當彼此的緣分交會,在最剛好的時光互相陪伴,是這樣的溫暖讓我們相信,漫漫長路之後終會遇見動人的風景。
人間的悲歡離合,終將在心裡映成最美好的風景
人與人之間的回憶甘美而動人,如同生命在我們身上留下的每一道年輪。
這些人事今非,透過他溫柔真摯的筆,活躍在你我眼前,成為我們記憶中難以忘懷的人生風景。記得曾經與自己相遇的人、記得那些如煙的往事,是因為這一切造就了此刻的我們。即使今宵難聚首,仍可以期待他日再相逢。
寫給每個認真生活的你
從1994年開播至今,《點燈》節目已經走過25個年頭,是臺灣最長壽的談話報導型節目。25年來《點燈》紀錄了市井小民的生活樣態。從對人及對土地與社會的感恩為出發點,《點燈》持續以良善、正向的信念,讓每個人在黑暗中,仍能感受到社會的溫暖與希望。
這次,《點燈》製作人張光斗,用他的一片赤誠,刻劃警消人員與生命搏鬥的光輝與征途。他質樸溫暖、筆下有情,除了向警消人員表達敬重與感謝之外,更將他對親友的思念、面對人生無常的幽思寄情於35篇小品裡,舉重若輕,感人肺腑。
用溫柔的守候消融悲傷,給你一個最寬厚的擁抱
在和煦的燈火中,帶你品嘗人情冷暖與生命況味
作者簡介
張光斗
祖籍安徽滁縣,父親是老兵。1953年出生在臺灣彰化縣北斗鎮的一個平日的清晨;父親不期待他能光中、光華,只要把小小的北斗鎮照亮即可,故名光斗。
曾任職電視臺劇務、記者、駐外特派員、編劇、製作人。
1994年製作訪談性電視節目《點燈》後,因緣際會親近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人生道路因而有了巨幅的改變。
《點燈》節目歷經臺灣社會的變動,最終不被電視臺的主流價值接納;他自《點燈》第十一年開始,先後成立協會與基金會,執著於維護這盞照亮臺灣社會正能量的燈火,長明不滅;至今剛好二十五個年頭。
他製作的節目雖然獲得好評,個人也得過「東元人文獎」、「世新傑出校友獎」等,但還是希望能低調地寫寫專欄,做好《點燈》節目與相關社會活動,便得以坐擁人生最美好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