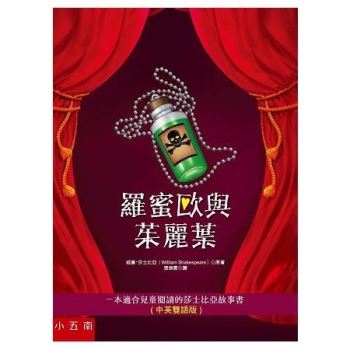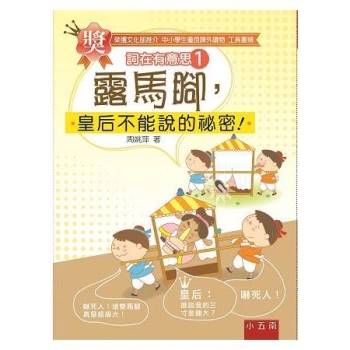圖書名稱:紅色城堡
這是一場看似再正常也不過的法國之旅。但其實我早已設下陷阱僱人綁架妻子,讓她進入一座位在森林深處的神祕城堡裡接受他人的性調教。
結婚三年來,妻子始終拒絕我的求歡,對性這件事表現得十分厭惡。──我被拒絕了,我的妻子打從心裡瞧不起出身貧窮人家的我,連帶著極為嫌棄我赤裸的身體,覺得我根本配不上她美麗的軀體、聰明的頭腦、優秀的家世!
城堡中的石室裡,窗帘開啟之後,在被石牆隔開的窗戶那邊,可以看到一個女性赤條條地站在燈火通明的房間裡,她伸開手腳,站成大字型,下腹部至胯股間被微微往前推挺。定睛一瞧,她的手腕還連結著從天花板而下的鎖鍊,兩腳被釘入地板的鐵環扣住。那是我神聖不可侵犯的妻子。
接著進來了幾個男人,他們開始對妻子上下其手。「住手啊!」我的心裡大聲喊著,但我的陰莖卻不自覺地猛然勃起了……
作者簡介
渡邊淳一(1933年10月24日-2014年4月30日)
日本作家。出生於北海道上砂川町,畢業於札幌醫科大學,曾任骨科醫生。後棄醫從事專業文學創作,以小說《光和影》獲直木文學獎,接著又以《遙遠的落日》獲吉川英治獎。2003年獲日本政府頒發「紫綬褒章」。2014年4月30日因前列腺癌在東京都家中去世,享年80歲。
1995年9月1日開始,在《日本經濟新聞》發表長篇連載小說《失樂園》,描寫不倫中的性愛,引起巨大反響,並相繼被拍成電視連續劇和電影,在日本掀起了「失樂園」熱。《失樂園》一書在日本暢銷超過三百萬冊。
渡邊淳一一貫堅持正面描寫愛與性,其作品甚至有時會被稱為情色小說,但這正是一位畢生探求生與死的作家所譜出的人間謳歌。因為渡邊一直探尋包括自己在內的「人性」,他才能將自己的體驗冷靜而透澈地注入作品之中。他始終對人類的本性充滿了好奇,並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小說的創作。
譯者簡介
邱振瑞
詩人、作家、日本文學翻譯家。現任文化大學中日筆譯班講師,著有《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蔚藍文化);詩集《抒情的彼方》(秀威)、《憂傷似海》(秀威)、《變奏的開端》(秀威);小說集《菩薩有難》(商周)、《來信》(允晨);譯作豐富,譯有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安部公房、松本清張、山崎豐子、宮本輝等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