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試圖扛起一切,到接受自己面對生命衰敗的無能為力;
從依附與壓抑,到活出真正的自己;
從渴望被人認可,到洞見自己的價值;
從永別親人,到彼此心靈相通,現實的永別反而成了內在的貼近;
用愛陪伴與被陪伴,不僅完整了自己,也有圓滿的人生。
❤最完美的陪伴是,在愛裡陪伴不完美的自己❤
在人生懸崖邊,
與另一位更接近實相的自己相遇,
並且以愛安在於陪伴與被陪伴的循環共生裡。
作者吳品瑜身為長年旅居國外的媳婦,回德國陪伴癌末的婆婆至往生。期間歷經各種自我的內在掙扎、與孩子的衝突、和婆婆的磨合、身為照顧者的心路歷程、漸漸明白被照顧者的心情……她最終領悟:
活著的美好不是物質世界的執持與擁有,
而是目睹了生命自然周序的律動與和諧,
更能踏實地在眼前這一刻,充分地活著、享受著、更覺知著,
並毫無抗拒地隨順滑入下一個階段。
她說:
在回首的長長黑暗甬道裡,
我與婆婆的身影交錯、故事重疊,
原來早在病榻邊的一線之間,
我已從照顧者翻轉成臨終者,
嘗試思索躺著的自己的所有想望與最後完成。
於是,「善終」成了活著的每一刻的在乎,
並且為自己許下一個夠好(good enough)的陪伴。
好評推薦
謝謝品瑜,把親身經歷轉化成為文字,提醒我們。透過品瑜的感官,邀請大家體驗完美照顧系統中的不完美,誠摯向各位推薦本書!——余尚儒∣都蘭診所所長、好家宅共生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好好說再見、好好道別很重要。品瑜與臨終婆婆的陪伴故事,給了我們最好的範本,原來,我們也可以這樣做。——周志建∣故事療癒作家、諮商心理師
這樣的空間讓這位臺灣媳婦得以跨越文化與世代的落差,靠近德國婆婆的生命經驗,成就一篇篇動人的故事。——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這本「德國臨終之旅」,一來讓我們學習,以改善臺灣「居家安寧療護」服務體系,再者是文化差異的磨合過程……我認為必須回到「安寧療護」強調的「尊重自主權與個別差異」去思考。——許禮安∣醫師、高雄市張啓華文化藝術基金會 執行長
| FindBook |
有 14 項符合
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臺灣女兒、德國媳婦的生命照顧現場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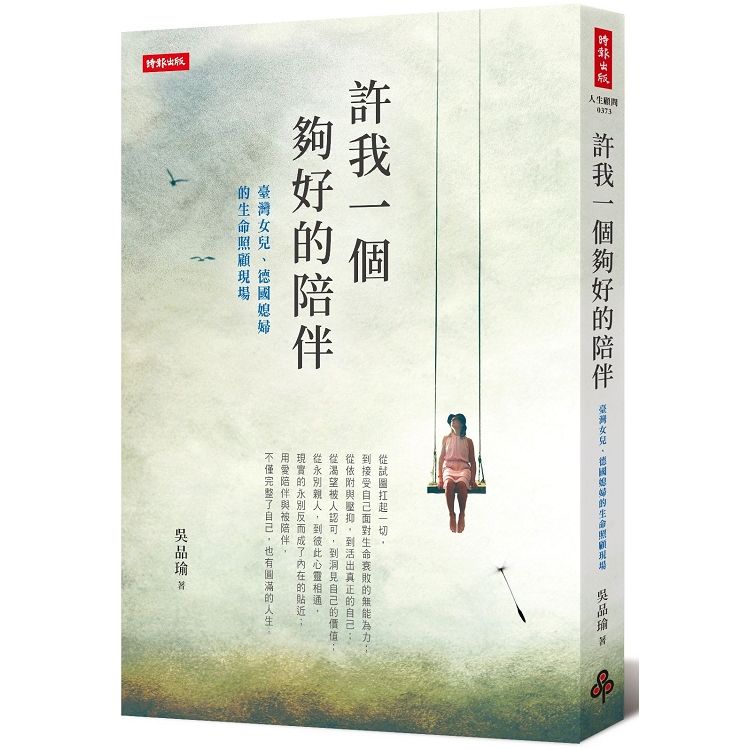 |
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臺灣女兒、德國媳婦的生命照顧現場 作者:吳品瑜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08-1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臺灣女兒、德國媳婦的生命照顧現場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吳品瑜
政大廣告、中正電傳所畢業,多倫多大學麥克魯漢中心研究,國際扶輪社駐加親善大使與訪問學人。
曾任職文化總會、天下雜誌與尼爾森行銷研究顧問公司。
城市光榮感極強的府城女兒,研究日治臺南仕紳史與臺語古典詩,也嘗試臺語書寫創作。熱愛榮格學說的童話分析,嗜好蒐集與分享「夠好(good enough)陪伴」的生命故事,並且積極實踐「愛的業力法則」,期盼每個人都能在愛與被愛的無限循環共生裡。
住遊加、英、德、中、馬二十年,目前與女兒們旅居德國海德堡,繼續學習「那些女兒教會我的事」,特別是與才六歲的小女兒紫晴共同成長歡樂,享受「半個阿嬤半個媽」的返老還童生活。
臉書FB: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
個人新聞台: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
Instagram:barbarakernwrites
吳品瑜
政大廣告、中正電傳所畢業,多倫多大學麥克魯漢中心研究,國際扶輪社駐加親善大使與訪問學人。
曾任職文化總會、天下雜誌與尼爾森行銷研究顧問公司。
城市光榮感極強的府城女兒,研究日治臺南仕紳史與臺語古典詩,也嘗試臺語書寫創作。熱愛榮格學說的童話分析,嗜好蒐集與分享「夠好(good enough)陪伴」的生命故事,並且積極實踐「愛的業力法則」,期盼每個人都能在愛與被愛的無限循環共生裡。
住遊加、英、德、中、馬二十年,目前與女兒們旅居德國海德堡,繼續學習「那些女兒教會我的事」,特別是與才六歲的小女兒紫晴共同成長歡樂,享受「半個阿嬤半個媽」的返老還童生活。
臉書FB: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
個人新聞台: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
Instagram:barbarakernwrites
目錄
推薦序∣找回臨終陪伴的文化 余尚儒
推薦序∣當生命走到盡頭,臨在陪伴最美 周志建
推薦序∣當臺灣媳婦遇到德國長照 王增勇
推薦序∣臨終是生命學習與靈性成長的最後階段 許禮安
自序
迎向自己
我所不知道的是,新生活的混亂不是眼下婆婆的癌症所引發,
而是我內在經年不知、無能或不願處理的生命課題——「自我」的混亂。
除了「媳婦」這個角色?或是還有更本然的「自我」?
一點點美味的恩寵
或許,身體感官逐漸崩壞,記憶裡的美好更勝食物本身,
因為真正的醍醐味緣由親密關係的陳釀,
那是美食享用當下的互動與人情,甚至是準備過程的愛與用心。
記憶裡的美食盛宴,才是永遠不散的身心靈享受。
重要的第三者:基福會的醫護人員
臨終病榻旁的重要第三者,
幫助的不僅僅是臨終者,還有家人與照顧者,
更在死亡催逼的短促時間裡,
打開了情感與生命的開闊空間。
誰該來病榻旁?
安寧陪伴最不需要他人「施展專業」與「盡義務」,
僅只需臨在病榻旁的一點點膚觸與溫度,
以及同理共感地在「陪跑」到終點之前,時光倒轉地將人生回憶一遍,
並於有聲或無聲的「重說」生命故事中再次「活著」,也就足夠了。
面對孩子的直言與真實
那一夜很長,卻也很騷動。
循著創傷的斑斑血跡,走回生命經驗的第一現場,
因為疼痛,卻也讓自我照看變得異常警醒與清晰。
「每一位最殘暴的成人背後,都有一位飽受恐懼與驚嚇的內在孩子。」
嘴角殘留的黑巧克力
這是一種生命的厚實感,此前未解的事件經歷,
既成了後來發生的緩衝墊,亦留下了追索的引子。
臨終病榻的陪伴經歷,成為我後來生命感縈繞反覆的起點,
伏藏的線索,預示著具有時空感的生命故事。
重新說出自己的故事
糾纏、折磨五十多年的羞「恥」,
就在她親口說出故事,也被自己耳朵聽見的那一刻,
反轉成一種自我認證生命韌性的驕傲與力量。
唯有凝視受苦的自己,才能升起對自己的最大慈悲。
指尖羅盤
臨終照顧的烽火線上,雖然壓縮了時間,創造了絕佳的空間,
讓我有機會嘗試承認自己不夠聰明、力有未逮,並且學習坦白與臣服。
雙手憑空放掌,並非什麼都不做了,
而是等待心的羅盤慢慢定位,等待頭腦意想之外的方向化顯。
照顧者更需要被照顧
身為「照顧者」也需要被照顧,
方能在被撫慰瞬間,復甦所有疲憊的身心,
繼而以敏受的感官,再次回應他人的需要;
擔任「陪伴者」更迫切被陪伴,因為情緒被牢牢接住,
才能踏實地接地氣,在每一時刻與人同理共感。
剪報圈成一只母愛的巢
婆婆向未知的死亡飛去,卻不是什麼都沒留下,
枯枝會散、老房會易主、崩壞,
但是那只用愛編織的巢,有了懂得的心安放其中,
就永遠有溫熱,她也永遠活在那顆心裡。
會說話的房子
我猜,婆婆的整間房子像只大海綿,
能將我們與孩子們的話語、笑聲與會心都滿載地吸附進去,
然後在我們離家的時候,婆婆的一枚想念,沉重如砝碼跌落在海綿上,
便能將這些聲音給擠了出來,繼續填充婆婆的耳朵。
讓孩子參與臨終陪伴
孩子參與臨終陪伴,不僅不是我的助手,
反而是現場演示,幫助我解構無意識的媳婦角色枷鎖。
而這一切都要等到我靜定,甚至是後來才懂,
了知這一切的安排,最終受惠的竟是自以為犧牲的我。
在死亡陰影中燦爛的美麗停格
世間最撕心裂肺,乃至最後的告別,
終究是自己的身體與靈魂。
然而若能帶著覺察,對慣常被我們無意識驅使的身體有更多的尊重與感恩,
並藉由平日一次次的停格與注視,分與合之間也就能如常。
為自己在紛亂人世留一點溫柔餘裕
我永遠會記得當時窗外橫衝直撞的車流,以及向內照看的迴視之眼,
提醒自己日後生活無論歲月靜好,或是多事之秋,
都別忘跟自己適時「喝一杯」,由外相的一切,反轉看見自己內在的情緒,
升起了接納自己的慈悲,也死去種種老舊心識與防衛。
臨終前的被愛滋味
鄉村蘋果派與節慶包餡甜甜圈,成了我女性生命的甜蜜隱喻,
在滋養她人之前,得先寵溺自己,這才是最美好正向的女性原則,
而給出的愛才能因為自愛的泉源,不虞匱乏。
蒲公英去旅行吧
活著的美好不是物質世界的執持與擁有,
而是目睹了生命自然周序的律動與和諧,
更能踏實地在眼前這一刻,充分地活著、享受著、更覺知著,
並毫無抗拒地隨順滑入下一個階段。
冷面醫生的慈悲
這一切在冷面醫生的退開,才得以成全,
透著光的明白瞬間,我突然紅了眼眶,感激起這位冷面醫生的慈悲,
教會我在臨終陪伴「空掉」心智自我,才能讓本真與存在相隨。
一朵熊媽媽白雲
她的「不在」卻成為了一份最溫柔堅實的「在」,
時刻提醒我成為自己!
懂得的幸福,儘管不是被給出那一瞬間的時鮮,
但時間的遲滯,卻讓幸福有了熟成的厚實香氣。
為愛遠行
婆婆生命的最後一個午後,我以情境劇的創想,
陪著她無邊叨絮,慢慢地等待虛幻的火車到來。
婆婆留下了生命最後月臺的優雅身影,一如她往生時面容淺淺的笑,
正是旅人帶著送行者的祝福,迎向未知的旅程。
先學會不為難自己
安寧,不難。只是我們得先學會不為難自己,
特別是將自己與「照顧者」這角色密緻綑綁,乃至徹底內化,
並且行為被制約在「掏空」與「出清」式的付出,
在面對身心注定趨疲與衰減時,面對的挑戰是遠大過於其他人的。
重說故事的馬鈴薯球
馬鈴薯球填飽了胃、安撫了飢餓,
而馬鈴薯球的象徵意義,則是療癒了無常生離死別的必然與痛楚。
我們繼續吃食、咀嚼,以及用創想給出新的意義與故事……。
許一段貝殼沙灘的柔軟
中年孤兒,失親的痛苦與療傷,
似乎比一般人來得更深長且晦暗無光。
為此,許一段貝殼沙灘的柔軟,
不僅是給往生者,亦是在世者的哀悼歷程,
允許自己走過,用最大的限度與慈悲。
凝視「理所當然」
這一切終究在婆婆過世之後,
孩子被無可言說的思親悲傷所牽引,
慢慢地反芻著「理所當然」的幸福,
甚而在疼痛與延遲的體會裡,
於生活中實踐「理所當然」的深邃感悟。
臨在,終點的起點
婆婆的往生開啟了我的內在告別式,思維著她的死,
照見了自己生命中慣性模式所造成的困局,雖生如死地殘喘活著。
人身難得,在世無常,死亡的震撼教會我
一一死去舊有的,一切如新便已開始。
你的臨終不能打亂我的節奏
善終,不僅僅是給予臨終的人,更是陪伴者的當下開始。
善終的企盼,不是帶著賭徒的僥倖心態,或者是虔誠教徒的執拗堅信,
卻是當下生命功課的開始。
後記
推薦序∣當生命走到盡頭,臨在陪伴最美 周志建
推薦序∣當臺灣媳婦遇到德國長照 王增勇
推薦序∣臨終是生命學習與靈性成長的最後階段 許禮安
自序
迎向自己
我所不知道的是,新生活的混亂不是眼下婆婆的癌症所引發,
而是我內在經年不知、無能或不願處理的生命課題——「自我」的混亂。
除了「媳婦」這個角色?或是還有更本然的「自我」?
一點點美味的恩寵
或許,身體感官逐漸崩壞,記憶裡的美好更勝食物本身,
因為真正的醍醐味緣由親密關係的陳釀,
那是美食享用當下的互動與人情,甚至是準備過程的愛與用心。
記憶裡的美食盛宴,才是永遠不散的身心靈享受。
重要的第三者:基福會的醫護人員
臨終病榻旁的重要第三者,
幫助的不僅僅是臨終者,還有家人與照顧者,
更在死亡催逼的短促時間裡,
打開了情感與生命的開闊空間。
誰該來病榻旁?
安寧陪伴最不需要他人「施展專業」與「盡義務」,
僅只需臨在病榻旁的一點點膚觸與溫度,
以及同理共感地在「陪跑」到終點之前,時光倒轉地將人生回憶一遍,
並於有聲或無聲的「重說」生命故事中再次「活著」,也就足夠了。
面對孩子的直言與真實
那一夜很長,卻也很騷動。
循著創傷的斑斑血跡,走回生命經驗的第一現場,
因為疼痛,卻也讓自我照看變得異常警醒與清晰。
「每一位最殘暴的成人背後,都有一位飽受恐懼與驚嚇的內在孩子。」
嘴角殘留的黑巧克力
這是一種生命的厚實感,此前未解的事件經歷,
既成了後來發生的緩衝墊,亦留下了追索的引子。
臨終病榻的陪伴經歷,成為我後來生命感縈繞反覆的起點,
伏藏的線索,預示著具有時空感的生命故事。
重新說出自己的故事
糾纏、折磨五十多年的羞「恥」,
就在她親口說出故事,也被自己耳朵聽見的那一刻,
反轉成一種自我認證生命韌性的驕傲與力量。
唯有凝視受苦的自己,才能升起對自己的最大慈悲。
指尖羅盤
臨終照顧的烽火線上,雖然壓縮了時間,創造了絕佳的空間,
讓我有機會嘗試承認自己不夠聰明、力有未逮,並且學習坦白與臣服。
雙手憑空放掌,並非什麼都不做了,
而是等待心的羅盤慢慢定位,等待頭腦意想之外的方向化顯。
照顧者更需要被照顧
身為「照顧者」也需要被照顧,
方能在被撫慰瞬間,復甦所有疲憊的身心,
繼而以敏受的感官,再次回應他人的需要;
擔任「陪伴者」更迫切被陪伴,因為情緒被牢牢接住,
才能踏實地接地氣,在每一時刻與人同理共感。
剪報圈成一只母愛的巢
婆婆向未知的死亡飛去,卻不是什麼都沒留下,
枯枝會散、老房會易主、崩壞,
但是那只用愛編織的巢,有了懂得的心安放其中,
就永遠有溫熱,她也永遠活在那顆心裡。
會說話的房子
我猜,婆婆的整間房子像只大海綿,
能將我們與孩子們的話語、笑聲與會心都滿載地吸附進去,
然後在我們離家的時候,婆婆的一枚想念,沉重如砝碼跌落在海綿上,
便能將這些聲音給擠了出來,繼續填充婆婆的耳朵。
讓孩子參與臨終陪伴
孩子參與臨終陪伴,不僅不是我的助手,
反而是現場演示,幫助我解構無意識的媳婦角色枷鎖。
而這一切都要等到我靜定,甚至是後來才懂,
了知這一切的安排,最終受惠的竟是自以為犧牲的我。
在死亡陰影中燦爛的美麗停格
世間最撕心裂肺,乃至最後的告別,
終究是自己的身體與靈魂。
然而若能帶著覺察,對慣常被我們無意識驅使的身體有更多的尊重與感恩,
並藉由平日一次次的停格與注視,分與合之間也就能如常。
為自己在紛亂人世留一點溫柔餘裕
我永遠會記得當時窗外橫衝直撞的車流,以及向內照看的迴視之眼,
提醒自己日後生活無論歲月靜好,或是多事之秋,
都別忘跟自己適時「喝一杯」,由外相的一切,反轉看見自己內在的情緒,
升起了接納自己的慈悲,也死去種種老舊心識與防衛。
臨終前的被愛滋味
鄉村蘋果派與節慶包餡甜甜圈,成了我女性生命的甜蜜隱喻,
在滋養她人之前,得先寵溺自己,這才是最美好正向的女性原則,
而給出的愛才能因為自愛的泉源,不虞匱乏。
蒲公英去旅行吧
活著的美好不是物質世界的執持與擁有,
而是目睹了生命自然周序的律動與和諧,
更能踏實地在眼前這一刻,充分地活著、享受著、更覺知著,
並毫無抗拒地隨順滑入下一個階段。
冷面醫生的慈悲
這一切在冷面醫生的退開,才得以成全,
透著光的明白瞬間,我突然紅了眼眶,感激起這位冷面醫生的慈悲,
教會我在臨終陪伴「空掉」心智自我,才能讓本真與存在相隨。
一朵熊媽媽白雲
她的「不在」卻成為了一份最溫柔堅實的「在」,
時刻提醒我成為自己!
懂得的幸福,儘管不是被給出那一瞬間的時鮮,
但時間的遲滯,卻讓幸福有了熟成的厚實香氣。
為愛遠行
婆婆生命的最後一個午後,我以情境劇的創想,
陪著她無邊叨絮,慢慢地等待虛幻的火車到來。
婆婆留下了生命最後月臺的優雅身影,一如她往生時面容淺淺的笑,
正是旅人帶著送行者的祝福,迎向未知的旅程。
先學會不為難自己
安寧,不難。只是我們得先學會不為難自己,
特別是將自己與「照顧者」這角色密緻綑綁,乃至徹底內化,
並且行為被制約在「掏空」與「出清」式的付出,
在面對身心注定趨疲與衰減時,面對的挑戰是遠大過於其他人的。
重說故事的馬鈴薯球
馬鈴薯球填飽了胃、安撫了飢餓,
而馬鈴薯球的象徵意義,則是療癒了無常生離死別的必然與痛楚。
我們繼續吃食、咀嚼,以及用創想給出新的意義與故事……。
許一段貝殼沙灘的柔軟
中年孤兒,失親的痛苦與療傷,
似乎比一般人來得更深長且晦暗無光。
為此,許一段貝殼沙灘的柔軟,
不僅是給往生者,亦是在世者的哀悼歷程,
允許自己走過,用最大的限度與慈悲。
凝視「理所當然」
這一切終究在婆婆過世之後,
孩子被無可言說的思親悲傷所牽引,
慢慢地反芻著「理所當然」的幸福,
甚而在疼痛與延遲的體會裡,
於生活中實踐「理所當然」的深邃感悟。
臨在,終點的起點
婆婆的往生開啟了我的內在告別式,思維著她的死,
照見了自己生命中慣性模式所造成的困局,雖生如死地殘喘活著。
人身難得,在世無常,死亡的震撼教會我
一一死去舊有的,一切如新便已開始。
你的臨終不能打亂我的節奏
善終,不僅僅是給予臨終的人,更是陪伴者的當下開始。
善終的企盼,不是帶著賭徒的僥倖心態,或者是虔誠教徒的執拗堅信,
卻是當下生命功課的開始。
後記
序
自序
二○一四年三月,從旅居五年半的上海,舉家搬遷到吉隆坡,三週後我獨自帶著三名孩子飛回德國照顧膀胱癌末期的寡居婆婆,直到往生。
在西南德山村的一棟五十多年老屋裡,終其一生照顧了五代人的八十四歲臨終德國老奶奶,再加上「自作主張」的臺灣媳婦,以及年齡各十四、十二與一歲半的「狀況外」混血孫女,還有至少六位輪班換值的「非政府」安寧體系照護員。
如此「拼湊」(patch)的雜牌軍在臨終病榻旁,究竟能有怎樣的故事演繹?
做為一名外籍媳婦,又是首次居家安寧照顧,技術生澀、對死亡全然陌生,以及不熟悉德國醫療體系的我,從在病榻旁就開始點滴記錄過程,包括德國醫護人員對我身分的質疑、婆婆執拗地抵抗他人在生活起居上的協助、女兒們與奶奶型態各異的互動、考量委請烏克蘭看護與否,到最後遺願的探詢與完成,甚至是否由「管」很大的維生系統介入的抉擇,以及「另類」善終的觀察。
過程中越是自覺不周到與錯誤的斷裂之處,越是成為後來追索答案的破口,甚至是補救學習的起點;越是感到沒有把握,以及自我懷疑的停頓處,就越是關聯自身陰暗面,等待多幾秒安忍恐懼的探照。
婆婆往生後,我接觸了更多生死學的書籍、講座,以及實際學習居家照顧技巧,甚至是這幾年許多生活的意外遭逢與發生,包括兩次急診住院,以及簽下放棄急救與器官、大體捐贈。因為每一次當下新的生命經驗,再持續回頭照看這段安寧照顧的經過,卻有了不同的理解,乃至更深化生命面向的探照。
彷彿是永遠走不完,又時時意義更新的歷程,但卻仍無法完全書寫出婆婆生命的豐厚感。
在回首的長長黑暗甬道裡,我與婆婆的身影交錯、故事重疊,原來早在病榻邊的一線之間,我已從照顧者翻轉成臨終者,嘗試思索躺著的自己的所有想望與最後完成。於是,「善終」成了活著的每一刻的在乎,並且為自己許下一個夠好(good enough)的陪伴。
臨終病榻邊,是每一個人最終會來到的所在。
不管是做為「臨終者」或「照顧者」,在這生死臨界的場域,時間與空間限縮的邊緣體驗裡,在世的角色、慣性模式、關係情感、自我價值,乃至於潛抑已久的生命故事,都像被突然輾壓爆開來的濃縮膠囊,顆粒分明地散落滿地,卻又非得被一一拾捻、凝視,才能再度回填、封存,成為一顆真正能滋養自己身心靈的長效良方。先吞下這膠囊,好好照顧自己,才能照顧他人的身心靈。
這份紀錄僅是呈現德國居家安寧照顧病榻邊的一個面向,無意鼓動某種角色義務的履行,或是強化所謂傳統的孝道,因為每一段相對關係都是獨一無二的,照顧與陪伴的形式對雙方都有難以言喻的意義,而且每個決定背後都有值得被尊重的原因,以及此去用生命傳續故事的無限可能。
然而,病榻邊許多困惑未解與自我反思,乃至對於臺灣政府完善社會福利與安寧療護體系的期待,以及企盼「老有所終」與「善終」具有時代意義,則是我希望藉由文字分享,能引發更多的共鳴與討論。
婆婆從發現罹癌隨即採用「德國基督教社福機構聯合會」(Diakonie,以下簡稱「基福會」)所提供的居家安寧照顧工作,該組織的成立宗旨正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自主且獨立地實現自身的生存權」,補救政府單位觸角未及的社會福利網漏洞。
這項宗旨深深觸動我,特別是「生存權」被廣義地擴延到臨終死亡的權利,讓每一個人到生命的最後,還能行使自主與獨立,正是臺灣當前推動安寧照顧可以參照的部分。
年過半百,身邊的友人一一成為臨終的照顧者,特別是單身未婚者,更陷入有苦難訴的獨撐困境,經濟、社會地位與自我價值隨著時間,土石流般地消蝕,甚至不知道終點究竟在哪裡?
除了呼籲政府完善社會福利網、周全安寧照顧體系,以及宗教資源的整合與投入之外,我僅能努力地以注視的眼,幫助友人們看見自己的付出,並感恩這樣的自己。
選擇不來或離開病榻邊,可能有千百個說辭,但是願意留下來照顧的,卻是得用漫長的一輩子去感受與想思,然後給自己一個安妥的理由。
又或者到最後,連這樣的理由追索都忘失了,而是意外地與另一位更接近實相的自己相遇,並且以愛安在於陪伴與被陪伴的循環共生裡。
二○一四年三月,從旅居五年半的上海,舉家搬遷到吉隆坡,三週後我獨自帶著三名孩子飛回德國照顧膀胱癌末期的寡居婆婆,直到往生。
在西南德山村的一棟五十多年老屋裡,終其一生照顧了五代人的八十四歲臨終德國老奶奶,再加上「自作主張」的臺灣媳婦,以及年齡各十四、十二與一歲半的「狀況外」混血孫女,還有至少六位輪班換值的「非政府」安寧體系照護員。
如此「拼湊」(patch)的雜牌軍在臨終病榻旁,究竟能有怎樣的故事演繹?
做為一名外籍媳婦,又是首次居家安寧照顧,技術生澀、對死亡全然陌生,以及不熟悉德國醫療體系的我,從在病榻旁就開始點滴記錄過程,包括德國醫護人員對我身分的質疑、婆婆執拗地抵抗他人在生活起居上的協助、女兒們與奶奶型態各異的互動、考量委請烏克蘭看護與否,到最後遺願的探詢與完成,甚至是否由「管」很大的維生系統介入的抉擇,以及「另類」善終的觀察。
過程中越是自覺不周到與錯誤的斷裂之處,越是成為後來追索答案的破口,甚至是補救學習的起點;越是感到沒有把握,以及自我懷疑的停頓處,就越是關聯自身陰暗面,等待多幾秒安忍恐懼的探照。
婆婆往生後,我接觸了更多生死學的書籍、講座,以及實際學習居家照顧技巧,甚至是這幾年許多生活的意外遭逢與發生,包括兩次急診住院,以及簽下放棄急救與器官、大體捐贈。因為每一次當下新的生命經驗,再持續回頭照看這段安寧照顧的經過,卻有了不同的理解,乃至更深化生命面向的探照。
彷彿是永遠走不完,又時時意義更新的歷程,但卻仍無法完全書寫出婆婆生命的豐厚感。
在回首的長長黑暗甬道裡,我與婆婆的身影交錯、故事重疊,原來早在病榻邊的一線之間,我已從照顧者翻轉成臨終者,嘗試思索躺著的自己的所有想望與最後完成。於是,「善終」成了活著的每一刻的在乎,並且為自己許下一個夠好(good enough)的陪伴。
臨終病榻邊,是每一個人最終會來到的所在。
不管是做為「臨終者」或「照顧者」,在這生死臨界的場域,時間與空間限縮的邊緣體驗裡,在世的角色、慣性模式、關係情感、自我價值,乃至於潛抑已久的生命故事,都像被突然輾壓爆開來的濃縮膠囊,顆粒分明地散落滿地,卻又非得被一一拾捻、凝視,才能再度回填、封存,成為一顆真正能滋養自己身心靈的長效良方。先吞下這膠囊,好好照顧自己,才能照顧他人的身心靈。
這份紀錄僅是呈現德國居家安寧照顧病榻邊的一個面向,無意鼓動某種角色義務的履行,或是強化所謂傳統的孝道,因為每一段相對關係都是獨一無二的,照顧與陪伴的形式對雙方都有難以言喻的意義,而且每個決定背後都有值得被尊重的原因,以及此去用生命傳續故事的無限可能。
然而,病榻邊許多困惑未解與自我反思,乃至對於臺灣政府完善社會福利與安寧療護體系的期待,以及企盼「老有所終」與「善終」具有時代意義,則是我希望藉由文字分享,能引發更多的共鳴與討論。
婆婆從發現罹癌隨即採用「德國基督教社福機構聯合會」(Diakonie,以下簡稱「基福會」)所提供的居家安寧照顧工作,該組織的成立宗旨正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自主且獨立地實現自身的生存權」,補救政府單位觸角未及的社會福利網漏洞。
這項宗旨深深觸動我,特別是「生存權」被廣義地擴延到臨終死亡的權利,讓每一個人到生命的最後,還能行使自主與獨立,正是臺灣當前推動安寧照顧可以參照的部分。
年過半百,身邊的友人一一成為臨終的照顧者,特別是單身未婚者,更陷入有苦難訴的獨撐困境,經濟、社會地位與自我價值隨著時間,土石流般地消蝕,甚至不知道終點究竟在哪裡?
除了呼籲政府完善社會福利網、周全安寧照顧體系,以及宗教資源的整合與投入之外,我僅能努力地以注視的眼,幫助友人們看見自己的付出,並感恩這樣的自己。
選擇不來或離開病榻邊,可能有千百個說辭,但是願意留下來照顧的,卻是得用漫長的一輩子去感受與想思,然後給自己一個安妥的理由。
又或者到最後,連這樣的理由追索都忘失了,而是意外地與另一位更接近實相的自己相遇,並且以愛安在於陪伴與被陪伴的循環共生裡。
圖書評論 - 評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