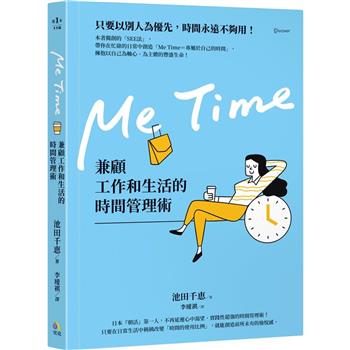▍序章 連國家都棄之不顧的世代
●無法逃離的非正職命運
無法成為正職員工……。
在三十五到五十四歲的人當中,以非正職員工身分工作的「中年打工族」(中年フリーター)有二百七十三萬人,相當於同世代中,十人就有一人是打工族,但這個數字不包含已婚女性。在同年齡層的非正職女性員工中,有些人不用刻意調低薪資,就符合被扶養人口的認定標準,而這些人多達四百一十四萬人,因此潛在的中年打工族其實應該更多。
身為中年打工族之一的松本拓也(四十三歲),平靜地說出自己長年以來作為非正職員工的心聲。
「到了現在這個年紀,我對雇用環境已經不再存有希望了。一想到今後我可能再也無法成為正職員工,非正職的我獨自一人在社會上載浮載沈的感覺就不斷襲來。」
拓也到目前為止做的都不是正職,而且每家公司都是黑心企業。三十多歲時他在量販店當約聘員工,月薪三十萬日圓,雖然很快就升為副店長,但每個月都要加班超過一百小時以上,最後他終於選擇了離職。
接下來拓也在餐飲業打工,一個月薪水十三萬日圓。由於拓也覺得勞動條件不合理所以跑去問公司是怎麼回事,結果竟然被開除。失業的他只能靠著政府補助去職訓班上課。
拓也並不放棄,仍然繼續找工作,終於在一家東京都內的高級超市以全職計時人員的身分開始上班。這間超市有許多分店,拓也總算得到了暫時的「安定」。目前人手不足的零售業界薪資有上漲的趨勢,而拓也的時薪是一千二百六十日圓。由於店面營業到很晚,拓也積極爭取讓自己的班表可以排到有加班費的時間,光是加班費一個月大概就有八萬日圓。雖然還要扣掉社會保險等費用,但一個月算下來仍然可以實拿二十三萬日圓。
雖說如此,但在合約還沒更新之前,拓也還是很怕公司通知他合約中止。有很多負責收銀的派遣員工「被離職」,但是他們看起來卻不生氣,可能因為他們也知道非正職被解雇是理所當然,一想到這點拓也就忍不住害怕。
「未來就算再怎麼努力,我這個年齡也很難成為正職員工了,加上存款又少,今後我該何去何從呢?」
再怎麼努力也無法脫離非正職員工的命運,社會上難以被發現的貧窮就存在於此。
●歷年來最好的應屆畢業生求職市場
現在的新聞經常報導勞動條件嚴苛的職場環境,而勞動基準監督署介入知名企業斡旋的例子也屢見不鮮。
這幾年引起最大風波的,莫過於二○一五年電通公司的女性職員因為超時工作自殺,結束了二十四歲的年輕生命。這個有大好將來的年輕女孩,明明進入了人人嚮往的大公司電通,卻因為上層仗勢欺人、強迫她長時間加班,結果她在進公司九個月後的聖誕節早晨走上絕路。這個事件被媒體大肆報導,連勞動省也介入調查,成為難以抹滅的事件。
少子化造成勞動人口減少,無論政治圈或財經界都不得不開始有所行動,針對勞動方式提出改革。安倍晉三推出了一連串諸如「一億總活躍社會」、「打造所有女性都能發光發熱的社會」、「工作型態改革」等有關勞動問題的口號,接二連三地端出過往未曾有過的雇用政策。
現在的應屆畢業生面對的是求職者占上風的市場,預定於二○一九年三月畢業的大學生內定率至二○一八年九月一日為止是九一.六%,跟前年九月的八八.四%相比,成長了三.二個百分點(株式會社Recruit Career調查)。從就業率(就職人數中畢業生所占比例)來看,二○一七年三月的大學畢業生為七六‧一%、二○一八年三月為七七‧一%,成長到接近於泡沫經濟之前的水準(文部科學省〈學校基本調查〉)。
光看就職的實際情況,就可以知道正職員工正在增加。
文部科學省在二○一二年度發表了就職人口中「正職員工」及「非正職員工」的內部分析資料,其中「非正職員工」指的是「雇用契約在一年以上或勞動時間相當於全職者」(從二○一二年起,變更為「雇用契約在一年以上或一週所定勞動時間在三十到四十小時者」)。從這份資料可以得知,二○一二年三月畢業的正職員工就業率為六○%,而二○一七年為七二‧九%,二○一八年為七四‧一%,一路攀升(〈學校基本調查〉)。
這裡點出的事實十分明確,也就是現今的勞動市場完全是以應屆畢業生為主流的市場。
●被忽略的中年勞動問題
在這種情況之下,卻留下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在就業冰河期(泡沫經濟崩壞後的就業困難時期)剛出社會,現在被稱為「中年打工族」的人們。
這個名詞在二○一五年受到注目。根據三菱UFJ研究顧問尾畠未輝研究員的試算,中年打工族不斷增加,在二○一五年時約有二百七十三萬人。
他們的存款比正職員工少,而且加入社會保險的比例也很低。當這些人到了可以拿年金的年齡時,一個月只會有不到七萬日圓的國民年金,屆時生活一定無法自理,很可能需要由政府照顧。然而日本的財政狀況並不能支撐這麼龐大的費用,社會福利制度很有可能會破產。
為什麼中年打工族會增加這麼多呢?
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在日本,應屆畢業時無法成為正職員工的人,之後也幾乎都是從事非正職的工作。勞動政策研究暨研修機構的〈非正職雇用之壯年勞工的工作及生活相關研究〉(二○一五年)中指出,男性在二十五歲時若為非正職員工,在五年後的三十歲時,成為正職員工的比例為四一‧七%、十年後的三十五歲為四九‧一%,將近半數。而三十歲時若是非正職員工,在三十五歲時成為正職員工的比例僅有二八‧○%。
過去剛畢業時經歷過失業潮的世代,現在已成了中年人(三十五到五十四歲)。也就是說,曾被稱為「就業冰河期世代」或「失落的世代」的這群人,過去找不到正職的工作,並且一直持續至今。
這裡我們從文部科學省的〈學校基本調查〉來確認就業率的走向。
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在經濟泡沫化後,一開始還維持在八○%左右的高水準,但是從一九九二年起由於經濟泡沫化的影響,應屆生的錄取人數開始縮水,一路往下降;在一九九五年已經跌到六五‧九%,但這只不過是冰河期的開始。一九九七年知名證券公司山一證券倒閉的時候,就業率更加慘澹,二○○○年時的統計第一次跌破六成,只有五五‧八%,而二○○三年時,則來到史上最低的五五‧一%。也就是每兩個學生中,就有一個找不到工作。
更大的問題在於當時「就業率」的定義是「雇用契約在一年以上」,等於非正職的雇用也包含在內;亦即無論正職或非正職都算在「就業率」之內。筆者大學畢業的二○○○年,雖說每兩個人就有一個找不到工作,但是有多少應屆畢業生是以正職員工的身分展開社會新鮮人之路,卻無從得知。二○○三年時,二十到二十四歲的完全失業率為九‧八%,等於應屆畢業生中十個人裡有一個沒工作。
之後,二○○八年的就業率回到了六九‧九%,接近七成;但同一年發生金融海嘯之後又再度下滑,二○一○年為百分之六○‧八%。等到金融海嘯漸漸和緩,再加上二○○七年起,由於團塊世代到了退休年齡因而出現大量離職潮,企業為了要確保找得到人才,從二○一○年之後就業市場突然站到了勞工這一邊。如之前所說的,二○一八年三月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上升到七七‧一%,終於回到了經濟泡沫化前的水準。
從上面的內容可以得知,應屆畢業生的錄取率會隨著每個時代的景氣而像雲霄飛車一樣上上下下,年輕人畢業的時間點不同,命運也大不相同。
●對失業潮世代置之不理的後果
另外還有以下的資料。
二○一七年總務省統計局的〈就業構造基本調查〉指出,若以男性大學畢業生的未婚率來看雇用型態的話,二十到二十四歲時,無論哪種雇用形態都有九五%以上未婚。然而到了三十五到三十九歲時,正職員工的未婚率降到二四‧七%,但相對地派遣或約聘員工則為六○‧六%、計時人員等打工族則有七九‧四%都是未婚。
而在〈二○一七年非正職雇用之女性相關調查〉中,可以得知女性的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就職的工作)會依雇用形態的不同而影響婚姻或生育。女性的第一份工作是正職員工的話,有配偶的比率是七○‧九%,但若是非正職則只有二六‧九%。若觀察是否有小孩的比率,第一份工作是正職的有五四‧一%,而非正職則只有二一‧六%。
出社會的起步若是非正職,會對生育造成很大的影響。
在各式相關的定期調查中,有一項由國立社會保障暨人口問題研究所所做的〈出生動向基本調查〉。這個調查每五年在全國實施一次抽樣調查,最新版為二○一五年。我想以經濟環境對生育態度的影響為例,來看看「夫妻的理想子女生育數」的變化。
在調查中最高的數值是經濟泡沫化之前的一九八七年(二‧六七人),而在二○一五年的調查中則跌到歷年最低的二‧三二人。若對象是結婚零到四年的夫妻則為二‧二五人,這也是史上最低的數字。若詢問的是「夫妻預計的平均子女生育數」,大約是二‧○人。由此可見夫妻間的「理想」不過是突顯少子化的嚴重性,但在現實中「預計」卻是不得不放棄的夢想。
少子高齡化是日本社會極為嚴重的問題,這點自不待言。二○一六年出生人數首次跌破一百萬人,而隔年(二○一七年)則創下史上最低的九十四萬人的紀錄。
這個背景來自於團塊二世世代(一九七一到七四年生的人)超過了生產年齡,以及過半數的團塊二世世代及後團塊二世世代(一九七五到八一年生的人)都是經歷過就業冰河期的人,這一點也不能忽略。他們的特徵是就算有伴侶,對結婚也猶豫不決、在生小孩上舉棋不定。
由於看不見未來,現在不談戀愛的中年打工族更多了。如此一來不婚或單身的世代就增加了。跟父母一起住在家裡,在還能利用爸媽的年金或儲蓄時,也許可以再撐一下也說不定。然而當爸媽走了之後又或者是自己生病需要看護時,生活就會立刻陷入困境。什麼安享晚年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有貧困跟隨在自己身邊罷了。
●再這樣下去社會保險會破產
有關這個問題,NIRA綜合研究開發機構在二○○八年四月時整理了一份〈就業冰河期世代的危機〉報告,敲響了警鐘。
該份報告將就業冰河期定義為從一九九三年起,約十年左右的期間。若當時是高中畢業則是一九七五年到八五年出生;若是大學畢業則是一九七○年到八○年左右出生。只是為了統計的方便,二○○二年的就業構造基本調查中,二十五到三十四歲(亦即一九六八年到七七年出生的人)也被視為就業冰河期的成員。
根據這份報告的試算,由於非正職勞工的增加或沒有上班上課的無業者──也就是打工族的增加,會產生七十七萬四千位接受社會救濟的潛在人口。當他們接受社會救濟之後,追加的累計預算金額會提高到十七兆七千億到十九兆三千億日圓。
接受救濟的人在二○一五年三月時,比最高峰期的二百一十六萬人略少了一些,但仍有二百一十萬人左右。從年齡上來看,六十五歲以上的銀髮族占了將近四五%,而四十到四十九歲約為一○%,等於十人中就有一人。長期來看,六十到六十四歲的人比四十多歲的更多,但在二○一四年卻逆轉了。
「失落的十年」延長成為「失落的二十年」,這是因為國家對雇用問題沒有認真看待的緣故。二○○○年時,「打工族太天真」、「年輕人只做自己想做的工作」這種風氣盛行,沒有人提出認真的反思導致問題被埋沒。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年輕人」變成了「中年人」,而「中年打工族」很有可能成為動搖國本的問題,這件事又有多少人察覺呢,到時連帶的消費跟稅收也都會大幅降低。
●筆者經驗談
筆者長年關注就業冰河期的問題,契機是我自身對於跟我同世代的朋友(包含我自己在內)的工作方式有著很單純的疑問。
筆者畢業於二○○○年,那一年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在統計上首次跌破六成,相當於每兩個人中就有一個找不到工作。筆者大約應徵了一百家公司,參加了五十家公司的面試。最後只拿到一家消費金融大企業的綜合職錄用通知。我婉拒了那家公司,在畢業後重新開始找工作,後來進到一家剛申請民事再生法(譯注:協助瀕臨破產企業重建的法律)的報社,成了正職員工。
一年後,週刊經濟以「只有剛開始是約聘員工」的條件把我挖角過去,我成了週刊經濟的約聘員工,與每日新聞社簽下了每年更新一次的合約。
我的工作範圍十分廣泛,每天都工作到渾然忘我,媒體業是沒有所謂上下班時間的。雜誌在送印之前一直上班到隔天早上是常有的事,也曾經在編輯部的沙發上蓋著報紙睡著,第二天一早又起來繼續工作。
只是過了一陣子之後,我對於約聘這事開始感到不安,因為看不到未來。但如果想要成為正職員工的話,還要跟著在學的學生們一起考筆試通過才算合格。那時我已經習慣這份工作了,當收到讀者對我寫的新聞或特別報導表達支持的信時,我又會認為這份工作是我的天職,一直當個約聘員工也無妨,這種矛盾感一直存在。
而環顧四周,不管是在哪個業界工作的朋友,不論是否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成就感,一樣都每天免費加班,搭著末班電車回家;星期六日也是照常上班不支薪,每天累得要命。
「大家都這麼累,不會有點奇怪嗎?這應該是很嚴重的問題吧。」
這是我當時直覺。
在擅長分析總體經濟學的週刊經濟中,勞動問題跟經濟或企業經營是完全不同極端的東西,但是我認為「形成總體經濟學的正是每一個個體的勞動」、「在勞動的意義上作為支柱的年輕人如果失去力量的話,對將來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有報導的必要。
我雖然向編輯部提出企劃書,但由於當時「年輕人太天真」的看法很普遍,所以沒有被採用。而且當時大家的焦點集中在中高齡裁員上,很少有人會去注意年輕人的雇用狀況。
那時「非正職員工」這個詞在社會上還不普遍,大家都以「飛特族」來稱呼非正職員工。「飛特族」這個詞是 Recruit於一九八七年所創造的,是將自由工作者及打工族兩個詞併在一起的造語。這個詞在八○年代的泡沫經濟時期,會讓人聯想到歌頌自由的年輕人,也因此不會讓人感受到事態的嚴重性。
在企劃書沒通過的二○○三年,我煩惱著是不是要換到其他一直找我過去的公司。年輕氣盛的我,約了當時伊藤忠商事的丹羽宇一郎社長跟他傾訴人生的煩惱。面對因企劃不過而感到沮喪的我,丹羽社長建議:「你就跟公司提三次看看,如果連提三次,主管應該會讓步。」
「再提三次企劃看看,如果還是過不了的話,我就離職換工作。」
下了這樣的決心之後,我再度將企劃呈上去。終於在向第三位主管進行第三次提案後,得到了許可。當時政府剛好發表了「國民生活白皮書」,大家對於十五到三十四歲的年輕打工族有四百一十七萬人這個問題十分重視。之後我有數篇特別報導被刊出,二○○五年刊出了第一回的特輯〈兒子女兒的悲慘職場〉,這些特輯包括了正職員工和打工族的平均年收差了二到四倍,由於飛特族和尼特族的增加,預計會在二○三○年達到六兆日圓的稅收缺口等等,另外我也舉出了對總體經濟學的影響。很幸運地這個特輯獲得了廣大的回響,我對於自己能洞察就業冰河期問題發端感到驕傲。
●無力的日本中年人
只是直到現在,情況仍然都沒有改變。我感覺從「年輕人」變成「中年人」後,事態更加惡化。
中年打工族無法成為正職員工的原因在於,經濟不景氣時正職員工的名額很少。一旦成為非正職員工後,因為「學不到技術」或者是「就算有專業也不被認可」的狀態會一直持續,所以就算景氣好轉、職缺增加,他們也找不到想做的工作。
正職員工一定要長時間工作,所以有些人會擔心自己做不來,最後正職員工的選項就被他們刪掉了。二○一六年厚生勞動省發表的〈時薪制勞工綜合實態調查〉中顯示,有一○‧三%的人選擇時薪制的理由是「如果以正職員工的身分工作,在體力上難以負荷。」
要選擇工時長的正職員工,還是選擇不安穩的非正職員工呢?
在二選一的情況下,有小孩要養的女性不得不選擇非正職,然而現在這種問題似乎也擴及到男性身上了。我能夠一直這樣工作嗎?有必要緊緊抓著正職員工的職缺不放嗎?我聽到了一些這樣的聲音。
接著另一個浮現的問題是「自暴自棄」。就算有想要成為正職員工的念頭,還是會出現「反正我一定沒辦法」這種「自暴自棄」的想法來攪局。
只要努力,總有一天可以找到安穩的工作,就業冰河期世代這樣相信著。然而這個世代卻是再怎麼認真也不受重視,用完即丟的免洗世代。他們對企業和社會開始產生不信任的感覺,工作動力最後也會慢慢消失。
另一方面,大企業似乎在歌頌這個世界的春天。財務省〈法人企業統計調查〉顯示,象徵企業保留盈餘的留存盈餘(金融保險業以外的全部產業)每年都在增加。二○一七年度比前一年增加四十兆日圓,達到四百四十六兆四千八百四十四億日圓,已連續六年創下過去新高。
從國稅廳〈民間薪資實態統計調查〉中可以得知,中年世代的平均年收,女性依舊是三百萬日圓左右維持不變,但正值盛年的男性收入卻年年遞減。男性的平均年薪若以「一九九七年→二○○六年→二○一六年」進行比較的話,三十五到三十九歲為「五百八十九萬日圓→五百五十五萬日圓→五百一十二萬日圓」,這二十年間年薪減少了七十七萬日圓。此外,四十到四十四歲則是「六百四十五萬日圓→六百二十九萬日圓→五百六十三萬日圓」,減少了八十二萬日圓;四十五到四十九歲則是「六百九十五萬日圓→六百五十六萬日圓→六百三十三萬日圓」,減少了六十二萬日圓。
不止如此,厚生勞動省的調查中,就算都是全職,一般員工跟非正職員工的薪水也有差別。四○到四四歲的非正職員工時薪為一二九四日圓,只有正職員工的百分之六三;四五到四九歲的非正職員工時薪為一二七○日圓,為正職員工的百分之五六; 五○到五四歲的時薪為一二五九日圓,只有正職員工的百分之五二。年齡越大,差距越大(二○一七年時的薪資)。
這種惡劣的現狀絕不能無視。
| FindBook |
有 19 項符合
中年打工族:為什麼努力工作,卻依然貧困?日本社會棄之不顧的失業潮世代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4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
中年打工族:為什麼努力工作,卻依然貧困?日本社會棄之不顧的失業潮世代 出版日期:2020-05-19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中年打工族:為什麼努力工作,卻依然貧困?日本社會棄之不顧的失業潮世代
即使拚了命努力,工作超過十二小時,
還是可能在一瞬間就跌入失業的深淵……
沒有收入、不能休息、無法翻身
//深度追蹤.日本勞動經濟記者的社會觀察 //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過去十年來,全球青年失業率不斷上升,其中有3/4的青年從事非典型工作。日本更是早在九○年代末期,因為泡沫經濟崩壞,企業縮減人事成本,連續數年出現年輕人求職困難,不得不暫時打工謀生。然而原本「暫時」的打工卻無限延期,時至今日,這些失業潮世代的青年打工族已成了「中年打工族」。
「就算是日領派遣也沒關係,只要每天都有工作就好了……」
──石田健司,38歲
「安倍經濟學的例子只適用於電視上才看得見的大公司,我們這些最底層的人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藤田信也,43歲
「考慮到工作時間和相對報酬,也許去超商打工或直接當妻子的扶養家屬會比較好……」
──廣田信平,33歲
「我真的很不想迎接40歲以後的人生,這樣下去別說結婚了,老了以後該怎麼辦?」
──松本拓也,43歲
「明明知道隨時會被開除,卻還要努力工作,真的很難受。」
──單親媽媽由夏,40歲
「為什麼和正職做相同的工作,薪水卻比他們低,難道我到60歲都只能是非正職嗎?」
──吉田健一,37歲
「雖然太太說想要再生第二胎,但靠現在的收入,我連能不能養大第一個孩子都沒有自信。」
──佐藤正志,41歲
「懷孕本是令人高興的事,然而現實中,職業婦女懷孕後,卻只能一直說『對不起』……」
──宫田弘子,40歲
被日本社會拋下的273萬人,經歷就業冰河期,成為中年打工族。
他們和其他414萬可能作為扶養人口而未被列入統計的人們,
只因為找不到一份穩定的正職工作,
被迫放棄戀愛、婚姻、生育、人際關係、房產,
不斷失去一切的人生,看不見夢想和希望……
身為同一世代的作者小林美希,從2003年起便開始關注這些打工族,透過深入且不間斷的追蹤與報導,使世人看見這群生活在底層的人們,在低薪、過勞、不穩定、缺乏訓練機會的職場中遭遇的絕望,以及掙扎努力後的徒勞,女性甚至還得面對「懷孕歧視」等更為惡劣艱難的處境。書中對中年打工族的採訪記述,不僅揭露日本社會階級底層的生活,也直指社會支持體系的各種失能。對此,小林美希以採訪政府及企業組織的方式,企圖積極尋求改變的可能性。
台灣近年來除了青年失業率不斷增加,整體經濟環境也和日本一樣處在薪資停滯不動的貧窮循環危機。日本社會面臨的難題可能成為台灣社會未來的寫照,甚至此刻台灣也許已踏上相似的路途,而這本書將為我們帶來警醒與思索。因為在一個健全發展的社會中,沒有一個人該被拋下。
名人推薦
朱剛勇│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林立青│作家、《做工的人》作者
阿潑│文字工作者
許伯崧│UDN鳴人堂主編
賴芳玉│律師
盧郁佳│作家
──一致好評
作者簡介:
小林美希こばやしみき
勞動經濟記者。1975年生於茨城縣,水戶第一高中、神戶大學法學部畢業後,曾任株式新聞社、每日新聞社《週刊經濟》編輯部記者,2007年起以自由記者的身分活動。主要著作有《深度報導 托育崩壞》、《深度報導 看護的品質》、《深度報導 托育差異》(以上皆為岩波新書)、《希望丈夫死去的妻子們》(朝日新書)等。
譯者簡介:
呂丹芸
輔大日文系畢,曾留學日本兩年,現為兼職譯者。譯有《在寂寞中靠近》、《只想好好結個婚》、《小數據騙局》、《才不是魯蛇》等。
章節試閱
▍序章 連國家都棄之不顧的世代
●無法逃離的非正職命運
無法成為正職員工……。
在三十五到五十四歲的人當中,以非正職員工身分工作的「中年打工族」(中年フリーター)有二百七十三萬人,相當於同世代中,十人就有一人是打工族,但這個數字不包含已婚女性。在同年齡層的非正職女性員工中,有些人不用刻意調低薪資,就符合被扶養人口的認定標準,而這些人多達四百一十四萬人,因此潛在的中年打工族其實應該更多。
身為中年打工族之一的松本拓也(四十三歲),平靜地說出自己長年以來作為非正職員工的心聲。
「到了現在這個年紀,我對...
●無法逃離的非正職命運
無法成為正職員工……。
在三十五到五十四歲的人當中,以非正職員工身分工作的「中年打工族」(中年フリーター)有二百七十三萬人,相當於同世代中,十人就有一人是打工族,但這個數字不包含已婚女性。在同年齡層的非正職女性員工中,有些人不用刻意調低薪資,就符合被扶養人口的認定標準,而這些人多達四百一十四萬人,因此潛在的中年打工族其實應該更多。
身為中年打工族之一的松本拓也(四十三歲),平靜地說出自己長年以來作為非正職員工的心聲。
「到了現在這個年紀,我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章 連國家都棄之不顧的世代
無法逃離的非正職命運
歷年來最好的應屆畢業生求職市場
被忽略的中年勞動問題
對失業潮世代置之不理的後果
再這樣下去,社會保險會破產
筆者經驗談
無力的日本中年人
本書構成
▍第一章 中年打工族的現實
1 中年男性的絕望──健司(38)的情況
「穩定的工作」到底在哪裡?
打工族也曾有賺很多的時候
被奪走的「穩定」二字
只體驗過一次的「正職員工」經歷
2離「景氣回復」還有好遠的路
被「三份工作」追著跑的日子──信也(43)的情況
因為憂鬱症而進入非正職的循環──武志(44)...
無法逃離的非正職命運
歷年來最好的應屆畢業生求職市場
被忽略的中年勞動問題
對失業潮世代置之不理的後果
再這樣下去,社會保險會破產
筆者經驗談
無力的日本中年人
本書構成
▍第一章 中年打工族的現實
1 中年男性的絕望──健司(38)的情況
「穩定的工作」到底在哪裡?
打工族也曾有賺很多的時候
被奪走的「穩定」二字
只體驗過一次的「正職員工」經歷
2離「景氣回復」還有好遠的路
被「三份工作」追著跑的日子──信也(43)的情況
因為憂鬱症而進入非正職的循環──武志(44)...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2020/12/27
2020/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