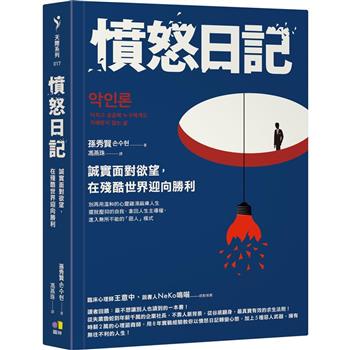好想吃滷肉飯、做腳底按摩!我得了「台灣缺乏症」
三個月來(註:本文寫於5月中旬。),我無法去台灣,哈日族也不能來日本,雖然被疫情阻隔,日本人卻比從前更認識台灣,我不斷思考,為什麼日本防疫遠輸台灣?
老實說,跟那些因為這次的緊急事態宣言而失業、減薪、無法上學的人比起來,我的狀況還算可以。寫作本來就是在家或職場上獨力為之的工作,一個星期都沒有與人見面也不稀奇。工作量沒什麼太大的影響,因此我也沒打算大吐苦水。
只是,無法去台灣真的很痛苦。自從我二〇一六年離開《朝日新聞》的工作,就每個月或每兩個月到台灣一次。但今年一月起,我就沒到過台灣,至今已經三個月了,我逐漸陷入了「台灣缺乏症」。我想吃滷肉飯、想吃排骨飯、想去腳底按摩、想去洗頭,也想見我的台灣朋友。在日本家中等待回復正常的我,時常湧現這些渴望。
同樣的,有不少台灣人也陷入了「日本缺乏症」吧?人口近兩千四百萬的台灣,去年就有五百萬人到訪日本。台灣人很喜歡日本,而世界第一的哈日國也是台灣。一年四季,春天賞櫻,夏天避暑,秋天賞楓,冬天看雪,為了不同趣味而走訪日本的人不少。
祕境溫泉、美食居酒屋、絕佳的民宿等,台灣人比日本人還清楚。
對於這樣的台灣人來說,這三個月的「日本斷捨離」,想必很辛苦。
即便如此,這三個月來,台灣在新冠肺炎防疫上的努力,讓日本人刮目相看、跌破眼鏡,感到吃驚,日本電視新聞也不斷報導台灣的事。而台灣的政治人物裡,不只總統蔡英文,唐鳳、阿中部長、大仁哥都在日本成了名人。
其中,我忍不住思考「台灣是什麼時候超越日本的呢?」流行病防疫對策,台灣的處理經驗遠超過日本。在日本,很多人指出:「因為台灣有SARS的經驗。」這只說對了一半。台灣確實以SARS的痛苦經驗為起點,修改了傳染病防治法,也增設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等,打造出防止新興傳染病入侵的法治與系統架構,這和今日的成功有關。
但是,當時的教訓,不是只有台灣經歷到,其他國家也在SARS時期遭受打擊。二〇〇三年,我在新加坡生活,當時社會也非常混亂與恐怖。但新加坡這次的防疫策略,還是有許多人遭受感染而陷入痛苦;中國則再次隱匿資訊,拒絕WHO調查團介入。
即便是日本,也握有足夠資訊,深知SARS有多嚴重。當時,身處SARS抗疫策略最前線的WHO西太平洋地區事務局局長,是日本人尾身茂。他也是現在日本政府新型冠狀病毒對策本部的諮議委員會長,日本首相安倍的記者會上,尾身茂總是站在旁邊給予支持,可說是日本對抗新冠肺炎的指揮官。
他是否記取SARS的教訓,對日本這次抗疫策略有所幫助?答案是沒有。當時,WHO因為中國隱匿資訊,拒絕調查團介入而苦惱的時候,代表和中國交涉的窗口就是尾身茂。
但這次日本和WHO都依賴中國提供的資訊,導致對新冠肺炎處置太慢。明明SARS經驗就告訴我們,早期檢疫、隔離有其必要性,但日本的PCR檢驗還是量能不足,檢測速度延遲的問題至今無法改善,隔離措施也只做半套,面臨感染人數增加,無法掌握實際狀況等種種問題。
也就是說,世界上有跟台灣一樣從SARS學到教訓的國家,也有跟日本一樣沒學到教訓的國家。
此外,就算用盡全力做隔離和檢疫,完善法律與制度面,但社會整體的努力不足,對抗傳染病的防疫體系依舊無法運作。
要讓這個體系妥善運作,必須檢視如何維持民主主義的健全性、資訊公開、對弱勢的關心、如何活用專業人才、防止假新聞等,傳染病防治對策靠的是國家整 體的綜合能力,公衛就是綜合政策。如此說來,SARS至今這十七年,台灣的努力沒有白費,才會有今天的成果。我認為,日本這次防疫失敗,就是「失落的十七年」造成的。
過去台日之間,從歷史架構來看,日本給予、台灣接受,幾乎常是這樣的關係。在國際社會遭到孤立的台灣,希望日本多伸出援手,日本人很習慣聽到這種來自台灣的請求。
但這單向關係逐漸改變的契機,始於十年前。東日本大地震時,台灣為日本提供援助,台南地震由日本援助台灣,熊本地震時台灣援助日本,花蓮地震由日本援助台灣。地震時相互幫助,建構出「震災支援共同體」的關係。
這跟以往日本單方面給予台灣的關係不同,而是象徵了雙方互相給予、援助的平等關係。這次的新冠肺炎,台灣也是援助日本的那一方,和過去的角色截然不同。日本一直收到許多從台灣提供的援助、口罩等醫療物資。當然,新冠病毒的衝擊,無論防疫階段何時告終,都不得不面對接下來的經濟振興問題。我想此時,日本應該可以向台灣提供一些幫忙。
我期盼台日之間,在既有的「震災支援共同體」之外,可以此新冠肺炎問題為契機,再培育出以傳染病防治為中心的「防疫共同體」。這樣的概念,加上將來台日自由貿易協定、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等,建立結合防疫、防災和經濟的綜合性合作架構。台日的政治家,可以為下一階段台日關係做準備。
我在台灣搭計程車常覺得很受傷,直到遇見一個唱演歌的運將
在台灣搭計程車,對我來說是個壓力。
因為搭車的時候,司機常問我「你是日本人嗎?」我對自己的中文溝通能力稍有自信,而且在中國、香港、東南亞講中文,最近不太會被識破我是日本人的身分。
我在中國的時候常說「我是香港人」或是「我從台灣來」。因為只要一說我是日本人,對方就會說起日本該為戰爭負起責任的話題,以及日本首相安倍的壞話。我說我不是日本人,中國人幾乎都會相信。
我知道,我的中文發音沒有特別「標準」,但對於北京、上海人來說,他們常聽四川、山東人說中文,反而更難懂,所以整體來說,我的中文還算比較好理解吧。
至於東南亞的華人,很難想像日本人會說中文,所以就更容易相信我的話,因為他們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日本人就是英文很差。
但是,台灣人太了解日本人了,計程車司機馬上就會對我說「你的中文好像日本人」。我一聽到這話,怎麼想都覺得很受傷,所以以前只要有台灣司機問我「你是日本人嗎?」,我就會心想「又來了」,然後不悅地以不友善的態度回他「我是日本人沒錯,有什麼問題嗎?」
十二月上旬,我在台北松山機場降落後搭上計程車。果然,司機就問我「你是日本人嗎?」但這次,他看起來跟以往的司機不太一樣。
這位五十多歲的計程車司機說,「如果你是日本人,我想請教你一件事。」接著,他說「幫我聽一下這首歌。」他打開手機,播放音樂,那是日本重量級演歌歌手北島三郎的曲子。歌放到一半,司機以認真的表情說,「從這裡開始,仔細聽喔。」
唱到「鶴先生、龜先生」的地方,司機問我說,「這句怎麼發音?」我回答他,「是烏龜,烏龜先生。」他就欣喜地說,「烏龜(日語讀音kame)嗎?我還以為是神(kami),原來如此。」
十多年前,他迷上演歌,就開始把歌詞寫在紙上,一一背下來。他把那張紙拿給我看,上面滿滿的都是手寫的歌詞。
「我們計程車司機有很多空閒時間。大家不是看電視,就是嚼檳榔,我是學演歌來打發時間,回到家也會唱卡拉OK,很開心,」他說。
我聽到司機這樣說,實在太開心,想都沒想就立刻低頭感謝他說,「謝謝你喜歡日本文化。」接著,我問他,「為什麼這麼喜歡日本演歌?」
他解釋,「因為日本演歌跟台語歌很像,台語歌幾乎是複製日本演歌而來。曲調都很熟悉,我查了一下歌詞的意思,內容也幾乎都能引起台灣人共鳴。」
其實,會聽日本演歌的台灣計程車司機很多。台灣的廟裡,也常看到許多太太,一早就開始唱日本演歌。為什麼台灣人這麼喜歡日本演歌,這是一個謎。但我想這應該跟戰後日本文化的限制有關。
戰後的台灣,是不准聽日本歌的。但那樣的曲調和風格,仍保留在台語歌謠之中。只是,在公開場合唱台語歌也沒有好處。我想我們可以說,直到解嚴後,台灣人可以唱自己喜歡的台語歌、日本歌謠,也形同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體現方式。
其實,日本演歌也是從人們對自由的渴望中衍生出來的。據說,演歌始於明治時代的民權運動,日本民主人士將批判政府的想法寄託在音樂之中,以日本風格的傳統音階,搭配西式節奏的歌曲,創造出折衷的混搭曲風。
演歌也在戰後的快速經濟成長期復活。當時,日本人把過去美好時代已逝的嘆息,寄託在歌手們的演歌上。包括石川小百合、八代亞紀、北島三郎、五木宏等,許多明星歌手在此時誕生,不知不覺地創造出「唱出日本心聲的傳統文化」。但當時距離日本人認真開始唱出演歌也不過才五十年的時間。
在日本,演歌是六〇到七〇年代間成長的世代在唱。像我這樣在八〇年代成長的世代,對演歌是不討厭,但更喜歡中島美雪、佐田雅史這樣的歌手兼創作者。他們的歌在台灣也很流行,前幾天我在大稻埕散步的時候,河邊的廟裡傳出卡拉OK的歌聲。
仔細一聽,發現是夏川里美的「淚光閃閃」。對於我的世代來說,夏川里美很親切。說到這,夏川里美每年都會在台灣辦演唱會,細川貴志也在二〇一九年年底到台灣辦晚宴秀。對於日本歌手來說,台灣是個重要市場吧。
說起日本人會唱的台灣歌手的歌曲,大概就是鄧麗君了吧。我希望日本人也愈來愈熟悉不一樣的台灣歌曲,盛大舉辦台日歌謠交流活動。台灣也有許多很棒的歌手,台灣的中文歌水平,我認為,在華語圈相對來說非常優秀的。
其實,我很喜歡去卡拉OK唱台灣的歌。尤其是張惠妹的歌,我很有自信可以唱得不錯。有時候,日本朋友帶我到林森北路,台灣朋友們聽了都覺得感動。
若是我在台灣的星光大道之類的綜藝節目唱,就會從作家變身為歌手也說不定。如此一來,我更要為了促進台日歌謠交流,奮不顧身地來努力了。
日本按摩為何變得比台灣廉價?
日本人來到台灣旅遊,最常見的行程組合莫過於鼎泰豐的小籠包、故宮的翠玉白菜、還有腳底按摩這三項。日本人喜歡在台灣享受全身或是腳底按摩的理由,是因為台灣按摩師的手藝好,又價格便宜。
在日本,過去按摩的基本行情是一分鐘一百日圓,也就是六十分鐘六千日圓,算是高消費了。反觀台灣的按摩,基本上是六十分鐘台幣一千元=三千五百日圓,也就是花費是日本的差不多一半,卻能夠享受到比日本更舒服的按摩,這是台灣按摩之所以吸引日本人的魅力所在。
但是,最近日本的按摩行情出現價格崩壞,甚至比台灣還要便宜,讓原本佔價格優勢的台灣按摩,也逐漸失去了光環。為日本掀起這股按摩風潮的,是六十分鐘兩千九百八十日圓按摩店的崛起。
我也常愛按摩,一個禮拜至少要去一、兩趟。我的作家生活離不開電腦,使用電腦的時間一天至少超過八小時,再加上長時間盯著手機螢幕,長期下來深受肩頸和後背僵硬痠痛所苦。
自由媒體人的我,時間較為彈性,若在安排的會面之間出現空檔時,在東京都心地區遲遲找不到可以休息放鬆的地方。這個時候,如果在按摩店有一個小時可以好好閉目養神、接受按摩的話,肯定能夠紓解疲勞、恢復活力。
但是,價格就是一大問題了。如果按摩一次就要六千日圓,喔個月下來的費用也相當大。感覺自己是為了按摩而努力賺稿費,有點本末倒置了。可是,如果是三千日圓的話,一個月按摩十次也才三萬日圓,比較讓人捨得花錢享受。
二千九百八十日圓的按摩店,大約是從二〇一〇年左右開始出現的,之後逐年快速增加。這是必然的趨勢吧!因為如果只是六千日圓和五千日圓做比較的話,也許還會猶豫按摩師的手藝、距離、店內氣氛等其他因素。可是,如果直接折半變成三千日圓的話,連考慮都不用考慮了,民眾當然趨之若鶩,而且還成為常客。因此,有越來越多的按摩店就跟風降價攬客。現在,反倒是價格超過二千九百八十日圓的按摩店比較稀奇。
長期以來,日本處在通貨緊縮的時代。其中,在我的印象裡面,出現所謂的價格崩壞的,有麥當勞的漢堡從兩百日圓降價為一百日圓,吉野家的牛丼從四百日圓降價為兩百日圓,現在是連按摩價格也砍半了。
過去,二千九百八十日圓按摩店的服務也好,師傅的手藝也好,都馬馬虎虎。可是,最近有很多按摩店都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看得出非常努力在經營。像是最大型的按摩連鎖店「Rirakuru」,在管理店員或是顧客預約等系統都採用IT化,日本全國一千五百間店舖,不管是哪一間都沒有設置店長,店的經營方式是按摩師以個人事業主(不成立公司,個人經營事業)的身分登錄,這就是為何能夠削減成本的原因之一。甚至,預約大爆滿,必須拒絕其中的三分之一,事業進行地非常順利。店內的裝潢和衛生也都進行了改善,跟六千日圓的店相差無幾。
另一方面,台灣的按摩價格在這十年幾乎沒什麼改變,基本上是一小時台幣一千元。便宜的話,頂多八百元或七百元,與日本的二千九百八十日圓幾乎是不相上下。但是,我個人還是偏好台灣的按摩,按摩師的手藝好,力道較重也很仔細,只是最近在台灣每次去按摩時,腦海裡都會想到「還是日本便宜啊」。
果然,來台灣享受按摩的日本遊客減少了,那應該與日本的「價格崩壞」有關吧!實際上,在旅遊書上介紹的台灣按摩情報,似乎也沒有比以前多。不過誰知台灣未來是否會有一天也發生價格崩壞,出現很多五百元按摩店呢?
唐鳳在日媒受寵的理由
最近,在日本的政治新聞上曝光率最高的台灣官員是誰?台灣讀者猜得出來嗎?正確答案是政務委員的唐鳳。
跨性別者唐鳳是IT專家。民進黨政府上任後,被延攬擔任數位科技政務委員時,當時才三十五歲,台灣民眾對他的工作能力給予高度評價。但是,為什麼會被日本媒體如此頻繁地報導呢。
理由是在日本剛被任命的科學技術IT大臣,與唐鳳形成強烈對比,因此日本媒體在批判這項新內閣人事時,唐鳳成了再適合不過的比較對象了。上個禮拜,首相安倍晉三完成大規模的內閣改組,十九名閣員中有十七人職位異動,這應該是二〇二〇年東京奧運前的最後一次內閣改組吧。而且,被任命科技大臣的是七十八歲的眾議院議員竹本直一。
實際上,竹本曾擔任過為了維持印章文化而成立的「日本印章制度•文化守護聯盟」的會長。科技大臣的工作理應是致力推動行政事務的數位化,與堅守在書面文件上蓋章的傳統印章文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於是在社群網路(SNS)上,網友紛紛對於這項任命表達擔憂,各種質疑聲浪四起。
其實1年前也發生過類似的問題,眾議院議員櫻田義孝在就任負責網絡安全事務的國務大臣時是六十八歲,卻對網路一竅不通。在國會上接受質詢時,他明確表示自己是電腦盲,而且「不曾打過電腦」;還有,被問到關於USB接口的用途時,竟然回答:「要用的時候,好像要把它插到洞裡去,詳細情形我不太清楚」等,屢次出現不可思議的答辯內容,也成為國際媒體的笑柄。
竹本大臣也是因為年事已高,對IT的熟稔度遭到質疑,但是他本人似乎不以為意,澄清說自己經常使用社群網路,這部分應該沒有疑慮。即使如此,要說是否擁有足以擔任IT大臣一職的專業度來講,那就未必了。正確說來,他的認知是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功能是「沒問題」的,那樣的話,程度未免也太差強人意了吧。果然不出所料 ,這次在網路上也拿他和唐鳳做對照,有網友說「差別也太大了吧」「應該要向台灣學習的」。
為什麼沒辦法做到「適才適所」呢?那是因為和日本政壇的「大臣病」結構性問題有關。
通常,日本首相大概會在一到兩年內進行大規模的內閣改組,理由不外乎是「人心一新」(日本諺語。意思是透過重整人事,讓民眾有煥然一新之感)等籠統的說詞。事實上,目的是為了提供職位給一大堆正在排隊等著要當上大臣的政治家。
政治家想要當上大臣的理由有幾個。首先,是有利於選舉,以前有句話說:「將來不是博士就是大臣」,用來形容父母望子成龍的期待,顯示出日本社會對於大臣一職有著強烈的憧憬,也容易接近利益和權力的核心,資金不虞匱乏。再者,對於政治家本人也是相當大的榮耀,將來接受天皇敘勳的等級也會提高等。
而且,在擔任大臣的期間,會配給專車、秘書和警備人員,可以在大臣專屬的辦公室工作,空間寬廣舒適。經常可以從當過大臣的政治家那裡聽到,當上大臣的感覺是無比的痛快。
因此,在國會議員裡面,如果當選五次以上的人就有資格進入「大臣待機組」,有機會被延攬入閣。因為能力強和知名度高的人會被優先任命,所以也不少議員當選了七、八次,依然與大臣一職無緣。那樣的人在內閣改組時,通常就會被分配到除了外交、國防和總務大臣等重要職位以外的缺,也被戲謔為「庫存出清特賣會」。而日本的科技大臣經常是用在這場特賣會上的職位,任用年紀大,不一定要懂IT的人物,也不會引起太大的反彈。
雖然我不認為科技大臣一定要像唐鳳這樣的IT專家,但是至少要六十歲以下,對網絡有一定知識的人才,這樣給人的社會觀感也比較好吧。也可以從民間延攬有能力的高手,像是活躍於軟銀或是樂天的傑出人才等。處在資安問題足以動搖國本的網路時代,希望在IT領域上至少也要任用專業度高的大臣。
| FindBook |
有 19 項符合
看見不一樣的日本: 「高級國民」引發階級對立,獲勝之道講求美學,不讓座是怕被嗆聲或婉拒……野島剛的46種文化思索與社會觀察【作者燙銀簽名+給台灣讀者的感恩祝福金句】的圖書 |
 |
看見不一樣的日本: 「高級國民」引發階級對立,獲勝之道講求美學,不讓座是怕被嗆聲或婉拒……野島剛的46種文化思索與社會觀察【作者燙銀簽名+給台灣讀者的感恩祝福金句】 作者:野島剛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08-2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看見不一樣的日本: 「高級國民」引發階級對立,獲勝之道講求美學,不讓座是怕被嗆聲或婉拒……野島剛的46種文化思索與社會觀察【作者燙銀簽名+給台灣讀者的感恩祝福金句】
提出46個令人深思的觀點,
帶大家從日本思維看台灣,也由台灣視角理解日本。
在比賽中,日本人認為「美學」比「勝利」更重要,
志村健的本名竟是源自德川家康,
日本天皇登基晚宴為何每次都堅持用法國酒?
長期來往兩岸三地的資深媒體人野島剛帶大家從日本看臺灣,從臺灣理解日本,在本書中提出46個深度觀察,包括:唐鳳在日媒受寵的理由、日本按摩為何變得比台灣廉價、日本超商的24小時營業會走入歷史嗎……等。種種精闢的見解及不同角度的反思,都能讓人產生恍然大悟或會心一笑的連結與共鳴。
日本人眼中的台灣
日本人來到台灣旅遊,最常見的行程組合莫過於鼎泰豐的小籠包、故宮的翠玉白菜、還有腳底按摩這三項。其中,按摩受日本人歡迎的理由,是因為台灣按摩師的手藝好,又價格便宜。
但近來,到台灣享受按摩的日本遊客減少了,在旅遊書上介紹的台灣按摩情報,似乎也沒有比以前多,這應該與日本的「價格崩壞」有關吧!日本麥當勞的漢堡從兩百日圓降價為一百日圓,吉野家的牛丼從四百日圓降價為兩百日圓,現在是連按摩價格也砍半了。
不過誰知台灣未來是否會有一天也發生價格崩壞,出現很多五百元按摩店呢?
日本的變與不變
日本過去把追求成長視為理所當然,加班時數愈多,愈覺得企業有在成長。員工也因為感受到「工作的意義」,而忍受漫長的工時。有些人認為,為了背負工作的責任,就該忘掉薪水,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家庭來努力。
但現在的日本已邁入低成長時代,即便奮力工作,企業不一定會成長,日本經濟也不一定會成長。既然薪水不變,就不用勉強自己用力加班。我們的思考方式,自然會往這個方向改變。
每年,日本認定過勞死的人約兩百位。沒有什麼工作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了。每個月加班到一百小時,這太荒謬了。我期盼有一天,日本「殘業」(加班)文化絕滅,不會再有任何一個人因為「過勞死」而離世。
日本,原來如此
來到日本的外國人經常會感到困惑,日本人很親切,可是為什麼在電車上就是不讓座。
這跟日本人親不親切無關,而是不喜歡惹是生非卻又在意他人眼光的日本人,在電車裡面為了不要被認為是正義魔人,心裡不斷掙扎,可是又遲遲開不了口,或者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搭乘公共交通運輸時,要讓座給老年人或身心障礙者,這是非常理所當然的事。日本人也知道這是正確的行為,但是日本社會對於讓座與否並沒有什麼「約束力」。所以,我行我素的年輕人或是疲倦的上班族,在電車上一看到老年人站在眼前,就裝睡或者是埋首在手機螢幕上,擺明就是不讓座。就算知道他們是裝的,但是周圍的人也都不會說什麼,而且老年人也不會主動說:「年輕人,起來讓座給我這個老人家」。這點就和台灣很不一樣。
「食文化」大解析
大阪曾舉辦一個珍珠奶茶的活動,當時用了在日本掀起熱潮的珍珠奶茶,製作飲料和料理。黑糖珍珠奶茶、珍珠花生湯這些還好,但甚至還推出了珍珠水餃、麻婆豆腐珍珠飯、珍珠鹹酥雞之類的料理。
網路上,台灣人的反應很有趣,像是「日本人不要玩食物好嗎」、「快點住手……珍珠不是這樣用的」、「珍珠鹹酥雞是怎樣啦,不要亂搞好嗎」……。我的感覺也是「太離譜了」。但是冷靜一想,正因為是日本人,才會嘗試不同的方式來料理珍珠吧。在台灣也有很多令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壽司,還會在飯上放著肉鬆跟皮蛋,許多日本人也對此懷抱疑問。
但我還是希望在日本做「台灣味」料理的人,盡量做到跟台灣道地的味道相近。
★每本書皆附有作者印刷燙銀簽名+給台灣讀者的感恩祝福金句
誠摯推薦
作家、評論家 胡忠信 /《中央社》社長張瑞昌 /作家張鐵志
作者簡介:
野島剛
資深媒體人、作家,大東文化大學特聘教授。1968年出生,就讀日本上智大學新聞系期間,曾赴臺灣師範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交流學習。1992年畢業 後,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擔任駐新加坡、臺北特派員。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後擔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擅長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
2016年開始成為自由媒體人,2019年就任大東文化大學特聘教授。著有《伊拉克戰爭從軍記》、《兩個故宮的離合》(聯經)、《謎樣的清明上河圖》 (聯經)、《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聯經)、《台灣十年大變局:野島剛觀察的日中台新框架》(聯經),以及《銀幕上的新台灣:新世紀台灣電影中 的台灣新形象》(聯經)、《故宮90話》(典藏藝術家庭)、《日本人默默在想的事》(時報)、《原來,這才是日本》(時報)、《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台灣人》(游擊文化)、《野島剛漫遊世界食考學》(有方文化)等多部作品。目前為 《蘋果日報》、《天下雜誌》、《報導者》與《轉角國際》專欄作家。
2014年將中文漫畫《中國人的人生》譯為日文,榮獲日本文化廳藝術祭漫畫部門優秀作品獎;2016年以《台灣十年大變局》原文著作『台湾とは何か』榮獲樫山純三賞;2018年榮獲臺灣第17屆卓越新聞獎,創下史上首次外國人獲獎的紀錄。
章節試閱
好想吃滷肉飯、做腳底按摩!我得了「台灣缺乏症」
三個月來(註:本文寫於5月中旬。),我無法去台灣,哈日族也不能來日本,雖然被疫情阻隔,日本人卻比從前更認識台灣,我不斷思考,為什麼日本防疫遠輸台灣?
老實說,跟那些因為這次的緊急事態宣言而失業、減薪、無法上學的人比起來,我的狀況還算可以。寫作本來就是在家或職場上獨力為之的工作,一個星期都沒有與人見面也不稀奇。工作量沒什麼太大的影響,因此我也沒打算大吐苦水。
只是,無法去台灣真的很痛苦。自從我二〇一六年離開《朝日新聞》的工作,就每個月或每兩個月到台灣一...
三個月來(註:本文寫於5月中旬。),我無法去台灣,哈日族也不能來日本,雖然被疫情阻隔,日本人卻比從前更認識台灣,我不斷思考,為什麼日本防疫遠輸台灣?
老實說,跟那些因為這次的緊急事態宣言而失業、減薪、無法上學的人比起來,我的狀況還算可以。寫作本來就是在家或職場上獨力為之的工作,一個星期都沒有與人見面也不稀奇。工作量沒什麼太大的影響,因此我也沒打算大吐苦水。
只是,無法去台灣真的很痛苦。自從我二〇一六年離開《朝日新聞》的工作,就每個月或每兩個月到台灣一...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錄
推薦序站在孤峰頂上的二刀流張瑞昌
作者序 台灣和日本,在「施」與「受」之間
日本人眼中的台灣
好想吃滷肉飯、做腳底按摩!我得了「台灣缺乏症」
我在台灣搭計程車常覺得很受傷,直到遇見一個唱演歌的運將
唐鳳在日媒受寵的理由
九份是否為神隱少女的舞台?
日本按摩為何變得比台灣廉價?
台灣人會喜歡免治馬桶嗎?
借鏡日本地方觀光,讓旅客走出台北
觀光或環保?台灣天燈的功與過
誠品在日本瞬間成名的秘密
人數翻二十倍!日本高中海外教育旅行瘋台灣,他們來學什麼?
台灣人為何不把故宮視為「台灣之光」?
鄭...
推薦序站在孤峰頂上的二刀流張瑞昌
作者序 台灣和日本,在「施」與「受」之間
日本人眼中的台灣
好想吃滷肉飯、做腳底按摩!我得了「台灣缺乏症」
我在台灣搭計程車常覺得很受傷,直到遇見一個唱演歌的運將
唐鳳在日媒受寵的理由
九份是否為神隱少女的舞台?
日本按摩為何變得比台灣廉價?
台灣人會喜歡免治馬桶嗎?
借鏡日本地方觀光,讓旅客走出台北
觀光或環保?台灣天燈的功與過
誠品在日本瞬間成名的秘密
人數翻二十倍!日本高中海外教育旅行瘋台灣,他們來學什麼?
台灣人為何不把故宮視為「台灣之光」?
鄭...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