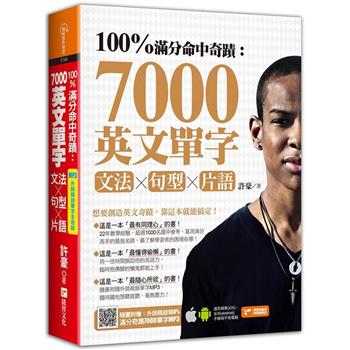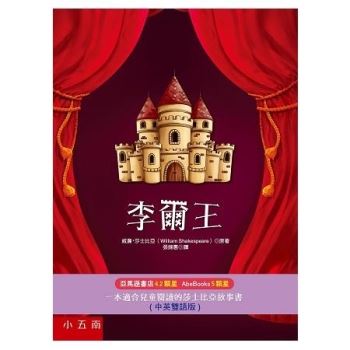壹・童年時期
我出生在戰爭時代,我的童年,簡單一句話,就是「吃不飽,但是很快樂」。
我家在屏東縣潮州鎮的三角公園旁邊,位置很靠近小鎮的中心,火車站就在附近,我爸爸在車站附近開糕餅店,養活我們一家。
早期我父母那個年代,因爲沒有節育觀念或避孕措施,家家戶戶都生得很多,光是我們家,就有八個小孩,為了養活一大家子,爸媽忙著做生意養家,根本沒空管我們,從小,我們就得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當年那個時代,日本當局對米、糖、油、魚、肉、青菜等,實施配給,物資缺乏,加上我們家八個小孩八張口,飯一拿出來,一下就吃光光,所有菜都是用搶的,誰要是動作慢、挑食就沒得吃了。
戰後台灣光復初期,大家日子都過得很苦、很艱難。
因為才剛打完戰爭,物資很缺乏,很多人家裡沒錢買不起米,有些同學帶來學校的便當,就混很多蕃薯籤,整個便當黃色比白色還要多。
一般家庭過年才有新衣服、新鞋子穿,有些人家境不好沒那麼多錢買衣服,小孩子又長得快,乾脆把美軍美援送來的麵粉袋、肥料袋,當衣服穿。
當時因為窮,我都打赤腳,很少穿鞋,乾淨白布鞋走在泥土路上,一下子就髒掉,所以我好珍惜,帶去學校頂多穿一下,主要是給老師檢查用的,平常根本捨不得穿,小心翼翼收著,就怕弄髒穿壞。
現在回想,我的童年真的是一段很愉快、沒有壓力、充滿歡笑的快樂時光。
奇妙的是,在那樣不受限制的環境裡,我反而發展出自律、獨立、負責任的性格,這點大概連我爸媽也沒有想到吧!
還記得我初二那年,學校規定學生上台表演話劇,不是在自己班上隨便演演那種,而是要站在開朝會時的大禮堂,演給全校上百名師生看,當時我們那個年代,不流行什麼舉手自願上台之類的,一切都是由老師指定。
為了應付學校的演出,也為了吸引全校的眼光,我們班導師劉志江親自操刀,寫了一齣名叫《矮小博士》的劇本,內容主要是講醫生怎樣幫患者看病、治療,中間鬧出一堆笑話,很輕鬆的歡樂喜劇。
演完了「假」博士(Doctor),背了一大堆醫學名詞,把病人從死神手上救回來,那種成就、滿足的愉悅感,無法形容,慢慢地,我對「真」醫師(Doctor)起了興趣,「當醫師」這個念頭,開始在我心中慢慢萌芽……
正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七十多年前,劉老師點了我主演《矮小博士》,可能連老師都不知道,他播出了一小顆種子,在我心中發芽長大,造就了我踏入杏林、濟世救人長達一甲子這條路。
話說當年,我的大哥,不分晝夜懸樑刺股,最後考上台大藥學系,僅僅只差五分,就能上台大醫學系。
大哥北上念書之後,看到他的機會變少了,不過,他放假時偶爾會帶同學來家裡玩,大哥的同學念電機系、藥學系、醫學系的都有,他們天南地北聊學校的點點滴滴,比如說功課有多繁重、上課老師怎麼嚴格要求,還有講一些追女生、耍曖昧、談戀愛的事情。
我愈聽愈嚮往大學生活,好想親自到「最高學府」一探究竟。
帶著這份嚮往,有一年寒暑假,我上台北去找大哥。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哥哥帶我去學生餐廳用餐,我看到每個人端著鐵盤,井然有序地排隊等著打菜,隔壁不同桌的台大學生邊吃邊討論病理,好像對醫學有用不完的熱情。
第一次逛台大,我深刻體驗到:「原來這就是菁英啊!」
回家之後,我比平常更加倍努力苦讀,最後不負眾望,考上第一屆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
我能夠順利考上醫學院,一部分是由於我的努力,另一部分也要感謝哥哥的分享,帶給我的刺激和啟發。
貳・求學時期
身為婦產科醫師,我忍不住想要回顧一下「台灣接生史」。從沒有執照全憑經驗的先生媽(接生婆)、日本政府培育出來的助產士,到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帶動西醫盛行,終致助產士沒落改由婦產科醫師引領風潮,這時代的演變,我有幸參與其中。
當年,要進婦產科真的很難,因為成績數一數二的學生,都喜歡選婦產科,向來喜歡挑戰的我,當然也不例外。雖然婦產科醫師要肩負母親與孩子的生命跟健康,責任非常重大,但是,當新生命呱呱落地的那一刻,同時幫助兩條生命,創造幸福喜悅,這種滿足和快樂,實在無法用言語形容。
除了難以言喻的成就感深深吸引我之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促使我立志當婦產科醫師,就是拜師在徐千田大將的門下。
我的恩師徐千田教授,是享譽國際的婦產科名醫,被稱為「世界五大子宮頸癌手術專家」,一九六九年,他應世界外科學院之邀,到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做專題演講並示範手術,一九七四年,他獲頒美國婦產科學院榮譽院士,是全球獲此殊榮的第三人。
我在醫學院最後一年,分配到市立中興醫院(現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實習,一畢業,接著進入中興醫院當住院醫師。
當時學生們都習慣用日文稱徐千田教授「大將(Taisho)」,大將不只是臨床名醫,對學生的要求更是出了名的嚴格。
念完醫學院,從見習醫師(Clerk)、實習醫師(Intern),到住院醫師(Resident),差不多也二十八、二十九歲,現在公私立住院醫師,每個月約有五到六萬薪水,大家可能很難想像,在五、六十年前,我們那個年代的住院醫師,通常都沒有半毛薪水,為了過日子,要嘛靠家裡人接濟,不然就得瘋狂兼差。
那時候沒有薪水,住院醫師只能領值班費一晚五十元,因為人多,一個月三十天不可能天天都是我值班,若能值到十五天,就算運氣很好了,但頂多也只能領個七百五十元。
雖然只有微薄的值班費可以領,但那時沒有人敢喊一聲苦或累,反而打起十二萬分精神,用眼睛看、用耳朵聽,不管什麼都拚命學,我們奮鬥的目標只有一個:盡快學得一技之長,早日獨當一面。
三百元或是兩萬的工作,你會選哪一種?
做一個月就可以賺到四年薪水的職位,有哪個傻瓜不接?
那個人就是我。
在我們那個沒有薪水可領,只能到處兼差看病的「兼職」年代,每位住院醫師都巴望著有天能被總醫師點名,指派去代診,雖然頂多只有一、兩個月時間,但代診一個月能賺到一萬元,對口袋空空的住院醫師來說,簡直是天大的恩惠。
不過,代診機會不多,再加上排在我前面資深的前輩,有好多人,跟我同期的住院醫師少說也有十幾個人,想要得到總醫師的青睞,真的很不容易。
我還記得,那時我才R2(住院醫師第二年),總醫師指派我到宜蘭醫院代診,聽到消息的那一瞬間,我感覺自己好像中了愛國獎券頭獎一樣,開心得要飛上天了。
當時宜蘭新生綜合醫院的院長,是前衛生福利部部長邱文達的父親邱永聰先生,邱院長平時要顧整家醫院,又要準備參選議員,忙得分身乏術,所以請徐千田大將幫忙介紹好手,到宜蘭新生綜合醫院代診。
沒多久,邱永聰院長如願當選宜蘭縣議會議長,他直接去找徐千田大將,拜託他放人,邱永聰議長表示他很愛才惜才,他想聘請我去宜蘭新生綜合醫院,擔任婦產科專科負責人。
邱永聰議長認為,我代診那段期間,工作認真負責,醫病關係也經營很棒,他對我印象十分深刻,很滿意我的表現,還記得有一天他跟我說:「你這邊三、四百塊不要賺了,來賺我這裡,我用七兩黃金聘請你!」
七兩黃金有多大?在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一兩黃金大概三千元台幣,算一算七兩黃金差不多兩萬多塊了耶!想想我值班一晚才五十塊,就算值班值到死,也不可能有這麼多,七兩黃金真是一筆天文數字。要去賺七兩黃金?還是繼續留在中興醫院修業?我左右為難,苦惱好久,最後決定聽聽家人的意見。
一聽到「每個月賺七兩黃金」這個數字,電話那頭的老爸非常高興,笑得好大聲,說我終於熬出頭了,連聲鼓勵我快點去上班。
我想不想賺錢?老實說,想啊!我當時到處兼職,一個月差不多賺一萬五,其中一萬塊拿回家給爸爸,我也想有能力多拿一點錢回家,老爸培養兒子這麼久,除了很感謝他,也想讓他有面子。但是回頭我又想,自己才學到R2,就這樣貿然出去獨當一面,R4該學的技術都沒學好,剖腹產不會,拿子宮也不會,如果我的實力還不夠水準,就直接拿槍上陣,對病患、對我都不是一件好事。
思前想後,我還是覺得自己還是應該再多蹲一陣子,把實力培養得更好再說,於是我毅然決然放棄挖角機會,謝絕邱永聰議長的好意。
被人賞識固然高興,但我還是決定摸著自己的良心,在「正確的選擇」跟「容易的選擇」兩者當中,選擇對自己最能交待的那一個。
參・成家立業時期
很多人不知道,「先生娘」叫起來好聽,但當起來可不是那麼一回事。
人前光鮮亮麗,背後卻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辛酸,特別是婦產科或外科醫師的另一半,先生總是二十四小時待命,醫師娘差不多就是「偽單身」,有老公也等於沒老公,家裡大小事都得靠一人操持,如果本身不夠獨立,很難撐下去。
幸好,我的太太本身就是一個能力強、獨立自主的女性,英美犧牲她大好的事業前途,一肩扛起家庭事務,悉心教導三位兒女,當我堅強的後盾,讓我在行醫過程中能夠全力以赴、沒有後顧之憂。
一九七○年代開始,許多人希望到台北闖一番人生事業。在那個年代,北漂是一種自主性的選擇,是追逐夢想的美好過程,也是台灣人刻苦耐勞、力爭上游的精神。
值此同時,我和英美成為北漂小夫妻。
我和英美沒跟家裡拿半毛錢,兩個年輕人憑著一股傻勁和勇氣北上打拚,小夫妻胼手胝足,縮衣節食,常常兩餐併一餐吃,苦不堪言。然而,時隔五十年年,思緒再次回到那一段寄人籬下的日子,頗有苦盡甘來、倒吃甘蔗的滋味⋯⋯
很多人問我,當年我北上打拚,為何不選在「首善之都」台北市開業呢?
之所以落點板橋,其實是有一段淵源的。
我們決定落腳板橋後,剛開始,先在湳雅夜市的「巷仔內」租房子,為何我不租大馬路上的店面?因為那時候地點好的街邊、三角窗地帶,租金每個月至少都要六千塊,我不敢一下子就租那麼貴,就湊合著先租「巷仔內」,只要兩千五。
因為我們不跟爸媽拿錢,手邊現金不多,剛開業時,婦產科診所相關設備都沒有買新的,而是買退休醫師二手的設備來用,在草創之初,我們什麼都很省。
慘的是,以前房子隔音不好,來我診所分娩的產婦,每每哭得驚天動地,還常常在半夜時分,吵到左鄰右舍,我就天天被房東罵,罵到後來,房東連病人一塊罵,什麼難聽的三字經、五字經都有。我跟房東、鄰居失禮賠不是了半年,想想這樣下去不行,最後我和太太輾轉找到目前在南雅南路上的「起家厝」。
值得一提的是,「蕭中正醫院」招牌那五個大字,鐵畫銀鉤,龍飛鳳舞,是我太太英美親自書寫的,別有一番意境。
我行醫將近一甲子,始終以「視病猶親」的態度和理念,對待每一位病人,這也是蕭中正醫院一直以來的堅持。在還沒有健保的年代,我的診所時不時會有經濟能力不佳、付不出錢的病人上門求診,我總是想「先醫再說」,這樣的例子還不少,具體的數字我沒有印象,不過,醫院內部帳目經過核對,發現這些費用加一加至少也有上百萬元之多。
所謂「醫者父母心」,我想,人總是有狀況好跟不好的時候,病人也不是故意交不出錢,既然如此就罷了,我想我能做到的,就是這樣吧。「視病猶親」不僅僅是一句口號,它就像我的DNA細胞一樣,真實應用在我的行醫生涯裡。
是醫療不當才會有糾紛嗎?那可不一定。我行醫超過四十年,如果要說我有什麼最自豪的事,應該就是「醫糾少」吧?!次數不超過兩雙手十根手指頭!話雖如此,我印象中有一件醫療糾紛,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後法院判定我的處置沒問題,不起訴,可是前前後後也弄了兩、三年。這也是唯一一件,讓我太太英美擔心害怕長達兩年多的醫療糾紛。
開業一陣子,蕭婦產科在板橋闖出名氣後,我們好像被黑道盯上,開始陸陸續續接到勒索電話。打電話來恐嚇勒索的,可能是準備跑路的道上兄弟,也可能是瘋狂簽賭的亡命之徒,反正他們毫無顧忌,有膽找我們賭一把,萬一我們給的答案不合對方心意,搞不好會來個魚死網破。每次對方有什麼要求,我都先應下來,電話一掛,立馬報警處理。
警察也很好,一聽到報案,立刻派便衣刑警趕到我們醫院保護,小孩上下學本來就有司機接送,還沒抓到人的那幾天,我們都麻煩刑警一起坐上車保護。還好,每次接完勒索電話,大概不到十天歹徒就落網,不然真的是如芒在背、寢食難安。
我記得當時民國七十三年左右,家裡妹妹弟弟一個十二歲、一個九歲,都還在國中、國小階段,仍是很需要照顧的年紀,英美沒辦法陪乃彰出國唸書,我們兩個都捨不得讓大兒子獨自一人去美國當小留學生。
那時候,英美使盡手段,百般阻撓,好說歹說,希望他打消出國唸書的念頭,等大學之後再說,英美甚至連「適應不良就得馬上回來」這些難聽的話都說出口了,但乃彰這孩子依舊不為所動。我那時也想不通,怎麼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可以這樣執著、這樣無懼?
乃彰在美國一路從國中、高中、大學醫學院到後來念博士,這十多年來,沒有爸媽陪在身邊,他不但沒有變壞,每一個求學階段,乃彰的學業成績表現優異,社團生活精彩豐富,人緣又好。直到二○○○年後,乃彰學成歸國,之後子承父業,成為現在蕭中正醫療體系的蕭乃彰「營運長」,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肆・醫院創立轉型時期
百年企業要傳承,一定要「與時俱進」,我的醫院也是。
再來說說,我為何能夠在大醫院船堅炮利、健保制度腹背受敵之下,還能撐下來。
姑且不論健保制度該如何改,怎麼改都有人不滿意。對我來說,我最在乎的是三件事,如何把病人照顧好,如何讓院內醫護同仁開心工作,如何讓醫院長治久安,這三點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既然如此,蕭中正醫院不能倒,帶領醫院成功轉型,是我的首要之責。
一家四十年老店想要轉型並不容易,有一度我曾經考慮過轉型做生殖醫學,也就是治療不孕的方向,後來因緣際會沒往那邊走。
二○○三年(民國九十二年)之後,我的大兒子蕭乃彰回來接任營運長,開始引進呼吸照護、洗腎等慢性醫療長期照護,二○○四年更名為「蕭中正醫院」,並創建呼吸照護病房,我們也在新北市三峽,打造台灣第一個「醫養結合」的醫院──清福醫院。
另外開了「新福星診所」服務需要洗腎的病人,甚至成立自己的車隊以及祝三實業有限公司,專門接送病人來院,蕭中正醫院從地區型的婦產科專科醫院,成功轉型成為區域型的蕭中正醫療體系,我的頭銜,也從「院長」升格為「總裁」。
就像其他百年企業,遇到轉型危機,企業二代臨危授命,接手上陣,常常跟企業一代不合、有代溝,我們家也是一樣。
我們父子就像電玩遊戲一樣,雙方壁壘分明,他攻,我守,營運長PK總裁,你來我往,每天上演不一樣的攻防。後來我也慢慢接受乃彰的意見,畢竟他是營運長,也是接班人,我得相信他,也必須尊重他。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改變久了之後,我才慢慢發現,乃彰的建議,其實很宏觀,他的觀念很新,跟得上台灣現在的健保制度,以及國際趨勢,當年我覺得他太急、太求快了,但就結果來看,說不定這個「急」在這個時代剛剛好。
經過十多年的轉型和蛻變,蕭中正醫療體系持續成長茁壯,這段逆轉勝的奮鬥過程,可以說是一本「台灣基層醫院完全生存手冊」,我們所做得的一切一切,其實是為了求生存,不得不另闢一條新路,靠著一步一腳印打拚出來的。我相信,我們的轉型故事,可以讓全國其他基層醫療院所同業們,當作借鏡和參考。
伍・家人支持成就了我
民國一○七年三月十三日這天,我滿八十歲,這天,英美送給我一個「沉重」禮物──她要去動大刀。
也許是這些年來她太過操勞,也許是人體老化必然過程,英美的第三節胸椎壓迫到她的脊椎神經,明明沒壓迫前都還健步如飛,民國一○六年的十二月,一切都還好好的,哪知道突然有一天英美痛到不能自已,才短短兩個星期她就完全不能走路了!
英美剛手術完住在林口長庚醫院那陣子,我們全家老少還排輪值表,每天都有人按照時段,到醫院輪流陪伴、守夜,現在回想起那段看護英美的日子,大夥兒比上班還要準時!
英美為了能夠擺脫輪椅,重新站起來,每天復健至少一小時以上,她非常用心,全力配合,連復健師都勸她「如果真的很痛就先緩一緩、不用急」,不過,英美還是堅持該做的都一定要做完!
慢慢地,英美從原本無法下床,持續復健到能夠短暫站立,再進一步恢復到可以靠拐杖走路,這段漫長艱辛的復健之路,我深深感覺到她的努力會戰勝一切。
人生,真的很奇妙,要不是乃彰當年堅持單飛到美國當小留學生,最後學成歸國,經過各方的磨練,練就一身醫療管理長才,佐以他的高瞻遠矚、宏觀格局,回台灣繼承衣缽,我的人生,可能就僅止於蕭中正醫院的「院長」而已,不太可能跟「總裁」劃上等號,也不可能承擔數百個家庭這樣重大的企業社會責任,或是照顧廣大需要長期照護的慢性病人。
而我的兒媳劉惠敏,和乃彰在美國唸書時認識,惠敏取得美國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系以及公共關係學系雙碩士,她和乃彰返國後,幫忙輔佐乃彰事業,相夫教子、家庭和樂,是一個稱職賢慧的好媳婦。
我的事業雖然忙碌,但對於三個兒女的關心還是盡我所能去做──這都要感謝英美很努力營造我們親子相處時光。
我讓三個孩子從小進診間、產房,觀察爸爸的工作內容和環境,多少起了耳濡目染的作用,大兒子乃彰、小兒子彥彰都走上白袍之路,至於夙倩,她在高中時,就表達她將來不想從醫的志向,她要唸心理系,最後如願考上台大心理系,到美國唸書時,有哥哥乃彰照顧,我和英美都很放心,後來夙倩順利拿到心理學碩士,回國擔任台安醫院兒童發展復健中心臨床心理師。
夙倩和女婿是國中同學,我們兩家住得很近,女婿的父親也是板橋地區的婦產科名醫,地緣關係加上背景相似,這段姻緣可以說是前世註定。
女婿是一名牙醫,他和夙倩兩人興趣相仿,兩人都是圖書館「忠實之友」,他們多年來累積的借書紀錄,在新北市絕對名列前茅,女婿更是旅遊美食達人,兩人夫唱婦隨,琴瑟和鳴。
我的小兒子彥彰,現在擔任台北林口長庚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拜在美國顯微重建外科醫學會至高榮譽教授、中研院院士、國內整形外科名醫教授魏福全的門下,深受栽培。
彥彰獲得魏福全院士推薦,陸續飛到美國芝加哥大學、亞歷桑納大學、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等,向Dr. Gary C Burget、Dr. Frederick Menick,以及Dr. Dean Toriumi等世界頂尖一流鼻部整形重建大師、鼻部美容醫師學習,專注鼻部的整形、美容與重建等研究領域。
林口長庚醫院官網形容彥彰是「鼻整形之一公釐的雕塑家」,彥彰自己也說:「我將還給所有人鼻子最重要的兩個功能──呼吸和美觀。」從這些小地方就可以看出,彥彰不只是一位醫師,還是一名文青,甚至可以說是一位美學藝術家。
時間過得飛快,跟我同期的同學或是婦產科同業們,他們都退休了,甚至,有不少比我還年輕的醫師,也紛紛離開這行。但在我的腦海裡,從來沒有浮現過「退休」這兩個字。
我畢生最大的幸福,應該是娶到好太太、生了三個好兒女、娶了兩個好媳婦、找了一個好女婿、擁有六個好孫兒吧!
說起來,我這一生能夠有所成就,家庭真的給我很大的力量,不管是我的太太英美,還是出類拔萃的兒女們,都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
人生走到這個階段,事業安定,兒孫自有兒孫福,我的一生圓滿順遂,接下來只期盼蕭中正醫療體系能夠綿綿不絕、永續經營,家人平安健康、幸福快樂,就是我最大的心願。
| FindBook |
有 14 項符合
中正醫路:從醫師到總裁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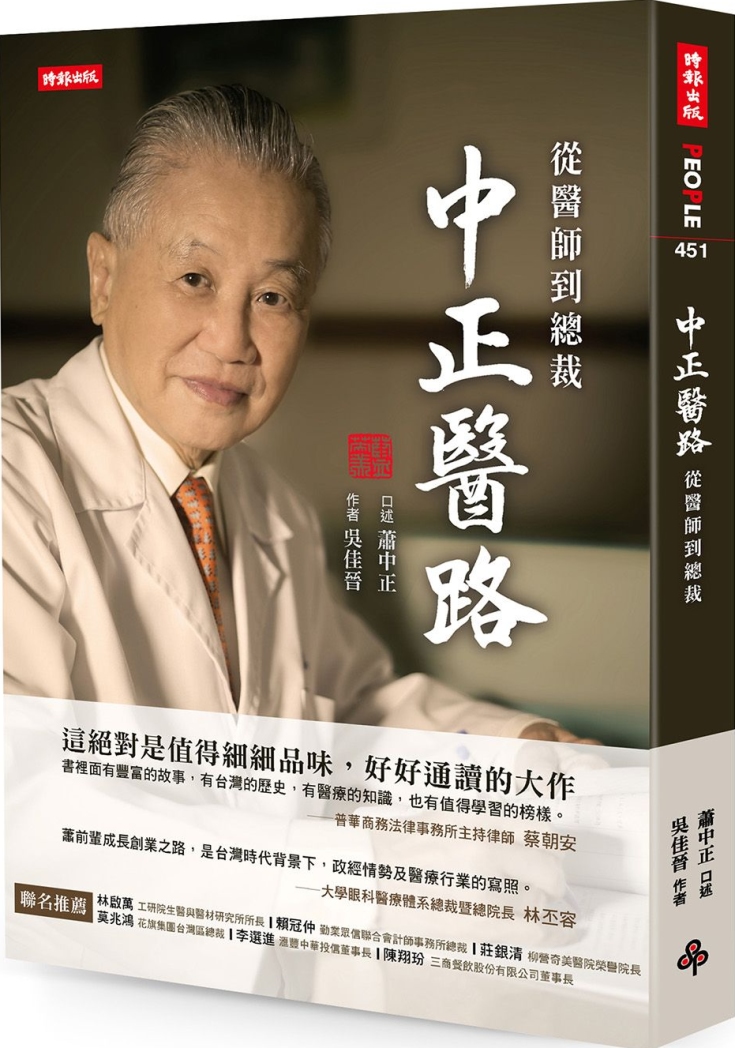 |
中正醫路:從醫師到總裁 作者:蕭中正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10-2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04頁 / 14.8 x 21 x 1.6 cm / 普通級 / 部份全彩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正醫路:從醫師到總裁
從年少到耆老的奮鬥歷程。
一部從戰後民生凋敝到經濟起飛,
見證台灣醫療史發展,一路改革轉型的自傳故事。
本書以自傳方式,描述蕭中正總裁在「醫路」上一生懸命的奮鬥史,
全書五個章節,生動刻劃出一名仁慈濟世的醫者,堅忍奮鬥、激勵人心的生命歷程。
從醫師到總裁,從「蕭婦產科」到「蕭中正醫療體系」,
這本《中正醫路》,不僅僅是蕭中正醫師夙夜匪懈的人生路,
也是蕭中正總裁留給新生代從醫志者的一部醫路典範。
所謂的生命,是「從零到有」的過程。而婦產科醫師所做的,就是站在生死關頭的第一線,親手迎接新生命,替每一位誕生的新生兒,寫下人生的第一篇序章。
一名懸壺濟世的婦產科醫師,生長於動盪不安的戰爭時代,揭開他生命序章的,是轟隆隆的無情砲火聲,但他的童年,並未被烏煙瘴氣的戰火蒙上灰塵,反而砥礪出他自律進取的樂觀性格。
童年演出的一齣的話劇,在他心中悄悄萌芽;兄長考上台大醫藥系,帶給他無限啟發,因而選擇了婦產科醫師為志業,展開他數十年堅定無悔的從醫之路。
醫路上,深受啟蒙恩師──徐千田大將指導提攜,接生救死,風雨兼程,奠定了觸手生春、聲名遠播的醫術;與妻子伉儷情深,夫妻倆胼手胝足,風雨同舟,在最艱困的環境之下,創立了蕭婦產科。從蕭婦產科到蕭中正醫院,又是一段「從零到有」的奮戰歷程,走過對簿公堂的醫療糾紛,遭遇過驚心動魄的恐嚇勒索,扛著種種壓力,一路走向蕭中正醫院的七十二變。
前人建功立業,最大的欣慰,莫過於後繼有人。全民健保帶來的衝擊、地區醫院為求生存不得不求新求變的改革,蕭中正醫師也面臨到了醫院的轉型時期,所幸長子歸國接下衣缽,在父子同心、其利斷金的並肩作戰下,全台首家「醫養結合」的醫療團隊──蕭中正醫療體系,終於應運而生。
時至今日,蕭中正總裁年逾八十,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舊秉持行醫濟世的初心,在醫路上全心奉獻。這本傳記,無疑是他行醫生涯的回憶錄,用他爽朗樂觀的口語自述,透過筆者生動淋漓的描寫,帶我們走進時光隧道,一同回顧他勵志感人的中正醫路……
【專業推薦】
中央研究院院士/魏福全
中華民國考試院前院長/伍錦霖
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暨立法委員醫師/邱泰源
前衛生福利部前部長/林奏延
漢東醫院院長/張漢東
中正兄不僅是位成功的開業醫師,在專業的婦產科上享有盛名,也是傑出的醫院經營者、醫師企業家。從中正兄身上,我看到人生不同風景與無限可能。──中央研究院士/魏福全
從診所到地區醫院,再成功轉型為區域型的醫療體系,結合慢性醫療的長期照護,貼心服務病患,這就是中正兄持續追求其一生的價值理念──「行醫濟世」所努力獲致的成果,堪稱杏林典範。──考試院院長/伍錦霖
此書可視為蕭中正醫師的自傳,在書中,把他從小的求學過程,如何立志當醫師、如何成家立業,如何把視病猶親當作行醫的理念與核心價值,做一詳實的紀錄,讓年輕的一代能理解前人的努力、奮發、濟世的理念及理想。──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暨立法委員/邱泰源
這本《中正醫路》非常推薦給所有在醫療體系工作的夥伴,書中學習成為醫師的過程,足以作為大家的典範與標的。──前衛生福利部部長/林奏廷
蕭醫師童年歷經日治時代、二次世界大戰及蔣介石總統三個時代,當時台灣生活非常困苦,刻苦耐勞、富有創業精神的父母影響了他的一生。長子留美取得博士回國接棒,後繼有人。蕭家的轉型故事,可為基層醫療院所開業們的借鏡和楷模。──漢東醫院院長/張漢東
【各界讚譽】
臺大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副院長/王鶴健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總裁/賴冠仲
大學眼科醫療體系總裁暨總院長醫師/林丕容
工業技術研究院生醫與醫材研究所所長/林啟萬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院長/林慶豐
柳營奇美醫院榮譽院長/莊銀清
大葉大學消防安全學程暨研究所兼任教授/何岫璁
新北市議會議員/何博文
靜宜大學校長/唐傳義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蔡朝安
永豐餘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何奕達
花旗銀行董事長暨台灣區總裁/莫兆鴻
滙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選進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翔玢
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會長/吳志揚
凱基銀行法務長/章勁松
盛弘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弘仁
華能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謝文泓
為之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正道
作者簡介:
蕭中正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
這本自傳主要寫我年少至今的醫師生涯。想起曾經忙碌的婦產科現場,看到媽媽為肚內小嬰孩整夜哀嚎、渾身濕透、身心俱疲仍堅持撐過,最後喜中帶淚迎接新生命的到來,深深打動我,所以踏上婦產科醫師這條路。
我知道一段路途即將走完,雖有很多波瀾起伏,但心裡總想著可以為後來的人留下一些什麼。
毫無疑問,這是一本讓我自己時時感恩而內心坦然的記事。
始終如此。
現任:
蕭中正醫療體系院長兼總裁
徐千田防癌研究基金會董事
新北市防癌協會常務理事
台北市屏東縣同鄉會常務理事
台灣防癌協會理事
歷任:
台北醫學院婦產科臨床講師
台灣防癌協會常務監事
台北市立中興醫院總醫師、主治醫師醫師
吳佳晉
橫跨醫藥、影劇、財經新聞三大領域逾20年的資深媒體人。常為國泰、元大等多家金控分享公關實務經驗,現為自由創作者。
近年她投身社會公益,不僅擔任桃園、新店等地監所的教誨師,更與藝人唐從聖組「從心出花」隊,成為渣打銀行2019年公益馬拉松路跑代言人。
此外,她籌組八十歲企業家傳記團隊,為老一輩紀錄口述歷史,執筆《中正醫路》,是她邁向傳記作家的第一步。
個人著作:
《從負翁到富翁》
《錢滾錢》
《這一生,一定要有一張保單》
現任:
台中女中校友會監事
中女好會講公益平台發起人
華人領袖100貴人學平台內容長
歷任:
財經短片「姑姑up」主持人
中時電子報財經組主任
中國時報財經組主任
工商時報理財組副主任
章節試閱
壹・童年時期
我出生在戰爭時代,我的童年,簡單一句話,就是「吃不飽,但是很快樂」。
我家在屏東縣潮州鎮的三角公園旁邊,位置很靠近小鎮的中心,火車站就在附近,我爸爸在車站附近開糕餅店,養活我們一家。
早期我父母那個年代,因爲沒有節育觀念或避孕措施,家家戶戶都生得很多,光是我們家,就有八個小孩,為了養活一大家子,爸媽忙著做生意養家,根本沒空管我們,從小,我們就得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當年那個時代,日本當局對米、糖、油、魚、肉、青菜等,實施配給,物資缺乏,加上我們家八個小孩八張口,飯一拿出來,一下就吃光光...
我出生在戰爭時代,我的童年,簡單一句話,就是「吃不飽,但是很快樂」。
我家在屏東縣潮州鎮的三角公園旁邊,位置很靠近小鎮的中心,火車站就在附近,我爸爸在車站附近開糕餅店,養活我們一家。
早期我父母那個年代,因爲沒有節育觀念或避孕措施,家家戶戶都生得很多,光是我們家,就有八個小孩,為了養活一大家子,爸媽忙著做生意養家,根本沒空管我們,從小,我們就得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當年那個時代,日本當局對米、糖、油、魚、肉、青菜等,實施配給,物資缺乏,加上我們家八個小孩八張口,飯一拿出來,一下就吃光光...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推薦序
中央研究院院士/魏福全
從中正兄身上,我看到人生不同風景與無限可能
我認識蕭中正總裁約有二十多年,雖未能見到他整個精彩行醫生涯中辛苦耕耘、播種、萌芽及開始茁壯的那一階段,卻有幸能見證他現正志業終於成蔭,並得以傳承最精華的這一時刻。
中正兄不僅是位成功的開業醫師,在專業的婦產科上享有盛名,也是傑出的醫院經營者、醫師企業家。由於洞悉到健保制度、少子化及醫院大型化可能給開業婦產科帶來的衝擊,他早在廿多年前就有了跨業經營的理念,並進行應有的準備,終而造就了今天成果斐然的醫療志業!
其中,最讓我驚...
中央研究院院士/魏福全
從中正兄身上,我看到人生不同風景與無限可能
我認識蕭中正總裁約有二十多年,雖未能見到他整個精彩行醫生涯中辛苦耕耘、播種、萌芽及開始茁壯的那一階段,卻有幸能見證他現正志業終於成蔭,並得以傳承最精華的這一時刻。
中正兄不僅是位成功的開業醫師,在專業的婦產科上享有盛名,也是傑出的醫院經營者、醫師企業家。由於洞悉到健保制度、少子化及醫院大型化可能給開業婦產科帶來的衝擊,他早在廿多年前就有了跨業經營的理念,並進行應有的準備,終而造就了今天成果斐然的醫療志業!
其中,最讓我驚...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蕭中正醫療體系院長暨總裁
我老好命
用一句話代表我的一生?說起來很難也很簡單,我腦海裡直覺浮出「人生圓滿、一生順遂」這八個字,簡單來說,就是「老好命」啦!
古代儒家提出所謂的「三不朽」,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用現代的話來詮釋,可以理解為人生的三個最高標準。
三不朽當中,「立德」居首位,簡單地說,就是誠信做人。我一輩子行醫,最重視的就是醫德,這點我有自信。
我從念醫學系當學生開始,受過無數老師栽培、前輩指導,七年醫學院、實習醫師、住院醫師、總醫師到主治醫師,當時日子過得好艱苦,不過現在一...
我老好命
用一句話代表我的一生?說起來很難也很簡單,我腦海裡直覺浮出「人生圓滿、一生順遂」這八個字,簡單來說,就是「老好命」啦!
古代儒家提出所謂的「三不朽」,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用現代的話來詮釋,可以理解為人生的三個最高標準。
三不朽當中,「立德」居首位,簡單地說,就是誠信做人。我一輩子行醫,最重視的就是醫德,這點我有自信。
我從念醫學系當學生開始,受過無數老師栽培、前輩指導,七年醫學院、實習醫師、住院醫師、總醫師到主治醫師,當時日子過得好艱苦,不過現在一...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我老好命/蕭中正醫療體系院長暨總裁 蕭中正
推薦序
從中正兄身上,我看到人生不同風景與無限可能/中央研究院院士 魏福全
熱血的醫生魂澎湃/考試院院長 伍錦霖
醫德典範/前衛生福利部部長 林奏廷
蕭家轉型,基層醫療典範漢東醫院院長 張漢東
醫者仁心/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暨立法委員 邱泰源
壹童年時期
我的父親母親
我的童年
我與死神擦身而過
矮小博士
哥哥是我的偶像
貳 求學時期
中國醫藥學院的第一屆醫科生
我決定當婦產科醫師
我的恩師徐千田大將
我在中興醫院當住院醫師的一千天
拒絕七...
我老好命/蕭中正醫療體系院長暨總裁 蕭中正
推薦序
從中正兄身上,我看到人生不同風景與無限可能/中央研究院院士 魏福全
熱血的醫生魂澎湃/考試院院長 伍錦霖
醫德典範/前衛生福利部部長 林奏廷
蕭家轉型,基層醫療典範漢東醫院院長 張漢東
醫者仁心/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暨立法委員 邱泰源
壹童年時期
我的父親母親
我的童年
我與死神擦身而過
矮小博士
哥哥是我的偶像
貳 求學時期
中國醫藥學院的第一屆醫科生
我決定當婦產科醫師
我的恩師徐千田大將
我在中興醫院當住院醫師的一千天
拒絕七...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