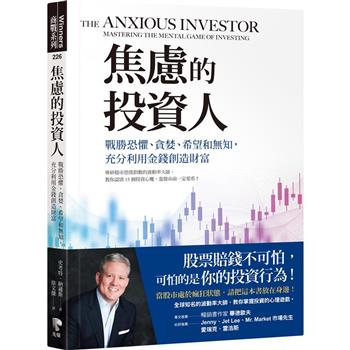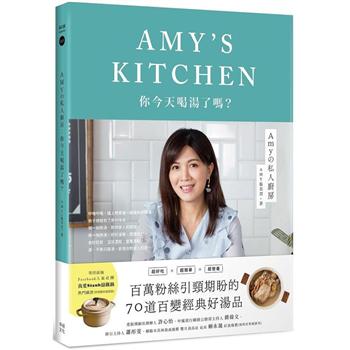圖書名稱:愛的教育
恩里科是義大利一名三年級的小學生,從開學的第一天起,他認識了老師和各式各樣的同學,像見義勇為的加羅內、努力學習的斯塔爾帝和身體殘疾的科羅西等,同學之間偶爾頑皮搗蛋、有時友愛相助,隨著日常的相處,彼此的情感逐漸變深……。恩里科以日記型式記錄發生在他身邊、學校和家庭中的生活點滴和見聞,以及老師在上課時分享的感人故事和父母的溫馨叮嚀等,共一百篇精采的故事,文字淺白樸實,卻洋溢著純真動人的同學、師生和親子情誼,是每個孩子和曾是孩子的大人一生必讀的經典。
作者簡介
艾德蒙多.德.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1846-1908
義大利殿堂級的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奇蹟童書《愛的教育》作者,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生於義大利的一個小鎮,從小酷愛學習與寫作。
曾經參加解放義大利的戰爭,擔任過軍事刊物記者。後來周遊世界各國,撰寫了許多膾炙人口的遊記,記述各地的風土人情。
經典代表作《愛的教育》歷時八年心血完成,於一八八六年首次出版,隨即造成轟動,短短二十年就印刷高達三百多版,往後的百年依然持續暢銷,不僅成為義大利家喻戶曉的童書、歐美家長送給孩子的必備禮物,更在全球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總銷量突破兩千萬冊,並被改編成漫畫、動畫、電影,獲得高度的讚譽。
全世界的孩子,和曾經是孩子的大人,都能透過本書懂得愛的真諦,變得更堅強、更友愛、更善良。
如同作者亞米契斯所說:「凡是讀這本書的人,都無法抗拒它的魅力,將流下感動的眼淚……」
譯者簡介
張密
著名學者、翻譯家,一九五○年出生於天津。中國義大利語教學研究會前會長,現名譽會長;中國義大利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義大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義大利語翻譯研究會發起成員之一。
一九七六年畢業於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並留校任教。一九九九年六月、二○○五年十二月、二○一四年四月三次獲得義大利共和國總統頒發的榮譽勳章。
祁玉樂
知名學者,在義大利生活工作長達三十多年,是義大利政府承認並聘請的高級翻譯學者,曾任義大利總統、總理官方翻譯。
一九六一年生於北京。一九八六年畢業於義大利錫耶納大學文學系,一九九八年獲得羅馬睿智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居義大利。


 2022/05/22
2022/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