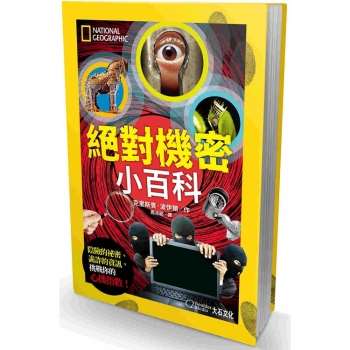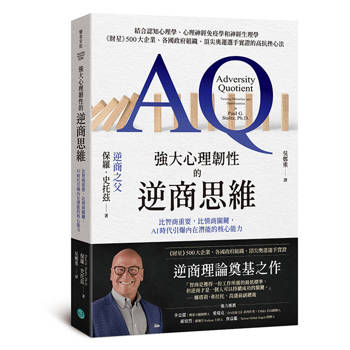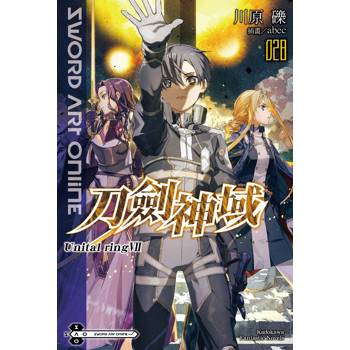圖書名稱:知識的癲狂
人類為什麼受知識吸引,同時又被它制約?
不相信真理的年代,求知的欲望如何為我們的心智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
──求索知識對人類存在的重要意義,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史蒂芬.康纳 啟迪思想之作──
徘徊在全知與無知之間,我們既永遠無法知道自己到底是誰,
又因知曉這項事實所帶來的屈辱而成為人類。
所謂的知識,必定讓我們明白自己對某些事物一無所知。
從過去到現在,許多人都曾思考過知識的力量及其局限之處,但很少有人想過「知識」這個概念對我們所產生的影響。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史蒂芬‧康納的《知識的癲狂》,探究人類心智如何受知識的吸引與制約,以及知識所引發的欲望、幻想、夢境與恐懼。這本書深入討論了人類的求知意志、對知識的迷戀與熱愛,以及情緒、求知渴望與知識之間奇妙而緊密的連結。人為什麼總想要「獲取知識」?為何我們能同時蔑視愚蠢,又神聖化「愚人」?康納藉由文學、哲學、宗教、歷史等多樣而令人目眩神迷的文本,求索知識對人類心靈、存在認同的重要意義。
這本書關注的是我們與知識的關係,以及對知識陷入瘋狂的世界所帶來的可能性和危險。在人工智慧蔚為風潮、不信任真理的後事實時代,康納的討論發展出一種豐富而細密、有時甚至令人不安的精神病理學。知識仍是力量嗎?它仍帶來權力與階級翻轉嗎?求知是人的本能,亦或終將成為一種精神疾病?康納幽默而鋒利的文筆,完整地為知識及人類的局限性進行了一場極富靈思的當代思想辯論。
作者簡介
史蒂芬.康纳Steven Connor
英國劍橋大學英語系教授以及藝術、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著作繁多,包括《膚之書》(The Book of Skin)、《蒼蠅》(Fly)、《空氣問題:飄逸的科學與藝術》(The Matter of Air: Science and the Art of the Ethereal)、《運動哲學》(A Philosophy of Sport)、《言外之意:嗚咽、悶哼、結巴與其他發聲》(Beyond Words: Sobs, Hums, Stutters and Other Vocalizations)。上述著作皆由英國出版社Reaktion Books出版。
譯者簡介
劉維人
自由譯者。從譯作出發,參與當代民主、公共討論等議題。譯有《世界上最完美的物件》、《被誤讀的哲學家》、《反民主》、《暴政》、《不穩定無產階級》、《憤怒與希望:網際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等。
warren1_liu@hotmail.com
楊理然
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哲學博士,交通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興趣為倫理學、政治哲學、藝術和翻譯。
li.ran.yang.tw@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