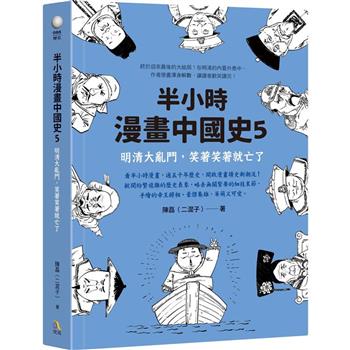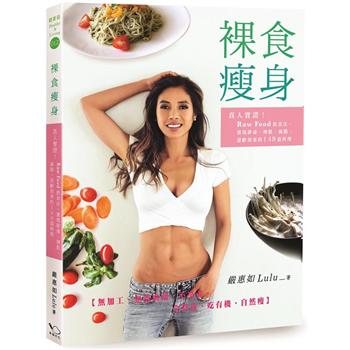第一章 尊嚴的政治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走到一半,世界政治發生劇烈的變化。
從一九七○年代初期到二○○○年代中期,出現了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歸類為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原本的三十五個增至一百一十多個。在這段期間,自由民主成了世界許多政府的預設形式—至少志在民主,就算沒有落實。
與這種政治制度的變遷並轡而行的是各國的經濟愈益相互依賴,即我們所說的全球化。後者得到諸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及後繼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等自由經濟機制之強力支撐,輔以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等區域性貿易協議。在這三十幾年間,國際貿易與投資的成長率超過全球GDP的成長率,而被公認為繁榮的最大驅動力。在一九七○年到二○○八年間,全球商品服務的產出增加三倍,成長幾乎擴及世界所有區域,而發展中國家赤貧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也從一九九三年的四二%降至二○一一年的一七%。兒童在過五歲生日前夭折的比率,則從一九六○年的二二%,降至二○一六年的不到五%。
但這種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並未造福每一個人。在世上許多國家,尤其是已發展國家中,不平等急遽惡化,致使許多成長的好處大多流向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既然成長與商品、金錢、人民從一地轉往另一地的數量增加息息相關,社會自然會出現大量顛覆性的轉變。在發展中國家,原本無電可用的村民突然發現自己住在大城市裡,看著電視,或透過隨處可見的手機上網。勞動市場適應新的情況,驅使數千萬人越過國際邊界,為自己和家人尋找更好的機會,或試圖逃離家鄉無法容忍的環境。中國、印度等國家冒出龐大的新中產階級,但他們所做的工作,取代了原本由已發展國家舊中產階級負責的工作。製造業不斷從歐美移往東亞和其他低勞動成本的區域。同一時間,在逐漸由服務主宰的新經濟體,女性正取代男性,而低技術工人正被聰明的機器取代。
世界秩序原本有股趨向愈漸自由開放的動能,這股動能從二○○○年代中期開始減弱,然後情勢逆轉。這時碰巧接連發生兩次金融危機:第一次是在二○○八年始於美國次級貸款市場,導致後續的經濟大衰退;第二次則是希臘無力還債而使歐元和歐盟面臨危機。在這兩個例子,菁英政策都造成巨大的經濟衰退、高失業率,以及全球數百萬普通勞工收入驟降。既然美國和歐盟是領頭羊,這些危機自然傷害了整個自由民主的聲譽。
民主學者賴瑞.戴蒙將金融危機後的那幾年形容為「民主衰退」的幾年,幾乎全球各區域的民主政體總數,都從高峰下墜。幾個以中國和俄羅斯為首的獨裁國家則更有自信,也更跋扈了:中國開始宣傳「中國模式」,作為一條明顯不民主的發展和致富途徑;俄羅斯也趁機抨擊歐盟和美國自由主義的墮落。一些在一九九○年代看似成功的自由民主國家,都走回較專制的老路,包括匈牙利、土耳其、泰國、波蘭。二○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固然瓦解了獨裁政府,但隨著利比亞、葉門、伊拉克、敘利亞陷入內戰,這個區域對於更民主的希望徹底破滅。引發九一一攻擊的恐怖主義浪潮並未被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擊退。那反倒突變為伊斯蘭國,儼然成為世界各地偏執、殘暴伊斯蘭主義者的指路明燈。跟伊斯蘭國的韌性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有好多年輕的穆斯林放棄在中東其他地方和歐洲相對安全的生活,前往敘利亞替伊斯蘭國出戰。
更令人驚訝,或許也更重要的是二○一六年兩場大出意外的選舉結果:英國投票決定脫離歐盟,以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兩場選舉的選民都擔心經濟議題,尤其是面臨失業與去工業化的勞工階級。但同樣重要的是對移民大規模湧入的反彈:移民被認為會奪走本土勞工的工作,且侵蝕確立已久的文化認同。反移民和反歐盟的黨派也在其他許多已發展國家擴充實力,尤以法國的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荷蘭的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和奧地利自由黨(Freedom Party)為最。跨過大陸,則有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畏懼,以及禁止表現穆斯林身分,如禁穿布卡(burqa,全身式罩袍)、尼卡布(niqab,只露出雙眼的面紗)和布基尼(burkini,只露出臉、手掌和腳掌的女性泳衣)所引發的爭議。
二十世紀的政治向來是沿著經濟議題界定的左右光譜來規劃:左翼希望更平等,右翼想要更大的自由。進步主義的政治活動以工人、工會和社會民主黨派為中心,他們追求更好的社會保障和經濟重分配。相形之下,右翼則主要關注縮減政府規模和發展私人產業。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條光譜似乎在許多方面讓給由身分認同界定的光譜了。左派已經沒那麼著重於全面經濟平等,而更想促進各種被認為遭邊緣化的群體—黑人、移民、女性、西班牙人、LGBT社群、難民等—的利益。右派,則將自己重新定義為愛國者,企求保護傳統的民族身分認同—常明顯與種族、族群或宗教有關的身分認同。
一個至少可溯至馬克思的悠久傳統,認為政治鬥爭是在反映經濟衝突:基本上就是爭奪能分得幾杯羹。這的確是二○一○年代故事的部分,即全球化造成眾多人口被世界各地的整體經濟成長拋在後頭。在二○○○年到二○一六年間,半數美國人覺得自己的實質收入沒有增加;一九七四年,國家總產出(national output)進了全美最富有一%口袋的比率只占GDP的九%,到二○○八年,已提高到二四%。
但物質性自利(material selfinterest)固然重要,人類也受其他事物刺激,而那些動機更能解釋目前發生的殊異事件。這或許可稱作怨恨的政治。在形形色色的案例中,政治領導人圍繞這樣的感覺來動員追隨者:這個群體的尊嚴遭到侮蔑、貶低或漠視。這份怨恨會刺激該群體要求公眾承認其尊嚴。受到屈辱、冀求恢復尊嚴的群體所承載的情緒重量,遠大於單單追求經濟利益的民眾。
因此,俄羅斯總統普丁談論了前蘇聯垮台的悲劇,以及一九九○年代歐洲和美國如何趁俄羅斯虛弱之際,率北約組織逼近俄國邊界。他鄙視西方政客的道德優越感,不希望看到俄羅斯被當成軟弱的區域成員(歐巴馬總統曾這麼說)對待,而要被視為強權。匈牙利總理奧班則在二○一七年指出,他在二○一○年重新掌權,就是象徵這個時候到了:「我們匈牙利人也決定想要收復我們的國家、想要取回我們的自尊、想要重獲我們的未來。」中國的習近平政府最後也談到中國受了「百年屈辱」,以及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如何試圖阻止它重回前一千年享有的強國地位。當蓋達組織(alQaeda)創建者奧薩瑪.賓拉登十四歲時,他的母親發現他異常關注巴勒斯坦:「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家裡看電視的時候,淚水從臉頰滑落。」他對穆斯林備受羞辱的憤怒,後來得到許多年輕信徒呼應;他們自願赴敘利亞,為他們深信一直在世界各地遭到攻擊和壓迫的信仰出戰。他們希望在伊斯蘭國重建早期伊斯蘭文明的榮光。
對尊嚴受辱的怨恨,在民主國家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佛格森(密蘇里州)、巴爾的摩、紐約等城市連續發生廣為宣傳的警察槍殺非裔美國人事件,使「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迅速湧現,希望外界注意看似漫不經心的警察暴力會使人民受到多大的傷害。在全美各地的大學校園和職場,性侵害和性騷擾被視為男性未真正平等看待女性的證據。先前未獲世人承認為顯著歧視對象的跨性別人士,也突然獲得關注。而許多把票投給川普的美國人都懷念過去社會地位較穩固的美好年代,希望透過自身行動「讓美國再次偉大」。雖然時空相隔遙遠,普丁支持者對西方菁英不可一世的感受,和美國鄉村選民的感受其實相當類似:後者覺得兩岸都市菁英及其媒體同路人,同樣忽視他們,無視他們的困境。
怨恨政治的實踐者意氣相投。普丁和川普對彼此懷抱的同情不只是個人的,更是根源於雙方共有的民族主義。奧班解釋道:「現今西方世界發生的變化,以及某位美國總統嶄露頭角,有某些理論形容為世界政治競技場上跨國菁英—被稱為『全球』菁英—和愛國國內菁英之間的鬥爭。」而他自己就是愛國國內菁英的早期典型。
在所有案例中,都有一個團體—俄羅斯或中國之類的強權也好,美國或英國的選民也好—相信自己的身分並未得到適當的承認,無論是外面世界的承認(就國家的例子而言),或同一社會其他成員的承認。這樣的身分認同可能也確實千變萬化:基於民族、宗教、族群、性取向、性別等不一而足。它們全都彰顯一種共同現象,表現出身分認同的政治。
「身分認同」(identity)和「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二詞的起源距今相當近,前者是在一九五○年代由心理學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大力宣傳,後者則到一九八○及九○年代的文化政治學才映入眼簾。今天,「identity」一詞有相當多種意義,有時僅指社會分類或角色,有時單指個人基本資訊(例如「我的身分證被偷了」)。若是這種用法,「identity」一直存在。
在這本書中,我會以一種特定意義來使用「identity」一詞,那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identity」在當代政治如此重要。首先,「identity」是因一個人真正的內在自我與外面社會規範的世界出現差異而生,外在世界並未適當地承認內在自我的價值或尊嚴。綜觀人類史,都有個人覺得自己和所屬社會格格不入。但一直要到現代,真實內在自我的本質彌足珍貴、外在世界會有系統性錯誤且對前者評價不公的觀念才站穩腳跟。不是該讓內在自我遵從社會規範,而是社會本身需要改變。
內在自我是人性尊嚴的基礎,但尊嚴的本質卻非固定,且已隨時間改變。在許多早期文化,尊嚴僅歸少數人所有,通常是願意在戰場上拋頭顱灑熱血的勇士。在其他社會,尊嚴是所有人類的特性,是有主體動力之人(people with agency)的固有價值。還有些例子,得到尊嚴是因為加入了某個有共同回憶和經驗的大群體。
最後,尊嚴的核心意義是尋求認同。要是他人不公開承認我的價值,光是我明白自己的價值是不夠的—更糟的是他人貶低我,或不承認我的存在。自尊是受他人尊重而生。因為人類天生渴望獲得肯定,「identity」的現代意義迅速演變成身分認同的政治,也就是個人需要公眾承認他們的價值。因此,當代世界的政治鬥爭,大都與身分認同政治脫不了關係:從民主革命到新社會運動,從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到當代美國大學校園的政治都是如此。哲學家黑格爾甚至主張,爭取承認的鬥爭是人類歷史的終極動力,而這股力量正是了解現代世界興起的關鍵。
過去五十多年全球化所引發的經濟不平等固然是當代政治的要素,當經濟不平等連上失去尊嚴或不受尊重的感覺,經濟不滿又變本加厲。實際上,許多我們理解為經濟動機的因素,其實並非反映對財富與資源的直接欲望,而是反映金錢被認定是身分地位的指標,可以買到尊敬的事實。現代經濟理論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建立:人類是理性的個體,人人都想將自己的「功利」(utility)—也就是物質福利—最大化,而政治不過是那種極大化行為的延伸。然而,如果我們要貼切地解釋真實人類在現代世界的行為,就必須拓展我們對於人類動機的理解,超越這種主導論述已久的簡單經濟模式。沒有人質疑人類能做出理性的行為,也沒有人質疑人類是出於自利,會追求更大財富與資源的個體。但人類的心理遠比單純經濟模式揭示的複雜。在我們理解當代身分認同政治之前,我們需要後退一步,更深刻也更充分地理解人類的動機和行為。換言之,我們需要更好的理論來詮釋人類的靈魂。
| FindBook |
有 17 項符合
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 / 譯者:洪世民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11-0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
歡迎收聽《讀冊過生活》節目,第068集 【 談《身分政治》一書】
已然成為現今世界的一種症狀,並嚴重威脅到了民主與自由!
追溯民粹主義病灶,提供治療當代政治困境的解方
★《週日泰晤士報》2018年度政治類好書
★《金融時報》2018年度好書
法蘭西斯‧福山早在2014年就察覺美國和全球制度已陷入混亂,衰弱到無法阻止國家被強大的利益團體攫奪。兩年後的英國脫歐公投與美國總統大選,讓福山的預言成真:政治圈外人崛起,他們的經濟民族主義和獨裁主義,正在顛覆國際秩序。
身分認同的需求看似界定了今天的世界政治。反移民的民粹思想、政治化伊斯蘭高漲,以及白人民族主義捲土重來,這些全都對自由民主的基礎構成艱鉅的挑戰。《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指出:當代世界許多被誤認為源起於經濟動機的鬥爭,實則根植於對於承認的需求,無法單純靠經濟手段滿足之,因而現今有太多人受到基於民族、宗教、派別、種族或族群的狹義承認吸引。
福山以扎實的考據與淺顯的論述,從柏拉圖、馬丁•路德、盧梭、康德、民族主義到現代的性別政治,追溯了身分認同概念的發展,他一針見血地提出警告:除非我們能對人性尊嚴建構普遍的理解,否則注定承受接連不斷的衝突。
名人推薦
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葉 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共同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作者簡介: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史丹佛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兼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喬治•梅森大學,擔任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員及國務院政策規劃幕僚副主任,亦曾出任美國總統生物倫理委員會委員。著有《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Our Posthuman Future)、《強國論》(State Building)、《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及《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等書。
譯者簡介:
洪世民
六年級生,外文系畢,現為專職翻譯,曾獲吳大猷科普著作翻譯獎,譯作涵蓋各領域,包括《在一起孤獨》、《東方化》、《倖存的女孩》、《刻不容緩》等書(以上皆由時報出版)。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尊嚴的政治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走到一半,世界政治發生劇烈的變化。
從一九七○年代初期到二○○○年代中期,出現了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歸類為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原本的三十五個增至一百一十多個。在這段期間,自由民主成了世界許多政府的預設形式—至少志在民主,就算沒有落實。
與這種政治制度的變遷並轡而行的是各國的經濟愈益相互依賴,即我們所說的全球化。後者得到諸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及後繼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走到一半,世界政治發生劇烈的變化。
從一九七○年代初期到二○○○年代中期,出現了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歸類為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原本的三十五個增至一百一十多個。在這段期間,自由民主成了世界許多政府的預設形式—至少志在民主,就算沒有落實。
與這種政治制度的變遷並轡而行的是各國的經濟愈益相互依賴,即我們所說的全球化。後者得到諸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及後繼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若非唐納.川普在二○一六年十一月當選總統,我不會寫這本書。跟許多美國人一樣,我對此結果感到驚訝,也為那對美國和全世界的意涵深感不安。那是同年第二場結果令人意外的重大選舉。第一場是英國在六月投票脫離歐盟。
過去一、二十年,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現代政治制度的發展:國家、法治、民主可問責性最初如何成形、如何演化和交互作用,以及最後可能如何衰敗。早在川普勝選之前,我就寫到美國的制度正在衰敗,國家正逐漸被強大的利益團體盤據,鎖進一個死板的架構而無法自我革新。
川普本身既是衰敗的產物,也是衰敗的貢獻者。他競選...
過去一、二十年,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現代政治制度的發展:國家、法治、民主可問責性最初如何成形、如何演化和交互作用,以及最後可能如何衰敗。早在川普勝選之前,我就寫到美國的制度正在衰敗,國家正逐漸被強大的利益團體盤據,鎖進一個死板的架構而無法自我革新。
川普本身既是衰敗的產物,也是衰敗的貢獻者。他競選...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第一章 尊嚴的政治
第二章 心靈的第三部分
第三章 內與外
第四章 從尊嚴到民主
第五章 尊嚴革命
第六章 表現型個人主義
第七章 民族主義與宗教
第八章 地址有誤
第九章 隱形人
第十章 尊嚴的民主化
第十一章 從身分到多種身分
第十二章 我們人民
第十三章 民族性的故事
第十四章 如何是好?
參考書目
第一章 尊嚴的政治
第二章 心靈的第三部分
第三章 內與外
第四章 從尊嚴到民主
第五章 尊嚴革命
第六章 表現型個人主義
第七章 民族主義與宗教
第八章 地址有誤
第九章 隱形人
第十章 尊嚴的民主化
第十一章 從身分到多種身分
第十二章 我們人民
第十三章 民族性的故事
第十四章 如何是好?
參考書目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20/11/08
20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