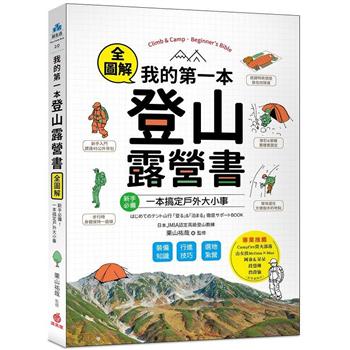讓你睡意全無、不敢喘氣、數度淚崩的懸疑推理小說
拷問人性的光明與黑暗、純真與複雜
同名電視劇拍攝中 2021即將上線
鄭執,「匿名作家計畫」首獎得主
華文創作圈備受矚目、青年暢銷作家
橫跨影視與文學創作,多部作品改編上映
二○一三年,一具妙齡屍體橫陳在爛尾樓「鬼樓」的雪坑裡,腹部被刻上了一枚神祕的圖案,作案手法與十年前鬼樓姦殺案如出一轍,當年負責此案的刑警馮國金,在查案過程中失去了一名年輕同袍,關鍵錄影資料憑空消失,疑犯也在追捕中遭槍擊成為植物人。如今兇手再度現身,難道十年前真的抓錯人?
「小孩子的惡是純粹的惡,成年人的善是複雜的善。」
黃姝,花樣年華的美麗少女,也是刑警馮國金女兒馮雪嬌的同班好友,自小家庭破碎,寄居舅舅家。秦理,八三大案犯人之子,越級就讀的天才。兩人因悲慘的身世,飽受同學的訕笑與欺凌,遭友人背叛與傷害,殘酷的青春往事歷歷,卻始終相互依持,直到黃姝陳屍鬼樓雪坑,秦理的哥哥秦天成為首號疑犯,秦理也與所有人失去聯繫。
「為了照亮她的生命,你將自己付之一炬。」
現實中不存在純粹的光亮。人性的最初都是非黑即白,兩者勢均力敵,大多數成年以後,都是白不勝黑。黃姝與秦理都被現實的黑暗生吞活剝,仍成為照亮彼此生命的點點星光。作者鄭執透過書中五位好友的生命故事,闡釋人性中的「黑白戰爭」,在不純然的善與惡中,每個人都是戴罪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