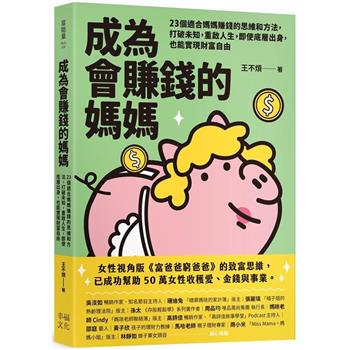圖書名稱:鐵路現代性
長期以來,鐵路、火車作為現代技術文明最耀眼的產物,自然也就被當作是現代性的象徵。鐵路可以說是為了讓人重新發現世界才誕生的,它改變了我們感受時空的方式,重塑了我們對世界的把握;不僅在社會經濟中發揮著實際作用,也在歷史文化領域滲透著強力影響。
《鐵路現代性:晚清至民國的時空體驗與文化想像》依據晚清至民國的時間順序,以鐵路的命名故事、《點石齋畫報》中的視覺與圖像、吳淞鐵路到洋務運動的論爭、孫中山的鐵路擘劃與國族建構、民國時期的鐵路旅行與文學書寫、現代主體與陌生他者的鐵路經驗和文學表述等六個不同面向,在鐵路與火車所引起的時空體驗和文化想像這個主題下,重新思考現代性的諸多問題。
作者李思逸以鐵路為方法、為契機、為理解中國現代性的鑰匙,透過1840年至1937年約一百年間,鐵路進入中國之後發生的衝擊與適應,探討鐵路在晚清民國的具體情境中是如何與現代的想像與經驗勾連在一起。而當鐵路成為人與世界的仲介,「中國」、「現代的中國人」又是如何透過語言認知、視覺感受、事件話語,在「人—鐵路—世界」這樣一種同時並列、不可分割的圖示中於焉成形。
關於鐵路的故事是說不完的,而且背後另有文化和思想的洞天,值得深入研究。因為不論是鐵路還是現代性,我們都沒有自以為地那樣了解它們。
作者簡介
李思逸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哲學博士。畢業於武漢大學人文科學試驗班,取得香港中文大學跨文化研究及語言學碩士學位,曾是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Visiting Fellow, Aug 2016 - Dec 2017);研究興趣集中於現代性理論與現代主義文學藝術、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史、視覺文化、歐陸哲學等。目前兼職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教育大學,教授課程「現代性與都市文化」、「文學與電影」、「五四知識分子:歷史與文本」等,發表研究論文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