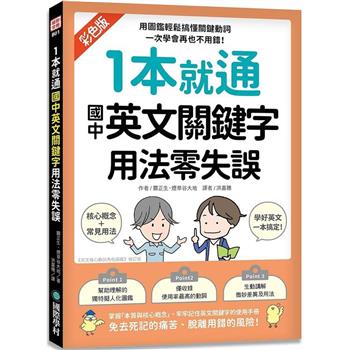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5 項符合
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全新修訂校對版)的圖書 |
 |
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全新修訂校對版)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 / 譯者:林麗雪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12-1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2020年讓全球措手不及。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導致的肺炎疫情意外爆發,不僅考驗各國政府如何保護國民健康、維繫經濟活動,更加速國際政治情勢的變化,疫情能否獲得控制仍在未定之天,世界秩序已然大洗牌。如今重讀政治思想家法蘭西斯.福山於2014年寫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彷彿置身於政治預言之中。
法蘭西斯.福山師承杭亭頓(Samual P. Huntington),希望能藉由這套《政治秩序的起源》,補足其政治思想因時代衍生的落差。但他的做法並非接續杭亭頓的著作從1970年代開始分析,而選擇從人類史前開始,自人類的靈長目祖先黑猩猩談起。
法蘭西斯.福山認為現代國家要實施民主並不難,真正困難的是建立有能力為人民服務,並且保障人民安全的合法現代國家。《政治秩序的起源》分成上下兩卷,其理論基礎在於,現代成功的自由民主,來自三大政治體制:國家、政治、可問責的政府。
第一、國家必須能合法、有效地使用權力。
第二、法治是用來限制國家、統治者的權力。
第三、一個可問責的政府,會藉由公平自由的多黨選舉等民主程序,迫使統治者以全民利益為優先,而非謀一己之私。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福山檢視現代政治發展,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全書分為四部,前半從美國、歐洲不同地區、拉丁美洲、非洲、東亞等各區域實例探討,為何在看似類似的條件下,不同國家會產生不一樣的政治結果;後半則綜合檢討成功發展政治秩序的因素,以及分析為何會導致政治衰敗。福山認為要建立和維持政治秩序,除了民主,還需要強效的政府和法治,並探討民主在不同情況下面臨的危機:
‧殖民主義如何在拉丁美洲、非洲與亞洲國家產生不同的影響?
‧過早進入民主政體,反而會導致缺乏效能的政府?
‧美國的分權制衡與利益團體如何導致民主制度的崩壞?
‧如果民主是普世價值,如何面對民主的衰退?
對照2014年書中提到的質疑與推測,如中國能否在專制制度下維持經濟成長,如今讀來分外值得深思。縱然自由市場、有活力的公民社會、自發性的群眾智慧,都是民主重要的成分,但都無法取代一個強健、階層分明的政府。民主建制的存在,並不是評斷某國治理好壞的有力依據,未能兌現承諾,才是政治制度面臨的最嚴峻挑戰。如何「向丹麥看齊」,建立民主、安全、繁榮又不腐敗的國家,是本書追求的理想國度。
作者簡介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史丹佛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兼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喬治•梅森大學,擔任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員及國務院政策規劃幕僚副主任,亦曾出任美國總統生物倫理委員會委員。著有《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Our Posthuman Future)、《強國論》(State Building)、《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以及《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Identity)等書。
審訂者簡介
陳思賢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長: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
譯者簡介
林麗雪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專職譯者。曾任職國會助理、記者與編輯。喜歡有生命力的人事物;熱愛文字工作。譯有《QBQ!就是要傑出》、《3300萬人的聊天室》、《學校沒教的就業學分》、《我用死薪水,讓錢替我賺錢》、合譯有《怪咖成功法則》、《虛擬貨幣經濟學》、《如何打造營收上億的App》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