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彈丸飛出,白煙繚繞,擺在五十步外的木頭靶子,瞬間被砸了個四分五裂。
迅速從叉棍兒上取下一個巨大的鳥槍,張維善將槍口朝上,利索地從腰間摸出一竹管火藥,直接倒了進去。隨即,填彈,壓實,架槍,瞄準,擊發,所有動作宛若行雲流水,又是「砰」地一聲,將六十步外的第二張靶子也打了個粉碎。
「好槍!」
「少爺使得好槍!」
「少爺厲害……」
喝彩聲宛若雷動,張府的家丁們,爭先恐後地替自家少爺呐喊助威。張維善年輕的臉上,却不見多少得意之色,再度從叉棍兒上取下鳥槍,裝藥,填彈,壓實,架槍,瞄準七十步外的第三張木靶子,「砰」 地一聲,將靶心射了個對穿。
緊跟著,第四張,第五張靶子,也先後被彈丸擊中,家丁們的喝彩聲,愈發響亮。然而當張維善信心十足地開始第六次射擊之時,大夥却只聽到了火槍的轟鳴,擺在一百步處的靶子,紋絲不動。
喝彩聲,頓時就小了下去,張維善的臉上,却依舊波瀾不興。又瞄著靶子陸續開了四次火,直到確定不是因爲自己瞄得不準,而使得彈丸脫靶之後,才將從倭寇手裡繳獲的巨型鳥槍取下來,轉身遞給了一直默不作聲的李彤,「第四張靶子,就向左飄了。第五張靶子,只能算勉强擦了個邊兒。這斑鳩槍,其實也就那麼回事兒。看上去打得挺老遠,八十步以上,能不能打中基本就得靠矇!」
「我托人打聽過了,這東西咱們叫斑鳩槍,佛郎機那邊叫重型火槍。好處不是比鳥槍打得遠,而是用料足,輕易不會炸膛。萬一來不及裝藥,還可以倒著掄起來當鋼鞭使。」李彤笑了笑,伸手將斑鳩槍推了回去。
「那倒是,這傢伙足足有二十多斤!」張維善聽得眼神一亮,立刻單手倒抓著槍管上下揮動。仗著自己臂力過人,竟然將五尺半的槍身,揮得「呼呼」有聲。
李彤禮貌性向他挑了下大拇指,然後又開始對著遠處的湖水發呆,兩道劍眉之間,愁緒濃得宛若墨汁。
這可不是年輕人應有的模樣,至少不是一個年輕勛貴子弟應有的模樣。南京城內,像他這個年紀的公子哥們,大多數還處於「爲賦新詞强說愁」的階段,心緒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沉重。而他,却在炎炎盛夏時節,滿眼都是秋風。
「怎啦,還爲前幾天的事情發愁呢?」張維善明顯感覺出了好朋友情緒不對,將斑鳩槍扔給家丁張樹,操著一口剛剛學來的遼東腔大聲詢問。「王總兵不是說,所有事情他的接過去了麼。我可是打聽清楚了,這廝的祖父居然是陽明先生 。怪不得根本不把嚴瘋子的威脅當一回事兒。甭說嚴瘋子,就是南北兩京內的官員,有本事爲難他的,恐怕都找不出一巴掌。」
「叔元兄一諾千金,他答應的事情,我自然放心。」 李彤咧了下嘴,輕輕搖頭。「我只是覺得心裡頭堵得慌。要不是老天爺忽然開了眼,降下了一場大暴雨。八卦洲糧庫,肯定會被徹底燒城白地。」
「最後不是沒燒麼,倭寇也被咱們幹掉了一大半兒。剩下的雖然上船逃了,但當時江上白浪滔天,他們能不能活著逃掉,還要兩說。」 張維善也咧了下嘴,笑呵呵地大聲安慰。
不像李彤那麼敏感,是個天生的樂觀者,無論遇到多大的麻煩,都該吃時候吃,該睡時候睡,該玩時候玩,從來不讓麻煩影響到自己的性情。
「是啊,最後沒燒。」李彤又嘆了口氣,臉上的表情愈發陰沉,「可那是因爲老天爺開眼。人做事情,總不能全靠老天爺。偌大的南京城,文武官員加起來三百餘,從江南突然遭到倭寇刺殺,到最後咱們在姓嚴的府上救下他的命,足足大半個月時間,竟然沒有一個人想到,倭寇的真正目的是八卦洲糧倉。」
這,是他的心裡話,也是最無法理解的事情。
大明乃天朝上國,人才濟濟。南京鎮守衙門、錦衣衛、應天府、南京六部,裡邊的文武官員,個個都是百裡挑一的人精。可這麼多人精,却全成了泥塑木雕,硬生生讓數百倭寇在自己眼皮底下殺上了八卦洲。
按道理,早在發現江南遇刺的凶手來自倭國,上元縣的官員就應該有所警惕。按道理,在他和張維善去追查謀害江南的幕後黑手,却不小心堵了半船的倭寇,江寧縣和應天府的官員,就該爲之震驚。按理說,倭寇雨夜殺人,並且公開對抗巡街的官兵,錦衣衛、南京鎮守衙門,都應該立刻有所行動。南京六部,督查院,通政司,就該立刻聯手徹查此事,並且要求周圍各個衛所加强戒備,以防萬一。
而事實却是,以上各衙門的衆多官員,誰都沒當回事兒。南京錦衣衛忙著跟北京的某些大員一道,阻止王錫爵返回朝廷再度入閣;南京城的各部文官,在努力上書朝廷,阻止大明出兵朝鮮,以免將門借此重新崛起,打破百餘年來好不容易形成的「文貴武賤」大局;南京的督查院的嚴大御史,正忙著誣陷兩個籍籍無名的貢生,以給他那個收過王家好處的門生「報仇雪恨」;南京城的武將們,則巴不得事情越鬧越大,以此證明文官們的昏聵無能。
所有人精都很忙,並且忙得理由充足。誰也沒拿倭寇當一回事,更沒功夫,去考慮倭寇頻頻在南京城內製造血案,到底是何企圖?
只有他和張維善兩個貢生,兩個沒有任何職位,沒拿過朝廷一文錢俸祿的貢生,稀裡糊塗地被捲入了一個巨大的漩渦,稀裡糊塗地跟一夥倭寇打生打死,最後又稀裡糊塗地提前一步登上了八卦洲,稀裡糊塗地參與了守衛糧倉的戰事,令倭寇最後功敗垂成。
八卦洲的戰事已經結束三天了,李彤依舊覺得自己像是在做夢。一個漫長而又荒誕的噩夢。
如果是夢,那麼,大半月來所經歷的任何荒誕,都能夠得到合理的解釋。
但是,無論他如何努力,如何用冷水朝自己頭上澆,如何偷偷用針扎自己的大腿,他都無法讓自己從這個荒誕的夢境裡走出來。
原因很簡單,因爲大半個多月來所有荒誕,所有匪夷所思,都是現實。
「你呀,就是想得太多,累!」張維善的話忽然從耳畔傳來,每個字都帶著如假包換的關切。
換做平時,面對朋友的善意勸告,李彤肯定從諫如流。然而今天,李彤却忽然覺得對方的話好生刺耳,「不是我想得多,而是不該這樣。大明,大明不該這樣!」
「那你說該怎樣?」張維善抬手撓了撓汗自己津津的腦袋,咧著嘴追問。「咱們平時見到的,不都這鳥樣子嗎?」
「這……」李彤無法回答,更無法反駁。
大明朝平時就是這幅模樣,清流們整天找藉口撕咬,武將們忙著種地撈錢,地方官員吃了原告吃被告,小吏們變著法子敲詐勒索。他和張維善雖然都嬌生慣養,却都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白痴,以往沒少聽說各種官場奇聞,也沒少見識各種徇私舞弊的手段。
甚至連同他們的父輩,也完全靠著大明朝目前的種種痼疾,才活得有滋有味。才能讓他們兩個吃喝不愁,甚至偶爾出去一擲千金。
可以往大明朝是什麼鳥樣子,都不關他們的事兒。他們就像站在河畔的看客,看著別人在水裡且沉且浮。而現在,他們却自己不小心掉進了何裡,並且差點就嗆了水,差點活活淹死。大明朝的這副鳥樣子,就再也無法讓李彤高興得起來。
他心目中的大明,即便做不到君賢臣直,衆正贏朝,至少不能差到幾乎沒人肯幹正事兒。他心目中的大明,即便做不到威服四夷,外王內聖,只要也應該不會對夷狄在自己家裡殺人放火視而不見。他心目中的大明,即便做不到文武相和,齊心對外,至少不應該在外敵都宣告目標是打進紫禁城了,還忙著互相扯後腿。他心目中的大明,即便做不到……
「少爺,張家少爺,國子監劉博士派下人送來請柬,請你們明日中午過府飲宴。」家丁李財忽然跑了過來,雙手呈上一份精美的請貼。
「不去,我最近胃口不好,不想在外邊吃喝。」李彤正憋著一肚子鬱悶之氣無處發洩,果斷搖頭拒絕。
在剛剛過去的那一系列荒誕事件當中,最讓他失望的,就是國子監博士劉方。後者擺出一副老謀深算模樣,煽動他們去將事情鬧大,並且信誓旦旦地說,會有大明將門出面爲他們兩個撑腰。然而,在他們兩個真正需要撑腰之時,後者却果斷選擇了避而不見。
若不是他們兩個善有善報,不經意間救了小春姐,進而得到了漕運總兵王重樓的垂青。若不是王重樓運氣好,誤打誤撞搶先一步帶著他們登上了八卦洲,給了倭寇迎頭一擊。若不是李如松、李如梓等人仗義援手,幫忙組織起了八卦洲的衛所兵將,僅憑著他們兩人的細胳膊細腿兒,根本沒辦法擺脫那個深不可測的漩渦。
他們兩個,極有可能,越陷越深,最後連骨頭渣子都不剩。
按照王重樓和李如梅兩個旁觀者的推測,整件事雖然起因是倭寇刺殺高麗國的郡王世子,後來,却涉及到了好幾家神仙的鬥法。
南京錦衣衛、南京清流、南北兩京六部、大明內閣、大明將門,都抱著各自的目的,在裡邊渾水摸魚。而他們兩個雖然也是勛貴子弟,但跟幕後出招的神仙們比起來,却連臭魚爛蝦都算不上。裡邊隨便一路人馬發了狠,都能用輕鬆將他們碾成齏粉。
「我覺得還是去得好,劉方再不厚道,也是咱們的老師。」 張維善很少當著下人的面兒跟李彤唱反調,今天却忽然破了一次例。從旁邊快速搶過請柬,大聲提醒,「況且,他還是你的未婚妻的叔叔,駁了他的面子,盈盈姐也跟著沒臉。」
「那就告訴劉府的下人,說我最近淋了一場雨,風寒入體,燙得厲害。怕將疫氣傳給他們。」李彤想了想,隨即大聲補充。
比起先前那句胃口不好,這次的說辭,已經委婉了許多。讓張維善想要再勸,也找不到足夠理由。正猶豫間,却忽然聽見不遠處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哎呀,誰這麼大火氣,連我家都不想去了。李子丹,莫非你最近有了新歡,想把我姐姐給拋棄了不成?那我可是得跟你好好算算,咱們兩家這一大筆糊塗賬。」
「繼業!」李彤頓時顧不上再鬱悶,邁開大步朝樹叢後竄過去,隨即,就叉出來一個圓滾滾的「肉球」,「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不告訴我們一聲!剛才萬一守義朝樹叢裡開火……」
「哎呀,哎呀,別掐,別掐,脖子都給你掐斷了,斷了!」長得像肉球般的胖子劉繼業,淒聲慘叫,彷彿真的隨時都會被活活掐死一般。
「滾,你脖子這麼粗,得多重的手,才能掐得斷?」 李彤只好鬆開手,朝著對方作勢欲踢。「這半年來,你究竟躲哪裡去了?怎麼每次派人送信來,都含糊不清。」
「是啊,你小子到底躲哪裡去了?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知道我和子丹在這兒?!」 張維善也興奮得滿臉放光,上前迎戰胖子,迫不及待地追問。
「老夫不是躲,而是出去修了幾天道法。師父傳下了諸葛亮的馬前課,老夫掐指一算,就知道你們兩個,肯定會來莫愁湖這邊。」 劉繼業假裝向前撲了兩步,然後回過頭,晃著胖蠶般的手指大聲回應,「所以老子就過來聽聽,在老子外出修行這陣子,你們兩個又幹了多少齷齪事情!特別是你,李子丹,是不是背著我姐,在外邊偷腥?」
「皮癢了是不,守義,咱們給他鬆鬆筋骨。」李彤聽他越說越不像話,果斷決定以武力解決問題。
張維善也正高興得不知道如何是好,聽到李彤的提議,立刻欣然以應。兄弟倆一左一右,各自控制住胖子劉繼業的一隻大粗胳膊,隨即舉起另外一隻手,就準備施加「嚴懲」。還沒等第一個殺招使出,就聽劉繼業大聲喊道,「別,別胡鬧。有人,有客人。你們哥倆,多少給我留點臉面。有貴客,真的是貴客!」
「貴客?」李彤和張維善聽得將信將疑,趕緊抬起頭,朝著先前死胖子劉繼業藏身處張望。却沒看見任何人影,只有密密麻麻的蒲草,在風中搖晃。
「收拾他!」二人互相看了一眼,大叫著就要動手。就在此時,更遠處,忽然傳來一聲清叱,「兩位兄長,且慢!待我將他先送回家,你們再敘舊也不遲。」
「啊——」李彤和張維善再度齊齊舉頭,恰看見,一個長髮飄飄,藍衣如水的高挑女子,從樹後走了出來。雙目之中,宛若有寒星閃爍。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大明長歌(卷二):前出塞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大明長歌(卷二):前出塞
蟬、螳螂、黃雀 誰又是懷丸操彈之人
在生與死的關頭,人性的醜惡與自私,被展現得毫無遮掩。
不但要防範敵人,還要防範自己人。
能搶到好馬,就多一分生機。被打下馬背,或者搶不到好馬,則葬身火場。
少年時,喜歡做夢,其實沒什麼不好。
至少睡眼裡看到的世界,更溫柔一些。
遠不像成年後看到的那樣冰冷。
李彤、張維善為避禍事決定遠離南京,遠赴遼東投筆從戎,其後與好友劉繼業尋找深入朝鮮執行任務的總兵祖承訓與在其下任職的舅舅史儒。路上遭遇已經潰敗的朝鮮軍隊,從中得知史儒所在的前鋒營遭逢敵軍偷襲,潰軍大部已從平壤再度撤回到馬寨水邊,現時身邊兵馬已不到三成,情況危殆,下落不明。
日本軍隊節節進逼,然而朝鮮諸侯?無不想藉機稱王自立,或試探,或伺機,各自盤算。女直各部亦欲從中獲利,是敵是友實難分辨。而傳聞中的朝鮮傳國金印在幾經波折下,落入在祖承訓之手,準備將金印護送回大明。各路人馬聞風而來搶奪金印,初入朝鮮即遭逢困境的眾人,為求脫身自保只好引火焚山,不料野火燎原,頓時各方人馬陷入混亂……
作者簡介:
酒徒
內蒙古赤峰人,男,1974年生,東南大學動力工程系畢業,現旅居墨爾本。其作品擅長運用真實史事,從小處下筆,著眼處往往是前人未曾觸及的視野,以小人物的故事做為開端,結合傳統俠義、愛情傳奇等諸多元素,建構出當時歷史環境的整體風貌,寫實刻畫場景,細膩透寫人物,在歷史小說中推陳出新,有歷史小說裡的金庸如此的讚譽。目前為中國歷史小說界的翹楚,也是中國作家協會首度納入的網路作家。曾擔任網路文學導師,走進大學校園演講,培育新一代的文學作家不遺餘力,現為中國獲獎最多的網路作家。
著有《亂世宏圖》、《大漢光武》(以上為時報出版)等數十部作品。
章節試閱
「砰!」彈丸飛出,白煙繚繞,擺在五十步外的木頭靶子,瞬間被砸了個四分五裂。
迅速從叉棍兒上取下一個巨大的鳥槍,張維善將槍口朝上,利索地從腰間摸出一竹管火藥,直接倒了進去。隨即,填彈,壓實,架槍,瞄準,擊發,所有動作宛若行雲流水,又是「砰」地一聲,將六十步外的第二張靶子也打了個粉碎。
「好槍!」
「少爺使得好槍!」
「少爺厲害……」
喝彩聲宛若雷動,張府的家丁們,爭先恐後地替自家少爺呐喊助威。張維善年輕的臉上,却不見多少得意之色,再度從叉棍兒上取下鳥槍,裝藥,填彈,壓實,架槍,瞄準七十步外的第三張木...
迅速從叉棍兒上取下一個巨大的鳥槍,張維善將槍口朝上,利索地從腰間摸出一竹管火藥,直接倒了進去。隨即,填彈,壓實,架槍,瞄準,擊發,所有動作宛若行雲流水,又是「砰」地一聲,將六十步外的第二張靶子也打了個粉碎。
「好槍!」
「少爺使得好槍!」
「少爺厲害……」
喝彩聲宛若雷動,張府的家丁們,爭先恐後地替自家少爺呐喊助威。張維善年輕的臉上,却不見多少得意之色,再度從叉棍兒上取下鳥槍,裝藥,填彈,壓實,架槍,瞄準七十步外的第三張木...
顯示全部內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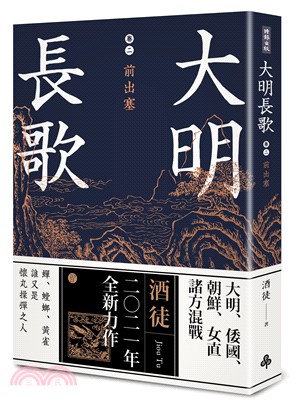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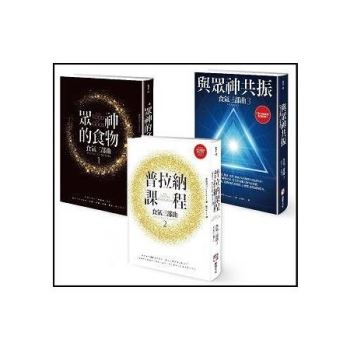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