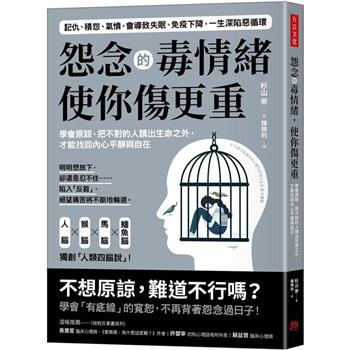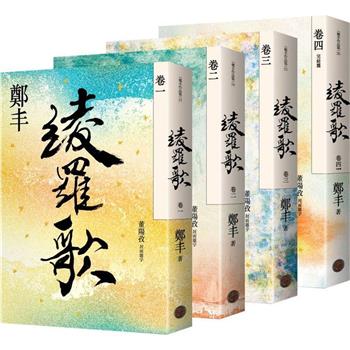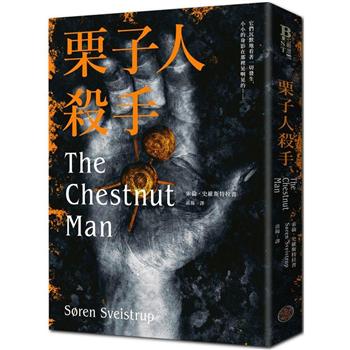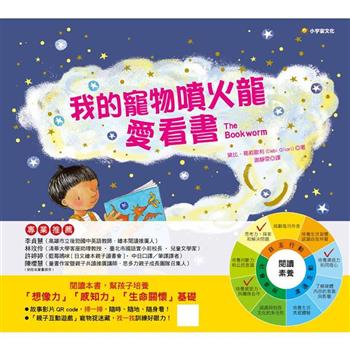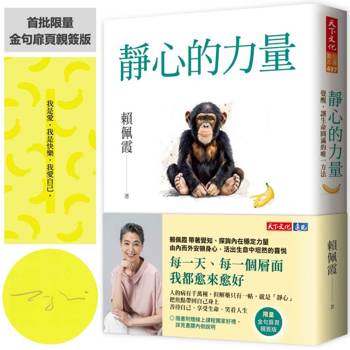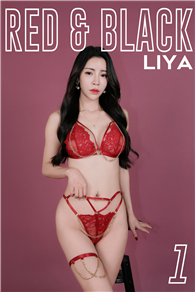〔推薦序〕從生活雜質中打磨出的寶石夏夏
三房,一廳一衛。二十五坪,有一點奢侈的寬敞,但不至於大到沒辦法負擔。至於屋齡,見仁見智,該從孩子出生那年算起,你們同時晉級到「雙親」這個傳說中的魔王關(這一關要打很久,而且生命值常常不夠用),圓滿了一個幸福家庭的想像?還是要從新婚的第一天算起?或是從更早之前,你初來乍到這個世界上,你的母親成為母親的那一天?
當然,關鍵是低總價,雖然仍要揹上幾年的房貸,利息是不斷增生的白髮與皺紋。不過問題是你願意為心目中理想的「家」付出多少代價?
讀《在家》時,我忍不住聯想到預售屋展售時常見到的屋內配置平面圖,且看用方格標示出來的每個縮小空間,容納著無限的想像。何亭慧將《在家》全書巧妙地以空間來做區分,分別是門、臥室、小孩房、浴室、廚房.書房、客廳與後院。此處所言的「家」,絕不是暫時屈就的單身套房或與人共用衛浴的雅房,而是一個完整的家呈現在紙上。而這正是何亭慧自《形狀與音樂的抽屜》、《卡布納之灰》之後,時隔十三年所集結的成果,每一篇都像是熬煮已久的濃湯,醞釀多時的一罈佳釀。
首篇〈愛情〉彷彿是一則簡短的前情提要,使人聯想到何亭慧從前敏銳、質地澄澈清脆的詩,如「我的絕望/來自於/被吻/但,不被愛」(〈蠟〉)。接著,轉眼間便踏入可嗅聞到生活氣息的玄關,過往玻璃般的詩句被鍊成了溫潤的瓷器,在這裡愛情是「像晒棉被的好天氣」(〈家常〉),是會讓人吃光光的家常菜色。
而閱讀《在家》時,猶如一場紙上導覽,詩人的文字帶領讀者穿越門廳,進入到一個家庭最私密的所在,用無聲的文字重演每一個特別的時刻。而其中的重頭戲,就屬「廚房.書房」。
在「廚房.書房」這一輯中收錄了兩首以〈自己的廚房〉為題的詩。第一首致英國作家吳爾芙,首先以詩題呼應吳爾芙所提出關於女人的房間,詩人以幽默的語句指出在作為書房的廚房裡,家電與筆電並列,「甚至咖啡機/丈夫睡著後/我在餐桌上寫詩/(詩的發展永遠鮮嫩)」,寫作與做菜何其相仿,詩人料理三餐也料理生活的殘渣與「白日零碎的思想」。在吳爾芙道出其名句後,女人們經歷了約一世紀的奮鬥,何亭慧以全詩末段「吳爾芙我的朋友/妳坐在書桌前太久了/來碗麵暖胃吧」的輕鬆口吻,標誌出新的女性典範:坐鎮於家電與筆電之前,一手家務一手寫作,連男僕(或丈夫?)都不用,可說是家庭與事業都難不倒的新女性。此詩可作為全書的定錨,作為支撐一個理想家庭的鋼骨,卻不顯露霸道,而充滿女性特有的優雅與包容。第二首致英國小說家珍.奧斯汀,背景音效是爐子上噗噗滾著的熱湯,在沒有門的廚房裡,任何人隨時都可來去,連房間都算不上。然而在這樣克難的情況下,「角落的筆電/偶爾在餐桌上打開」輕描淡寫一句「偶爾」,有經驗之人才知道那絕非自動從天上掉下來的偶爾,而是將寫詩這件事時時掛在心上,因此即使不常派上用場,筆電仍備在一旁靜待突如而至的偶爾到來。然而詩人卻不以為苦,既無心當「女主角」,學會了對生活與自己妥協,且在詩的第三段這樣寫著,「兒子的造句作業:/「有空──媽媽有空的時候就會寫ㄕ。」實為神來一筆,生動描寫出做為母親與詩人雙重身分的生活樣貌,作為全書的基本色調。特別是「ㄕ」字留予人想像與猜測,何亭慧繼續寫道,「親愛的珍,為了老師打的紅色問號/妳一定會樂不可支」讀來令人莞爾一笑。兩首以〈自己的廚房〉的詩作像是兩道旋律鮮明的輕快旋律,彼此呼應,勾勒出專屬於這個時代女性的明快爽朗,溫厚中依然能保有剛強的自我。
而接續其後,像是取自前兩首主旋律的變奏,終於來到〈自己的書房〉與〈食譜〉。在這兩首詩中,何亭慧分別闡述生活觀與詩觀,「沒有非得留在書架上的/心,不需展示/就讓食譜、樂譜打亂所有主義和流派/過一種活力充沛的現實」,「把廉價寫出富裕/平淡寫出驚喜/寫/放學後的廚房」在此延展出向內的力道,探查剖析自我的組成,而能隱約見到淡淡的疤痕/接縫,所接連的分別是Before和After兩種生命樣態。
Before是從前那個寫詩的女人,After是成為母親的詩人。兩者的差別看似只在於一道細細的接合處,然而這道縫隙卻深入骨與肉之中,漫散於詩集中。如〈夜遊〉作為一道鮮明的分野,寫新生兒誕生,亦是母親的誕生。稚嫩的嬰孩四個小時便須進食一次的生理時鐘牽連著母體,因此母親在脹奶之中痛醒,在夜裡將滿脹的乳房擠出乳汁,不禁聯想到從前不寐的夜晚,「我在夢的外頭/獨自遊走/像從前寫詩時那樣」。〈預測〉一詩中,則寫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初識萬物的奧祕,雖然此刻「音樂/被困在笨拙柔弱的手指裡」,然而未來將在其中窺見美好的詩意,「如我曾在詩裡/聽見的那首永恆的歌」。
而在Before與After之間的印記既是永不斷裂的接縫,也是永不癒合的裂口,自此處傳出的是對生命的驚嘆。一如在〈洗澡〉詩中所寫,「怎麼可能/我怎麼可能是母親/紗布巾下活生生的臉/我不認得」連續兩次「怎麼可能」的吶喊點出了對生命的敬畏與對未知的不安。
而這份來自於信仰的謙卑,廣見於何亭慧的詩作中。我特別喜歡她在〈鏡子〉中寫出不同層次的「看見」。從鏡中看見日漸衰敗的容貌,又從其中看懂了詩句般的缺陷,而最重要的是平凡的生活是一面鏡,為要「映出造物主的形象/不大成功但/汗水/閃亮」或許是有此體悟,何亭慧的詩經常在細微處拉處另一隱藏的高度,在繁盛至極時懂得止步退讓,容許更多的可能性,容許空白發聲。
最後一定要造訪的,是主人精心打造的「後院」。在此輯中,何亭慧的文字引領賓客穿過一道道走廊,迎上開闊的視野。有綴滿紅豔果實的桑葚、蒐集星星的楊桃樹,也有倒在自己的香氣裡的檸檬桉,何亭慧如同園藝高手,用文字栽種出旺盛的枝與葉,不著痕跡地修剪,且比任何人都格外珍惜著院裡的一枯一榮,細細地刻劃書寫。
這份珍惜也見於〈十年〉中,何亭慧藉院中象徵愛情的玫瑰花,揭開童話的面紗,寫出真實的家庭與婚姻中好似「院子裡的灌木/莖粗 尖刺多」甚至「幾經寒霜以為不會再開」。一趟家園的紙上導覽至此,讀來格外有巧妙的深意。
《在家》收錄三十六首詩作,這是從生活雜質中打磨出的寶石,從日常消耗中修煉出來的黃金,在何亭慧的筆下卻意外地貼近生活,因而每首詩讀來素樸、簡潔,其中收納了豐盛意象與情感,飽滿地裝載在其中,且井然有序地展示著。讀著讀著,我不禁幻想,詩人放在廚房角落多半呈現關機狀態的筆電,到底都在什麼樣的時候被開啟,鍵入字句?
「從來沒把游泳學會/我不知道怎樣在兩個平行卻相異的世界/順暢換氣」(〈游泳池〉)或許對何亭慧來說,詩就如同轉換於兩個世界中的換氣過程。《在家》,有女人、女兒、妻子、母親和詩人,穿梭於不同的角色間,能夠深刻感受到何亭慧在其中調整出獨到的平衡感,不疾不徐,詩句在平穩的吐納間流出,正是我們曾經嚮往的家的氣息。闔上書本,彷彿還能聽見風輕輕掀動著窗簾,細碎而熟悉的聲音從紙頁間傳出,正在等待著人們回家。
洗澡
上帝用塵土造人
其餘是水嗎
初生兩周
他光裸如一尾無鱗的魚
水掀動眼、脣、鼻息
不,他毫不聖潔。呼喚
鬆軟細黃,沉積耳蝸
淤泥黏附眼角
連指甲——透明的鋤子
都像剛犁過
生命的畦田
殘留灰褐色的時間
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是母親
紗布巾下活生生的臉
我不認得
我不能計算他在羊水中的體重
精確對準出生的鬧鐘
不能使奶水充沛
按比例使他長大
不能免於災病免於苦痛
甚至不能在洗澡的時候
停止他的啼哭
我一無所有
從水中把你拉上來
只能把所有
給你
在山裡走
他看不了太高
跑不了太遠
「滾糞蟲!」他驚呼
兩隻巧克力圓甲蟲
用糖絲拉的後腳踢著球
迅速交錯而過
其中一隻奮力推進枯葉底下的球門但
卡住了
我們蹲下見證
草的歷史。
小稻蝗嚇一跳
翻倒巨山蟻搬運的午餐
彩虹尾巴閃現
「是石龍子!」他大喊
倉皇躲進石縫
在山裡走
走了很久仍是一小段路
風景縮得很輕
遺忘的名字突然變得重要
沒有名字的更重要。
孩子收藏樹葉、莢果在掌心,在口袋
睡著的時候手還要細細撫摸
這生之輪廓
產房手記*
一種半倒立的姿勢
雙腳
套進不鏽鋼環
若是兩手撐地
就可以像體操選手
翻身彈起接受掌聲
但畫面凝結在
完美落地的
前一秒
持續了數小時。
疼痛,疼痛,痛
自身體底層痙攣
裂開地表
「先別用力」教練們聳聳肩。
我尖叫——
岩漿蓄勢待發
指揮官下令:「現在!」
一枚魚雷射出
(為什麼不像按一個鈕那麼簡單?)
炸開響亮的哭喊
歡慶的樂聲
他們撫弄擦拭
把額頭印著血跡的嬰孩
別在我的左胸
他吸吮一顆鬆弛的汗珠
赤裸的孩子啊
我苦難與喜樂的勳章
正如當年亞當
睜開疑惑而惺忪的雙眼
不明白宇宙
因最大的神蹟而震驚
*襲自美國詩人林妲.派斯坦(Linda Pastan, 1932-)“Notes from the Delivery Room”一詩。
夜遊
痛醒時
胸口溼了一片
乳腥味
夜沁涼
我的兩乳腫脹滾燙
汩汩的奶水從夢的邊緣擠出
等你醒了熱著喝
剩下的冰凍
在你漸漸孤獨的日子裡一一拆封
加溫
我來回穿梭水槽
冰箱紫外線消毒鍋
意識的走廊
窗外的黑暗淡了
也有鳥輕輕叫著
丈夫仍熟睡
我在夢的外頭
獨自遊走
像從前寫詩時那樣
晨歌*
朝露的氣息,這是地球
半夢半醒的呼吸,這是
母親。
整個晚上守護你的鼻息
像泌乳的月亮
你眼睛的深井,尚未裝進淚珠
——仍在上帝珍藏的皮袋裡
世界
一片渾沌
用摟抱與親吻,分開晝與夜
不曾踏過泥濘,半透明腳掌
輕輕踩著空中的土地
指甲柔軟——掌窩裡緊擁的白羽毛
不需抓取食物,情誼,甚或
時間。
晨起,歷經小死亡的行星展開新生
你甦醒:微暗,微亮。
嘴,單單尋找母親
時起時歇的哭聲中,語言揮舞它的手勢
血液在你皮膚下流動
生之花在你臉上綻放
*襲自美國詩人希薇亞.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Morning Song”一詩。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在家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在家
詩人何亭慧,以柔軟詩心,書寫生活中種種暖心時刻與生命歷程。
夏夏專文推薦
向陽孫梓評陳育虹暖心推薦
《在家》收錄三十六首詩作,這是從生活雜質中打磨出的寶石,從日常消耗中修煉出來的黃金,在何亭慧的筆下卻意外地貼近生活,因而每首詩讀來素樸、簡潔,其中收納了豐盛意象與情感,飽滿地裝載在其中,且井然有序地展示著。(夏夏)
巴斯卡認為人類所有問題都肇因無法獨自安靜「在家」,何亭慧以一整本詩集做為答辯──這冊同樣可歸類於「媽媽+1」的寫作主題,除了再度為臺灣已婚女詩人身兼母職、妻子與寫作者身分的光譜增色,曾經隨身攜帶的《形狀與音樂的抽屜》也沒荒廢,詩行裡隨處可見與眾多女性創作者的襲化與對話,彷彿一枚等身穿衣鏡,隨書寫者移動於家居。靈動簡潔的詩句,精巧準確的想像,恰到好處的感情,何亭慧以她的詩捕捉了「生之輪廓」,那些記憶描出的裝飾畫,顯誕於日常的神蹟。(孫梓評)
詩人何亭慧自踏入家庭之「門」,與之相伴的除了愛情,還有哺育生命的護犢之愛,以及生活中各式風景,詩人以創作,在反覆敲打鍵盤後,將這些歷程釘掛於牆上,名之為「在家」,堅定而柔韌。
「臥室」裡與丈夫握著幸福票根,同享異夢,她半夢半醒,守護孩子的鼻息,如泌乳的月亮;「小孩房」中「彈珠,故事,小螞蟻/媽媽的溫柔在手套裡/爸爸的陪伴在鞋底」,土裡的甲蟲、滾輪奔跑的鼠……最後留下不乖打屁股的貓,小國王正急著獨處閱讀滿室的書;「浴室」是女詩人就鏡自鑒的小天地,生活讓她汗水閃亮,終能欣賞缺陷,願傾注所有,從此身上的盛妝將會是緊緊環抱的小手。
「廚房.書房」是詩人/家庭主婦身分切換的場域,湯正噗噗滾著,偶爾打開的筆電也等待著珍.奧斯汀、艾蜜莉.勃朗特、小川洋子上線入詩,歡迎入座自由來去;「客廳」,連接著過去與現在,是記憶的承載體,也是生活樂趣所在,追劇、拌嘴、愛上孔龍凶猛想像的兒子、練拾種籽的逸趣想像,熱鬧歡快;「後院」以天為幕的大自然世界,有醉倒在自己香氣裡的檸檬桉,如綴寶紅寶石教堂的桑椹,還有十年玫瑰,彼此見證最醜陋腐敗的時刻,脈脈待放。
歡樂四溢的客廳、獨語自白的浴室、自由切換身分的廚房與書房、充滿稚趣的小孩房、野氣戲劇性的後院,見證了何亭慧十三年來全心投入的家庭生活。精簡素樸的字句,意外地貼近生活樣貌,豐盛的意象裡,滿溢著對生之愛與包容。有形的物質生活雖稱不上富裕,但串連起每個小小的平凡時刻,幸福得有如神蹟。「美有許多,/未必要擁有/但可以期待那些,落下又綻開的花朵」謹以此詩句,為這本溫柔暖心的詩集定調。
*〈洗澡〉、〈在山裡走〉獲第十四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二獎
*〈產房手記〉、〈夜遊〉、〈晨歌〉獲第三十八屆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
作者簡介:
何亭慧
1980年生,中壢人。畢業於元智大學中語系、東華大學創作所。詩作曾獲時報文學獎首獎、林榮三文學獎二獎、葉紅詩獎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優秀青年詩人獎等。曾獲獎助出版詩集《形狀與音樂的抽屜》、《卡布納之灰》。當過編輯,現為家庭主婦,定居臺中。
章節試閱
〔推薦序〕從生活雜質中打磨出的寶石夏夏
三房,一廳一衛。二十五坪,有一點奢侈的寬敞,但不至於大到沒辦法負擔。至於屋齡,見仁見智,該從孩子出生那年算起,你們同時晉級到「雙親」這個傳說中的魔王關(這一關要打很久,而且生命值常常不夠用),圓滿了一個幸福家庭的想像?還是要從新婚的第一天算起?或是從更早之前,你初來乍到這個世界上,你的母親成為母親的那一天?
當然,關鍵是低總價,雖然仍要揹上幾年的房貸,利息是不斷增生的白髮與皺紋。不過問題是你願意為心目中理想的「家」付出多少代價?
讀《在家》時,我忍不住聯...
三房,一廳一衛。二十五坪,有一點奢侈的寬敞,但不至於大到沒辦法負擔。至於屋齡,見仁見智,該從孩子出生那年算起,你們同時晉級到「雙親」這個傳說中的魔王關(這一關要打很久,而且生命值常常不夠用),圓滿了一個幸福家庭的想像?還是要從新婚的第一天算起?或是從更早之前,你初來乍到這個世界上,你的母親成為母親的那一天?
當然,關鍵是低總價,雖然仍要揹上幾年的房貸,利息是不斷增生的白髮與皺紋。不過問題是你願意為心目中理想的「家」付出多少代價?
讀《在家》時,我忍不住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從生活雜質中打磨出的寶石/夏夏
【門】
愛情
家常
【臥室】
拼圖,或者婚禮
產房手記
夜遊
晨歌
臥室
【小孩房】
黑糖多拿滋
閱讀
玩具間
寵物
預測
【浴室】
洗衣
鏡子
洗澡
項鍊
【廚房.書房】
自己的廚房
自己的廚房
自己的書房
食譜
流動的饗宴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客廳】
雨中回憶
追劇
科博館
說說
不忍想念的海
關於種子的收藏
【後院】
桑葚
楊桃樹
檸檬桉
在山裡走
指環
夜間探照
十年
游泳池
後記
【門】
愛情
家常
【臥室】
拼圖,或者婚禮
產房手記
夜遊
晨歌
臥室
【小孩房】
黑糖多拿滋
閱讀
玩具間
寵物
預測
【浴室】
洗衣
鏡子
洗澡
項鍊
【廚房.書房】
自己的廚房
自己的廚房
自己的書房
食譜
流動的饗宴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客廳】
雨中回憶
追劇
科博館
說說
不忍想念的海
關於種子的收藏
【後院】
桑葚
楊桃樹
檸檬桉
在山裡走
指環
夜間探照
十年
游泳池
後記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