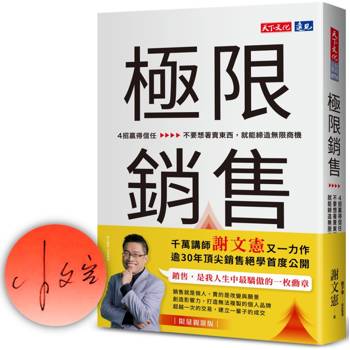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
《蕉風》誕生於馬來西亞建國前夕,不僅是大馬最重要的華文純文學雜誌,也是世界出版史上最悠久的中文文學刊物。相對於冷戰時代激烈的革命文學主張,《蕉風》站在「非左翼」立場,大量引介文學新思潮與世界文學,並提供文壇新人嘗試創作的舞台,捍衛文學的獨立性,為馬華文學留下可貴的遺產。由於只發表中文作品,也讓《蕉風》與大馬華人的命運緊緊捆綁在一起,一定程度地見證了華人在這個民族國家的處境。
《《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以歷史為經,人物為緯,藉由文獻收集與細膩分析,定位《蕉風》在馬華文學發展脈絡中的歷史座標。林春美通過南來文人的著述與理念,闡釋《蕉風》初期的「純馬來亞化」主張,並爬梳馬華新文學體制建立之歷程;繼而藉由分析60至70年代馬華現代主義文學作品,觀照在蕉風椰雨中成長起來的本土第一代現代小說家。
作者簡介
林春美
馬來西亞檳城人,祖籍福建福州。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文學雜誌《蕉風》主編,現任博特拉大學中文專業副教授。著有散文集《給古人寫信》、《過而不往》;論文集《性別與本土:在地的馬華文學論述》;編有《鍾情11》、《週一與週四的散文課》、《青春宛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議性課題選》(合編)、《馬華佛教散文選(1982-2010)》(合編)、《與島漂流:馬華當代散文選(2000-2012)》(合編)、《爬樹的羊:馬華當代散文選(2013-2016)》(合編)、《野芒果:馬華當代小說選(2013-2016)》(合編)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