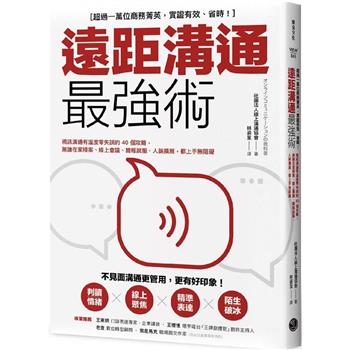圖書名稱:臺灣人意象
本書探討當代香港與大陸影視作品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中,如何透過鏡頭凝視與劇本書寫,建構臺灣與臺灣人的形象。臺港中三地政治分割長達逾半世紀,各自形成不同的文化與創作風格,加以個別官方意識型態的霸權宰制,框架了三地影視題材與方向。這種人為的阻隔,讓兩岸三地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必須隔著好幾層紗在觀看彼此,進而產製了不少帶有刻板印象的作品;換言之,臺港中都各自為彼此建構了所謂的「他者」,這些被想像、被生產、甚至是被發明的他者,其實是再現研究上饒富理論與旨趣的主題。
1990年代以後,隨著兩岸關係的解凍以及香港1997年的回歸,臺港中的民間社會展開實質接觸互動,影視人同步展開頻繁交流,透過影視作品對彼此的凝視又推進到全新的階段,經過實際接觸與交流所產生的刻板印象與互文性,也大幅影響兩岸三地的電影創作,若干在影像語言中作為彼此凝視所生產、建構的他者,同樣具有很大理論與研究旨趣,而香港與大陸之間的跨境再現研究,其實已累積了相當多的學術文獻,但港臺與兩岸間的跨境再現,特別是「臺灣再現」這個領域,卻是一個很大的研究缺口,作品稀少固然是其中主要的因素,但即便是少數作品仍有很大的論述空間,本書即是針對相關華語影視作品中涉及這個相關主題的文本進行論述分析,嘗試補足這個缺口。
從影視作品識讀政治──香港與大陸的電影、電視劇如何凝視臺灣?如何建構臺灣意象?
看本書精闢分析──
►從偉人建構與傳記電影,談1980年代兩岸「孫文形象」之再現
1986年兩岸同步拍攝孫文傳記電影,敘事觀點卻截然不同,官方政治立場是如何從電影鏡頭再現「一個歷史,兩種史觀」?
►從認同、黑道敘事與臺灣政客形象,談港產電影的「臺灣政治」再現
香港經歷1997年的回歸的同時,臺灣正邁入政治結構變動最劇烈的年代,「黑幫電影」集中再現的黑金掛勾、幕後交易、收編背叛等,有多少是臺灣的政治現狀?
►從香港凝視,談1960年代香港電影中的臺灣原住民
透過漢人男性/原住民女性的二元對照,影視作品時常以扭曲、拼貼、刻板印象化的手法再現漢人觀點的「異族奇觀」,觀眾觀影時應如何發現?
►從陸劇《原鄉》,談再現的臺灣警備總部與眷村老兵
一部以臺灣老兵返鄉探親為題,卻從未在臺灣播映的電視劇,負面的警總形象雖確有其背景,但與當時的社會現狀真的相符嗎?
►從身分政治與撒嬌論述,談大陸電影《撒嬌女人最好命》中的臺灣女性
撒嬌女的身分設定,為何總是臺灣女性?是「臺灣腔」的原罪?還是某種政治型態下的想像?
作者簡介
倪炎元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中國時報》前總主筆。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媒體資歷豐富,1987年至2012年任職《中國時報》,歷任專欄組記者,專欄組主任,特案中心副主任,特案中心主任,主筆、總主筆等職務。近年曾先後受邀擔任財政部賦稅署、農委會漁業署、中油公司及司法院等政府機關與事業機構的專題講座,講授有關新聞發布、公共關係與危機處理等課題。
已出版著作:《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比較臺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月旦,1995)、《別笨了,問題在政治:2001我見我思》(時報,2001)、《再現的政治:臺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韋伯,2003)、《公關政治學:當代媒體與政治操作的理論、實踐與批判》(商周,2009)。
繪者簡介
倪瑞宏
1990出生於臺北,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研究所畢業,目前全職創作生活中。創作主軸在研究當代迷茫精神狀態,習慣用帶有黑色幽默的高彩度繪畫與空間裝置,來描述我們身處的世界和那些說也說不清的關係。作品曾入選2019年「臺北美術獎」,曾參與了第29屆「金曲獎」插畫設計,2020年將創作歷程出版成《仙女日常奇緣》一書廣受好評,現在仍以成為臺灣好媳婦目標努力中。
Official:juihungni.carbonmade.com
Facebook:倪瑞宏 Ni Jui_Hung
Instagram:juihung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