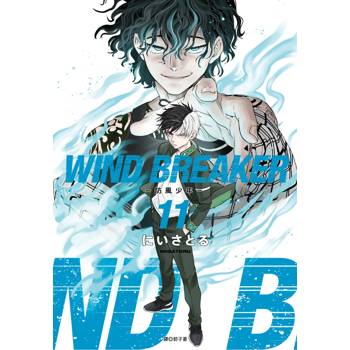即將破曉的嚴寒之中,黎諾‧岡薩雷斯(Leonor Gonzáles)從秘魯安地斯山脈間一處冰雪峰頂的石屋走出,跋涉山徑,仔細巡查落石可有金色斑痕。如同歷代先祖,她背負一袋袋沉重石頭蹣跚而行,拿簡陋的鐵鎚猛敲,腳踩輾碎,再磨壓成細砂礫。在罕見的幸運日裡,將砂礫混入汞溶液中晃動,她能費勁淘出微小至極的金屑。黎諾才四十七歲,可是牙齒已崩落。她的臉孔受烈日不斷烤曬、被寒風吹乾,雙手泛著醃肉的色澤,手指扭曲變形。儘管失去部分視力,每當太陽從阿納尼亞山區(Ananea)的冰封峭壁略微探出頭來,她加入世界最高海拔人類居地拉林科納達(La Rinconada)的女人們,攀爬通往礦坑的陡坡,翻撿所有發著光、裡頭可能有料的石頭,扔進將於黃昏時分一路扛下山的沉重背包。
這幅景象也許出自《聖經》裡描寫的時代,實情則不然。昨天黎諾攀爬山脊「撿礦石」(pallaqueo),像自古以來的先祖一般尋覓黃金,明日她也將踏上同條山徑,重複四歲時第一次陪母親去工作所做的事。她毫不理會三十英里內有一間加拿大礦業公司,正用二十一世紀的笨重機械更有效率地執行相同任務;抑或澳洲、中國、美國的龐大企業,就在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湖另一側投資數百萬美元購置先進設備,搶進拉丁美洲的採礦發財熱。深深挖入地球內裡奪取發光寶藏的事業,在這片大陸擁有長遠根源,從許多方面而言,定義了我們所成為的拉丁美洲人。
黎諾是「白銀、刀劍與石頭」的典型化身,書名舉出的三件事物實為一體,這三種執迷在過去一百年間牢牢困住拉丁美洲人。「白銀」是對貴金屬的貪求,那股著迷支配著黎諾的人生,也支配在她之前的數代人:狂熱追尋她無法享用的獎賞,需求來自她永不踏足的城市。金銀熱的痴迷早在哥倫布時代以前就熾烈燃燒,接著在其不斷爭討美洲之際吞噬西班牙,驅策奴隸與殖民剝削的殘忍制度,引燃一場血腥革命,使區域歷經數百年的不安,而今化身為拉丁美洲未來的最大希望。如同印加(Inca)和阿茲特克(Aztec)統治者視金銀為榮耀象徵,如同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扮演最主要貴金屬供應商而變得富裕強盛,礦業依舊是當今拉丁美洲前途的重心。即使礦場有限、即使狂熱注定終結,那股執迷存續至今──挖出閃爍珍寶,再一船船裝滿運走。
黎諾身為「刀劍」的產物,程度不比「白銀」少,拉丁美洲永無休止的強人文化如影隨形。那是這片區域的傾向,就像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何塞‧馬蒂(José Martí)、馬利歐‧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及其他人所描述的,憑恃單方面展示令人驚懼的權力來解決問題。借助殘忍,仰賴力量、威嚇,以及對獨裁者和軍隊的傲慢偏愛,鐵拳頭(la mano dura)至上。
早在西元前八百年好戰的莫切文明(Moche),暴力必定是容易採取的權宜之計,到阿茲特克和印加帝國統治時愈演愈烈,在西班牙將領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和法蘭西斯可‧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的殘暴教導下更加精通且制度化,以致十九世紀拉丁美洲獨立的慘烈戰事期間變得根深柢固。暴力的遺緒包括國家恐怖主義、獨裁統治、無止境的革命,阿根廷的骯髒戰爭(Dirty War)、名為光明之路(Shining Path)的秘魯共產黨、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墨西哥的犯罪集團,以及二十一世紀的毒品戰爭。刀劍仍是拉丁美洲有權有勢者的工具,情況一如五百年前,當時道明會(Dominican)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悲嘆西班牙殖民地「被印地安人流不盡的血哽住了」。
不,黎諾對高壓和暴力並不陌生。她的先祖生活在亞地帕拉諾高原(altiplano),被印加人征服並強制勞役,其後又被西班牙征服者再度占領奴役。數百年來,她的族人被迫依米塔制度(mitmaq)的需要遷徙──印加帝國於征服地區實施的強迫勞役制度,西班牙隨即效法。此外人們也被移往教會的「傳教村」(reductions),持續投入重新安置大量原住民的雄圖大業,目的是拯救他們的靈魂。十九世紀時,黎諾的族人受武力驅趕強逼上戰場,為革命對立的雙方犧牲生命。到二十世紀為了躲避光明之路的恣意屠殺,他們愈退愈高,直入安地斯山脈的冰雪地帶。不過即使是海拔一萬八千英尺、空氣稀薄的高山屋舍,刀劍仍具主宰力量。現今在偏遠、無法紀的拉林科納達礦城,謀殺和強暴猖獗,活人祭品被獻給山中惡魔,沒有一個官派警察局長敢去任職。在橫暴的力量面前,黎諾跟五百年前的祖先同樣脆弱。
每天醒來時,黎諾摸一摸放在窄床橫架上的灰色小石頭,旁邊是她已逝丈夫胡安‧索斯托‧歐丘丘克(Juan Sixto Ochochoque)的褪色照片。每晚跟兒孫擠進同一張毛毯之前,她再摸一次。「他的靈魂安息在石頭裡。」她在我造訪寒冷山屋時訴說。僅單一房間的室內不超過十平方英尺,她跟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和兩個孫兒傍著山間的冰川前緣同住。她與照片裡的紅臉礦工胡安不曾正式成婚;在黎諾認識的人裡,沒人曾踏入教堂許下誓約。對她而言,胡安是她的丈夫和孩子的父親,從礦井塌陷、致命氣體充斥肺部害他送命那天起,擺在她床頭的灰色圓石就成為胡安的象徵,甚至代表黎諾的全部精神寄託。如同北起格蘭河(Rio Grande)、南至火地群島(Tierra del Fuego)的眾多原住民,黎諾只接受能反映先人神祇的天主教教義。聖母瑪利亞是大地之母帕查瑪瑪(Pachamama)的另一面,看護我們腳下的土地,所有豐沛泉水的源頭。神是阿卜(Apu)的同義詞,意指山巒間的神靈,能量來自太陽並棲身石子表面。撒旦就是蘇帕伊(Supay),掌管死亡與陰間的苛刻魔鬼,出沒於地底深處的黑暗內裡,索求安撫平息。
黎諾的石頭代表千年來牢牢支配拉丁美洲的第三種執迷:此區域對於宗教制度的熱烈信奉,無論是神殿、教會、繁複的大教堂或神聖的石堆皆然。在相隔千年的前哥倫布時期,強權彼此征服後的當務之急即為搗毀對方的神祇。西班牙征服者抵達美洲後,阿茲特克和印加人為榮耀神靈立起的勝利紀念石碑,常遭拆貶淪為雄偉主教座堂的基座。神聖事物的特殊含義並未在被征服者心中消逝。石頭堆疊於石頭之上,宮殿建造在宮殿頂端,教會蓋在每一座重要的本地神殿或瓦卡紀念碑(huaca)上,使宗教變成哪方占上風的有力、具體提示。即使時光消逝,即使天主教已成為拉丁美洲勢力最龐大的宗教體系,即使其中一些追隨者開始被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ism)勸走,拉丁美洲人依舊信仰虔誠。人們路過教會時朝身前畫十字,在家中建神龕,皮夾裡攜帶聖人肖像,跟古柯葉說話,掛十字架在後視鏡上,口袋裡裝滿神聖的石子。
黎諾不是唯一受到白銀、刀劍與石頭束縛的個體,無須往外驗證太多人際分隔,就能發現拉丁美洲多數人的命運跟她綁在一起。採礦在墨西哥、秘魯、智利、巴西和哥倫比亞恢復四百年前的首要地位,礦業取得斐然成就,包括重新定義進步、促進經濟、幫助人們脫貧,並且觸及社會結構的所有層面。貴金屬從鄉間傳遞給城市搬運工,從棕色雙手交給白皮膚的手,由窮人運給富人。從黎諾山屋下岩石裡挖鑿出黃金,推動了複雜的經濟:離她家門數步之遙的破陋啤酒吧、山腳下普提納鎮(Putina)的成群童妓、首都利馬(Lima)的金融家、加拿大的地質學家、巴黎的社交名流、中國的投資人。產業獲利最終流往海外的多倫多、丹佛、倫敦、上海等地,正如黃金曾搭乘西班牙加利恩帆船(galleon)跨越大西洋,運抵馬德里、阿姆斯特丹與北京。收益的普遍流向從未改變,短暫逗留後隨即向外輸出,夠本地人在酒館喝杯啤酒,或買隻蒼蠅光顧過的羊腿掛上屋梁。錢財就這麼消失無蹤,遠赴他方。
「刀劍」同樣擁有滄桑歷史,從奇穆王國(Chimú)戰士拿來切開敵人胸膛的鋒利石刃,到塞達幫(Zeta)在墨西哥華瑞茲城(Juárez)取用的粗陋菜刀。暴力文化在拉丁美洲盤旋不去,潛伏暗處等待爆發,威脅這片地域邁向和平繁榮的蹣跚進展。在貧富不均分明的區域,刀劍一直是唾手可得的工具:在奧古斯多‧皮諾切(Augusto Pinochet)掌權的一九七○年代智利、多為識字白人族群間發揮效用,一如現今宏都拉斯文盲貧民的染血街道。世界上最危險的十座城市全都在拉丁美洲國家,難怪美國出現從墨西哥、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逃來的大批絕望移民。恐懼是驅使拉丁美洲人北漂的動力。
至於緊攫心靈的「石頭」,制度性宗教無疑在上述美洲地區扮演關鍵角色,並且延續至今。溯及印加帝國時代,當偉大統治者帕查庫特克‧印加‧尤潘基(Pachacutec Inca Yupanqui)與圖帕克‧印加‧尤潘基(Tupac Inca Yupanqui)「改變世界」,征服南美長幅土地擴張帝國,並強迫被征服的群眾敬拜太陽,信仰就一直是威逼的武器與社會凝聚的手段。阿茲特克人對征戰擁有跟印加人相似的渴求,也同樣熱衷於運用宗教。但是他們皈依信仰的途徑截然不同:只要他人的神與己有的神在許多方面共通,阿茲特克人常接納新近征服者的神靈。漫步於任一座中美洲或安地斯山村,你將發現那些古老信仰透過現代藝術和儀式傳統生動傳達。
而今,儘管拉丁美洲流傳的信仰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亞洲與歐洲等許多種類,五百多年前西班牙強加的信仰仍深深銘刻此地,也就是忠貞不移的天主教徒。全球整整百分之四十的天主教徒住在這裡,形成凝聚信眾的堅定紐帶,從烏拉圭首都蒙特維迪歐(Montevideo)一直到墨西哥大城蒙特雷(Monterrey)。讓六個南美共和國獲得自由的西蒙‧玻利瓦(Simón Bolívar),確曾夢想這些說西班牙語、信奉天主教的美洲國家,有可能形成開創偉業的強大統一力量。也許西班牙君主竭盡全力防止殖民地之間互通、貿易或建立和睦關係,卻在帶領人們來到耶穌腳前時就讓他們永遠聚在一起。玻利瓦解放的多元、紛擾西班牙語基督教人口,最終從未在他帶領下組成強盛的泛美聯盟。但是今日的教會一如玻利瓦的時代,依然是拉丁美洲最受信賴的體制。
這本書關照千年來形塑拉丁美洲社會的三項因素,無意偽裝成全面性的歷史定論。相反地,它企圖闡述拉丁美洲人民的歷史遺產與我們過往的三項要素,或許能彰顯未來的某些面向。在我們共有的執迷之中,必定有其他要素更能鮮明描繪這片大地:例如我們對藝術的迷戀,對音樂的熱忱,對烹飪的熱情,對修辭的愛好。拉丁美洲人筆下流淌而出的西班牙語,構成當代廣受矚目、最具原創力的文學。也少有其餘區域特質,比我們對家庭的忠誠或是對人性溫暖的傾向更加明亮動人。但是在我看來,上述沒有一種因素像拉丁美洲對採礦的執迷、用殘暴武力寫下的傳奇故事或者宗教那般牽動人口,在地景留下痕跡並創造歷史。
這三種執迷並非獨立敘事能訴說分明,它們的歷史在過去一千年裡激盪疊覆,變得緊密交纏,就像黃金、信仰和恐懼在黎諾生命中形同緊密編織的毛線。然而拉丁美洲對宗教和暴力的傾向,以及堅守未必導向永續發展的採礦業古老形式,多年來使我深深著迷。我相信這三種傾向的歷史,能讓我們更了解拉丁美洲人自身的面貌。如同一位歷史學家曾說,我們是「生來要削弱傳統真理的一塊大陸」,面向我們自身,不同於其他任何地方,別處盛行的理論或教條鮮少在此生根。多年來投入追尋這股密纏歷史的縱橫織線,也使我了解不可能說出完整的故事。
你要如何解釋半個地球和它的人民?那是不可能的任務,千真萬確,五百年來扭曲的歷史記載使情況更為複雜。儘管如此,我認為身為西裔美國人的經驗會產生一種共通點──某種具體特徵,假如你接受這個說法。我也把這特徵看作兩個世界重大衝突的直接產物,由此經驗產生違背本意的寬容態度定義了我們。在北半球找不到對等的產物。
在拉丁美洲,我們或許未必曉得自己確切代表的人種,卻清楚知道我們深繫於「新世界」而非「舊世界」。歷經數百年未受約束的結合,我們的外表更接近褐色而非白色,也比某些人或曾想像的更具黑皮膚或印地安血統。可是從兩種文明的第一次接觸(First Contact)開始,原始的政治力量就牢牢握在每一代焦慮不安的「白人」手裡,真正去衡量我們的認同一直是薄弱主張。隨你怎麼說,但是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歷史經久不衰,跟北美原住民的命運迥然相異,暗示在本地有著截然不同的解釋。我秉持無上謙卑提出我的解釋,希望傳達我從中領悟的某些觀點。
雖然我父親的家族在秘魯源遠流長近五百年,我的祖母羅莎‧西斯奈洛斯―西斯奈洛斯‧德‧阿拉娜(Rosa Cisneros y Cisneros de Arana)對西班牙的一切事物擁有無比熱忱。她常對我提起,西班牙習俗要讓兒子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好為茁壯的社會樹立棟梁。依照邏輯,一個兒子應成為世俗閱歷豐富之人(律師、政治家或商人),另一個兒子從軍,第三個當神父。第一個兒子協助國家的權力與金融事務以確立榮景,軍人報國維護和平,神父則教我們通往神的道路,開啟進天堂的大門。我從未在歷史書籍裡看過這項習俗的資料,卻在造訪拉丁美洲國家時反覆聽說。最終我明白金融家、將軍與主教確實是我們共同社會的支柱,他們扮演關鍵人物,使寡頭統治者、性別與種族在西班牙開創的嚴格階級制度裡各司其職。由君主子嗣、士兵和大祭司構成統治的三股合作勢力,同樣掌控了印加人、穆伊斯卡人(Muísca)、馬雅人(Maya)和阿茲特克人。在許多例子裡,最高統治者渴望同時成為以上三者。隨你怎麼說,不過三權鼎立的治理公式已在南美洲運作數百年。古老文化藉此擴張征討,殖民者藉此牢牢掌控受殖民人口的財力、武力與靈魂。縱然拉丁美洲帶給世人諸多贈禮,無論過往文明再怎麼被歌頌,這片區域持續受到亙古未變的支配力量統治,它們是白銀、刀劍與石頭。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白銀、刀劍與石頭:魔幻土地上的三道枷鎖,拉丁美洲的傷痕與試煉的圖書 |
 |
白銀、刀劍與石頭:魔幻土地上的三道枷鎖,拉丁美洲的傷痕與試煉 作者:瑪利.阿拉納 / 譯者:楊芩雯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7-0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白銀、刀劍與石頭:魔幻土地上的三道枷鎖,拉丁美洲的傷痕與試煉
2020年安德魯‧卡內基優秀小說與非小說獎入圍作品
執迷於採礦、用殘暴武力寫下傳奇故事、宗教的牽動人口
在這片魔幻土地留下痕跡,創造歷史!
怎樣全面掌握拉丁美洲的歷史和現實?這片土地上的人有著什麼樣的特徵?
無論是神祕的古代文明、鮮明的文學風格,還是動盪的政局、不平衡的發展,拉丁美洲究竟為何與世界其他地區如此不同?讀完這本書你會有答案!
專文導讀
李毓中(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褚縈瑩(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國內學者專家一致推薦
石雅如(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副教授)
何國世(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副教授)
宮國威(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主任)
耿哲磊(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系主任)
張翠容(記者)
陳小雀(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教授)
(姓氏排列按筆畫順序)
《白銀、刀劍與石頭》作者瑪麗‧阿拉納出生於秘魯利馬,童年時期經歷了兩國生活的轉換和適應,多年來思考自己的拉美文化身分,既有豐富的切身經驗,又能具備他者視角;既有批判,又有反思,以記者身分深度追蹤三位當代拉美人,短則五年,長則二十五年,在本書中用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和扎實的紀實寫作方式,將這三位訪談對象的故事與拉丁美洲過去千年的歷史無縫地編織在一起,使讀者閱見礦工、士兵和神父的生活軌跡如何與數百年前的祖先遙相呼應,從而闡釋了從前哥倫布時代至今,定義拉丁美洲的三個恆久主題:來自外部的對資源的無盡索取(白銀)、揮之不去的暴力陰影(刀劍),以及根深柢固的宗教信仰(石頭)。串聯歷史與現實,拋開「勝利者視角」,阿拉納嘗試挖掘拉丁美洲的獨特經歷所奠定的「本性」,勾勒出這片土地上人民的身分、心態與命運。
拉丁美洲蘊藏的貴金屬資源,白銀占其中絕大部分。從前哥倫布時代,金銀熱的痴迷早在哥倫布時代以前就熾烈燃燒,接著在其不斷爭討美洲之際吞噬西班牙,驅策奴隸與殖民剝削的殘忍制度,引燃一場血腥革命,使區域歷經數百年的不安,而今化身為拉丁美洲未來的最大希望。
縱觀從阿茲特克與印加帝國到血腥的十九世紀獨立戰爭,再到光明之路的國家恐怖主義,以至今日的毒品戰爭。拉丁美洲一直瀰漫著「刀劍」的暴力衝突文化。
不過拉美人本身的宗教文明傳統信仰,是豐富多元的迷人色彩,具體呈現在神廟、華美的大教堂或簡樸石頭堆,描繪出拉美地區對於宗教制度的狂熱信守,內化在石頭裡。
白銀、刀劍與石頭,是關於拉美大陸的波瀾起伏肖像畫,豐富多采的故事涵蓋千年歷史,也描寫活生生的真實人物:身形瘦小的寡婦黎諾養育五個子女,住在世界最高的人類居地拉林科納達,透過她講述拉美人採礦的歷史。「白銀」是對貴金屬的貪求,那股著迷支配著黎諾的人生,也支配在她之前的數代人:狂熱追尋她無法享用的獎賞,需求來自她永不踏足的城市。
古巴毒販卡洛斯在安哥拉戰場練就使刀手法,帶著他的機靈狡詐去到美國,隨後成為警方線人,彷彿呼應著阿茲特克人、皮薩羅、特魯希佑和皮諾切的暴行。暴力文化在拉丁美洲盤旋不去,潛伏暗處等待爆發,威脅這片地域邁向和平繁榮的蹣跚進展。在貧富不均分明的區域,刀劍一直是唾手可得的工具。世界上最危險的十座城市全都在拉丁美洲國家。恐懼是驅使拉美人北漂的動力,他們大批從墨西哥、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絕望逃走至美國。
緊攫心靈的「石頭」,制度性宗教無疑在上述美洲地區扮演關鍵角色,並且延續至今。
而今,儘管拉丁美洲流傳的信仰包括美洲原住民、非洲、亞洲與歐洲等許多種類,五百多年前西班牙強加的信仰仍深深銘刻此地,也就是忠貞不移的天主教徒。住在拉巴斯的耶穌會修士哈維爾,四十年來他努力讓天主教教義與安地斯山的克丘亞人和艾馬拉人共存,但是本地人寧可相信先祖的信仰。
一如本書書名所述,白銀、刀劍與石頭,是這片魔幻土地上的三道巨大沉重枷鎖,交織成拉丁美洲的歷史傷痕,也試煉它未來的命運。
國際媒體專家學者一致好評
在這本「來得適時且傑出的著作」(摘自NPR書評)中,瑪利‧阿拉納將這些故事細密織入過往千年的歷史,闡明自前哥倫布時代就定義拉丁美洲的三道橫亙主題:外國貪求此地的礦藏財富,根深柢固的暴力傾向,以及歷久不衰的宗教力量。《白銀、刀劍與石頭》結合『淵博的歷史分析、深入的報導和政治評論……本書傳達諸多知識與可靠意見,值得擁有廣大讀者。」
──阿瓦洛‧恩里格(Álvaro Enrigue),《紐約時報》
阿拉納來得適時且傑出的著作並非一部歷史書,也不是人們常見的那些文化行旅,對全球各區域進行沉思書寫。她的書結合故事、新聞報導、歷史,最重要的是還有洞察……。
──NPR(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以既清晰且動人的敘事探討拉丁美洲的身分認同難題……她兼具廣度與高度的描寫讓人想起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阿拉納給我們一部故事中的史詩,講述一個因財寶、權力與控制欲而相連的區域,以及長久束縛人們的情感黏著基礎。
──馬瑟拉‧戴維森‧艾維兒(Marcela Davison Aviles),NPR.org
一部拉丁美洲縱橫史……既令人著迷且包羅萬象。書中涵蓋如此多層面令人讚嘆。
──伊薇特‧貝納維德斯(Yvette Benavides),《出版人週刊》
阿拉納對於拉丁美洲史的嫻熟在這本書大放異彩,以獨特且引人入勝的視角,探問數百年來形塑拉丁美洲生活方式的三道『試煉』……在這本探索、連結與分析的傑作中,阿拉納提出富有新意、扣人心弦且讓人重新看待的觀點,解讀一個受到毒辣貪婪與凶殘暴政出賣,充滿生命力而壯麗的區域。
──伊薇特‧貝納維德斯(Yvette Benavides),《書單》星評
秘魯出生的作者瑪利‧阿拉納的最新力作,把我們帶往神祕且備受誤解的拉丁美洲核心……涵蓋層面廣大而複雜,但是阿拉納的敘事與她顯而易見的憐憫之心,引領我們穿行過往千年,踏上引人入勝卻也苦澀多變的旅程,前往我們全都應當理解之地。
──伊薇特‧貝納維德斯(Yvette Benavides),《聖安東尼奧新聞快報》
這位秘魯出生的作者深入探究拉丁美洲受西方強權剝削的三道癥結……一段出奇簡明卻又包羅萬象的歷史。一部極其動人的重要之作,提供新方式去思索「發現美洲新大陸」。
──伊薇特‧貝納維德斯(Yvette Benavides),《科克斯書評》星評
瑪利‧阿拉納是簡練而銳利的作者與觀察者,對於少有人瞭解的傳奇拉丁美洲,為我們做出縝密且發人深省的描繪。《白銀、刀劍與石頭》結合歷史與當代報導寫作,是一本令人信服的讀物。
──瓊‧馬查姆(Jon Meacham),著有《美國的靈魂:為我們更好的天使而戰》,NPR.org
行文優美,研究嚴謹……凡是努力理解拉丁美洲動盪過往、以及我們與南方鄰國危機四伏關係者的必讀之作。阿拉納對此主題的清晰、公正處理讓我們獲益良多。
──芭芭拉‧穆西卡(Bárbara Mujica),《華盛頓獨立書評》
研究嚴謹,本書強項是史詩般敘事的力量,優美行文與豐富的人物描繪……阿拉納的長處是說故事的力道與情感,以及她說明過去一千年是什麼形塑拉丁美洲時的字字珠磯……一本絕妙好書。
──湯姆‧格傑頓(Tom Gjelten),《華盛頓郵報》
彷彿一隻翱翔安地斯天際的兀鷹,阿拉納寫出拉丁美洲歷史的全面概觀。歷史常由贏家撰寫,但是這本書激盪著對於受害者與被看輕之人的情感,也頌揚使拉丁美洲如此受鍾愛的文化成就、充沛活力與慷慨氣度。
──約翰‧黑明,《征服印加人》作者
要追溯一個大陸的靈魂是項不凡偉業,阿拉納以學者的精確、道德的縝密與優雅的寫作風格完成。對於有興趣真正瞭解拉丁美洲面貌、以及拉丁美洲從何而來的任何人,本書必定是第一步。
──胡安‧加百列‧瓦斯奎茲,《聽見墜落之聲》作者
透過書寫的力量與美感,阿拉納使世上最複雜的其中一個區域顯得異常清晰。我從未讀過一本書有如此驚人的廣度與錯綜複雜的深度,同時捕捉到浩瀚歷史與新聞報導扣人心弦的即時性。她訴說的故事將令你心碎,使你耳目一新,卻也讓你更清楚瞭解拉丁美洲,並對於拉美人民的力量與堅毅深深驚嘆。
──坎迪斯‧米拉德(Candice Millard),《帝國的英雄》作者
她的能量與熱情無疑將吸引眾多讀者。」
──凱莉‧吉布森(Carrie Gibson),《衛報》
廣受讚譽的作者瑪利‧阿拉納交出一部拉丁美洲文化史,以及形塑該區域特徵的三種驅力:剝削(白銀)、暴力(刀劍)、宗教(石頭)。本書研究嚴謹,最大強項是史詩般敘事的力量,行文的優美,以及人物的描繪多采多姿……極佳之作。
──《華盛頓郵報》
《白銀、刀劍與石頭》是瑪利‧阿拉納浩瀚而令人驚嘆的拉丁美洲新史,對於任何想瞭解這個半球與我們當前危機的人是必讀之作。
──胡莉亞‧奧瓦瑞茲(Julia Alvarez),《蝴蝶的時間》作者
作者簡介:
瑪利‧阿拉納(Marie Arana)
生於秘魯利馬,著有進入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的回憶錄《美國女孩》(American Chica),兩本小說《玻璃紙》(Cellophane)和《利馬夜》(Lima Nights),《華盛頓郵報》知名專欄文集《寫作生活》(The Writing Life)及傳記《玻利瓦:美洲解放者》。《美國女孩》亦入圍筆會頒給首本非小說著作的瑪莎‧艾布蘭德獎決選,《玻璃紙》則入圍頒給首本小說的老約翰‧薩金特獎決選。美國國會圖書館文學部門主任,曾擔任《華盛頓郵報》文學編輯,生活於華盛頓特區
譯者簡介:
楊芩雯
專職譯者,現居台南。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畢,譯有報導文學《製造俄羅斯》、《總統的人馬》、《柬埔寨》,社會科學《泰國》、《蝗蟲效應》,小說《強尼上戰場》、《黃衣國王》,傳記《提姆.庫克》等書。
章節試閱
即將破曉的嚴寒之中,黎諾‧岡薩雷斯(Leonor Gonzáles)從秘魯安地斯山脈間一處冰雪峰頂的石屋走出,跋涉山徑,仔細巡查落石可有金色斑痕。如同歷代先祖,她背負一袋袋沉重石頭蹣跚而行,拿簡陋的鐵鎚猛敲,腳踩輾碎,再磨壓成細砂礫。在罕見的幸運日裡,將砂礫混入汞溶液中晃動,她能費勁淘出微小至極的金屑。黎諾才四十七歲,可是牙齒已崩落。她的臉孔受烈日不斷烤曬、被寒風吹乾,雙手泛著醃肉的色澤,手指扭曲變形。儘管失去部分視力,每當太陽從阿納尼亞山區(Ananea)的冰封峭壁略微探出頭來,她加入世界最高海拔人類居地拉林科納達...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國際媒體專家學者一致好評
導讀一/李毓中(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導讀二/褚縈瑩(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第一章 仍在追尋黃金國
第一部 白銀
第二章 山神的礦脈
第三章 金屬獵人
第四章 白王的小徑
第五章 盲目的野心
第二部 刀劍
第六章 嗜血欲望
第七章 形塑拉丁美洲心靈的革命
第八章 強人崛起與攔路惡龍
第九章 怒火悶燒
第三部 石頭
第十章 從前的神靈
第十一章 以石頭壓制石頭
第十二章 神殿
結語 這就是我們的天性
謝辭
注釋
參考書目
導讀一/李毓中(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導讀二/褚縈瑩(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第一章 仍在追尋黃金國
第一部 白銀
第二章 山神的礦脈
第三章 金屬獵人
第四章 白王的小徑
第五章 盲目的野心
第二部 刀劍
第六章 嗜血欲望
第七章 形塑拉丁美洲心靈的革命
第八章 強人崛起與攔路惡龍
第九章 怒火悶燒
第三部 石頭
第十章 從前的神靈
第十一章 以石頭壓制石頭
第十二章 神殿
結語 這就是我們的天性
謝辭
注釋
參考書目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