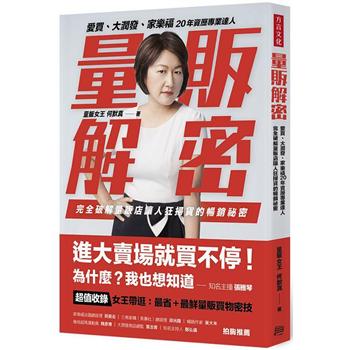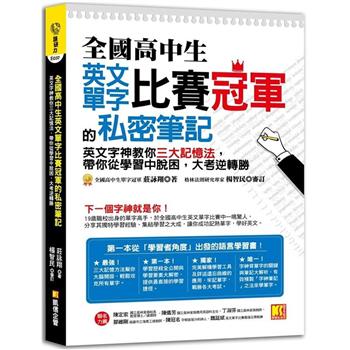華麗殘酷且近乎魔幻
滿載異域感的異變系小說
時報文學首獎得主白樵 亮眼處女作
文學恩師 阿盛、袁瓊瓊 惜愛推薦
石知田、林佑軒、馬翊航、陳思宏、陳栢青、鄧九雲、羅毓嘉 齊聲評讚
(照姓氏筆畫順序)「異地情人朋友們的東方,是薩伊德東方主義的近東:一座虛擬於符號世界裡,想像的,偏差的東方。那是我嫩滑的肌膚,我的黑髮,我的深棕色瞳仁所指涉的所有,而不是個別性的我……」──白樵
備受期待的青年作家白樵,散文和小說皆各有擅場。多年來他也從事劇場、編舞等跨界藝術,此回終於交出首部精湛的小說作品。這是一本跨越同志、異性戀、異文化議題的小說,探討了後殖民、強權、跨文化等主題。
曾經留學法國的白樵當年因一場重病,在巴黎送急診室,昏迷兩個月。他與死神擦身而過,脖子上也因此留下了插管的痕跡,他笑稱:「這是巴黎給我的刺青。」雖然因此不得不放棄當地的學業,但歸國後仍努力寫作不輟至今,並屢獲大獎。
起初棄島嶼逃逸至異國的白樵,創作初期竟無法以第一人稱視角出發,也難以成長的地域或都市為題材。早先的作品皆源自國外生活點滴,許多段落甚至神似引人入勝的翻譯小說。儘管那些篇章亦是十分迷人,但他仍想找回自己在島嶼的生命軌跡,重新埋頭書寫,不斷在記憶與情感間折返,由最遠卻也最熟悉的部分,漸次踏入最近卻也最陌生的領地,終於深入了他的島,與他曾最想逃避的,來自東方的我之意識主體。
於是最終成就了這本緊扣殖民與解構之書。八篇短篇小說切分為三輯:從描繪掙扎於歐洲生活各式角色的「他者」,翻轉自我身世的「邊界」,最後讓渡於台北「我城」的回歸之旅。白樵的文字乍看十分華麗,實則以冷靜視角包裹著濃烈的情感,周芬伶稱其「頗得海派文學之韻味」,鍾文音也在評讚其得獎作品〈南華夫人安魂品〉時點出,像似「一種運用作者獨特語感腔調所寫出的臺版式的追憶似水年華。」
白樵不僅是說故事高手,擅長解構的他也思索著,既有薩伊德的《東方主義》,或許也有某種「西方主義」的可能,而此書即以篇篇迷人的小說,不但坦露青春回憶與情慾冒險,同時也如多面稜角鏡般,呈現他對東西文化消長以及殖民位階的探索與詮釋。
作者簡介:
白樵
一九八五年台北生,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廣告學系畢,巴黎索邦大學斯拉夫研究碩士肄業,現從事翻譯,編舞等工作。
曾獲時報文學獎首獎、鍾肇政文學獎首獎等。作品散見《中國時報》、《聯合報》、《幼獅文藝》、《聯合文學》各大副刊及文學媒體。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白樵背景特殊,在國外的時間很長。長著東方面孔,不過靈魂絕對是異鄉人。他同時在地域的異鄉,也在時光的異鄉。我第一次看他作品時,疑惑這到底是翻譯還是創作,不僅是背景地區和角色名字,連文字中的情感和思索,都充滿異國風味。白樵文字很乾淨和平靜,但是情感強烈到嚇人。寫作於他好像是本能,筆尖直接連結著他的血液。──袁瓊瓊(作家)
白樵對於各種「異」的關照,以及在地、臺灣元素的暫時退場,不只讓小說「變得像外國」,而有空間展現出多重「作為」:如何「作為」一個異變者;面對諸種差異,如何有所「作為」。身份與(多數是極端的)行動,是小說中的醒目部位。但語言的黏著與緊張,惡行的循環與更新,記憶的魔幻與交換,也驅動讀者繼續向內探勘,是否暗藏其他啟示與處置。儲藏是面向過去的累積,也是背朝未來的重啟。《末日儲藏室》不只是白樵個人意義上的新作,也是他所屬世代的寫作新局。 ──馬翊航(作家)
真相是被寫下之物,白樵用身體在寫作,故事充滿異域感。
這八個主角根本是從地獄走來的人,身上還黏著燒成餘燼的皮屑。
痛,氣味刺鼻,恐怖又迷人。──鄧九雲(作家)
與白樵相識許久,他的直白定義了他的不難懂,而他的聰穎卻又使他難懂得通透。天性賦予了許多迂迴,於是他精於雕琢,用字遣詞總能恰恰捏著分寸。書寫遠方,卻隱約勾勒了自身,那是源於某種無可迴避,卻也是出於內心深處的渴望被乘載。讀著書稿,便是閱其真誠,沈浸在精緻的字花中,觀望他航向自身的姿態,格外迷人。 ── 石知田(新生代演員)
是不是總要離開巴黎,才能光芒亂亮?我們看見,朱嘉漢離開巴黎,從臺灣回望法國,勇猛精進、異彩大放。如今,又有白樵這一本花都書寫,從最絢爛一路寫到最晦暗,可說是一本以身、心、意、筆,不留餘地銘刻篆雋潑灑豔綻之傑作。──林佑軒(作家)
名人推薦:白樵背景特殊,在國外的時間很長。長著東方面孔,不過靈魂絕對是異鄉人。他同時在地域的異鄉,也在時光的異鄉。我第一次看他作品時,疑惑這到底是翻譯還是創作,不僅是背景地區和角色名字,連文字中的情感和思索,都充滿異國風味。白樵文字很乾淨和平靜,但是情感強烈到嚇人。寫作於他好像是本能,筆尖直接連結著他的血液。──袁瓊瓊(作家)
白樵對於各種「異」的關照,以及在地、臺灣元素的暫時退場,不只讓小說「變得像外國」,而有空間展現出多重「作為」:如何「作為」一個異變者;面對諸種差異,如何有所「作為」。身份...
章節試閱
少女伊斯蘭
塞納河畔,蘇利橋旁,一幢樓,恍如墜河之船。
玲正式消失前一年半, 她每週固定一天進入這沉艦腹部,大廳左邊轉角第一間房。 每個禮拜六,固定早上九點至十二點,不多不少剛好一節課時間,她在這冷灰而滿盈水氣的房間裡,學阿拉伯文。
一年半前,玲在家上網,下載了課程大綱,隨意揀個作業天,便乘地鐵從所居的佳麗村橫跨整座水域,來到五區,位於左岸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
她在櫃台領了報名表,填寫資料,並預繳半年學費。整套流程不過五分鐘。玲沿前院廣場走。陽光曬著她的無袖臂膀,同時在大樓鏤空花窗撒下立體剪影 。
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由七零年代名建築師尚・努維設計。聖日耳曼大道旁,玻璃帷幕高聳,微銀狐亮略帶科技感,遠看,卻像一艘倒插入河,靜待沒頂的艦。船身鑲有伊斯蘭遮櫺格柵,方便調亮採光。前院廣場,泊置一架朝後方房舍張裂血盆大口,超現實主義的巨型圓盤裝置。玲朝這異物繞,走走停停。她隔警戒欄觸碰著,挑不同角度拍照。陽光晴好,可拍出強烈對比映像。鼻翼四周的坑疤於光耀下鮮明,在瑪黑區剪的齊耳短髮,無法修飾圓潤臉型。以異星飛盤為景,玲把面頰左擺,右偏,嘗試將手機傾成不同角度。選好照,花十幾分鐘修圖,打卡,上傳至個人社群動態。
玲在主旨處簡單輸入:un nouveau départ。一段嶄新開始。
其實玲也弄不清自己為何想學阿拉伯文,佳麗村,人們俗稱的美麗城,麕集非裔,阿拉伯裔,黑人或與她緣近的亞裔後代。貨真價實移民鎮。玲住的斜坡巷口,就開著許多由阿拉伯青年營業,販賣來路不明廉價二手手機的店,粗食餐廳與雜貨鋪。他們口中喊的,不是玲喜歡的正統阿拉伯文,他們用方言與人日常交談,聽來卻像在市集裡非禮一頭無意經過的牲畜。
她喜歡禮拜時,從清真寺復刻繁花異果的橢圓窗內繞出的祝禱聲。小時候,父親難得休假,會帶她搭地鐵,轉幾個斜坡拐道,前往巴黎大清真寺附近的公園。父親不習慣牽手,他坐遠方長椅,脫鞋盤腿,兀自對空吐煙。玲玩過頭跑太遠時,他會朝沙地啐嘴,再朝她吼叫一聲。
玲懷著小孩特有的秘密,她不敢對父親提及,集體祝唸的阿拉伯文令她出神,聖歌吟遊嗡嗡嗡地在腦中東奔西竄,使人暈眩。那聲音靜電般細密遊走她年幼的皮膚上,爬滿疹子般,癢而酥麻。她用力摳,抓。玲有一回在個人社群動態上分享:comme la jouissance。似高潮愉悅。
玲小小的腳顛顛顛,不自主越飄越遠。禱詞方歇,回神,向父親奔去。她懼怕父親豪亮的音頻,或任何粗氣的辱罵。她把手汗往裙擺抹,撣淨沾了灰的鞋,戰戰兢兢,用食指輕戳父親的臂膀,示意他,可以回家了。
時常,父親對她用命令句。不諳法語的父親與玲使用純淨中文。敬語像菜渣,被父親拿牙籤剔除乾淨。成年後玲思索,自小兩人好像從不是書上標榜的健康親子溝通。溝通屬雙向,父親卻總先朝地上吐一沫口水,再對她喊:「腰桿挺直。吃飯時手別蹭桌上。雙手交疊。大腿闔緊。」她來不及回話,父親便把頭撇開了。
語言或更精煉成否定句。不准,這兩字被父親拆解,混搭成更多變異攣形體:「不准跟深膚色的同學鬼混。禮拜一禁止外出。不許提任何關於妳母親的事。」玲自幼知曉,年老的父親緊守著另一個秘密。
父親過早被生活折騰成一名乾癟又暴躁的老頭了,像不曾見他年輕過,家中無有任何照片可供參照。竹竿似瘦的父親在家,總隨意套件泛黃汗衫,搖扇蹣跚,身上總抹股不知要遮掩什麼的花油香。若逢熱天,汗液醚合著,在父親打了褶皺的薄膚上蒸出酸氣。
玲鮮少抱怨,一如所有佳麗村的黃面孔。學校同學或社區住民,都用一種過度討好的猥瑣姿態,或深怕遭人詬病的小心翼翼過日子。平時低聲交談,少同外人交際,偶有的互動僅存老者間,像父親休假來往的同鄉會成員。
「妳瞧。」 一日,父親戳著報紙頭條對她喊。
「唸出來,大聲點。」父親在凳上摳腳污,並將皮屑拍入塞滿煙屁股的碗裡。
「近郊歐貝維列,一名四十九歲中國裁縫路上遇襲,頭部遭重擊送醫不治。」玲接過報紙,試圖抑止顫抖的音。她瞄到報紙斜下角印著,在法華人同盟即將展開示威的標題。
「您會去嗎?」將報紙遞給父親,用指尖比著標題,玲低聲問。
「妳別給我搞政治。」語畢,父親頭也不回地出了門。
數週後假日進修班開課,玲開始固定每週六,潛入那冷灰沉艦大廳地下一樓,左邊轉角的房間。玲在家,總先偷偷倒掉父親備好的早餐,雖身為自家餐廳主廚,父親手藝實則一般。見桌上浸染酸辛調料的黑糊菜色,玲便消了食慾。巴黎長大出生的她,沒有一個東方的胃。抵達研究中心,她會在樓下自動販賣機前投幣,買杯濃縮咖啡或過甜的兩歐元熱茶,拿著燙手塑膠杯與事先盛好水的保溫壺,在左邊房前等候。
門鎖著,她習慣早到十分鐘。
大廳深灰無窗,寂靜出奇,她聆聽自己的腳步敲在地磚上的回音。敲著,走著,好像就慢慢遠離生活的瑣碎與不順心。她搓手,空調溫度極低,九月溽暑調成人工寒季。沉艦大廳偶爾滑過一兩道黑影,穿灰工作服頭紮黑帽深色肌膚的清潔婦女,整理完洗手間後,她們拉拖把,滑進看不見的角落。
教授阿拉伯文的,是來自阿爾及利亞的老先生阿赫美德。老先生年約六旬,乾淨整齊,常是淺灰西裝,白衫深藍呢背心,配紳士帽或深色鴨舌帽。聲音爽朗,極有朝氣。玲一連給阿赫美德教了三期。 成員人數汰換,半年內,玲始終是教室裡唯一的黃臉孔。學員大多是阿拉伯二三代移民,早嫁北非男子的年輕家庭主婦,或與中東行商業往來的巴黎人。大家散坐橢圓桌,態度不冷不熱,客氣的交際使玲有時學期過了大半,還記不著三分之一人名。
辛西亞例外。她與玲輪流當頭一兩名默默等待阿赫美德來開門的學生。有時兩人碰巧堵在門口,互道聲早,閒聊幾句。玲記得在第一堂課自我介紹時,辛西亞說她是柏柏人後裔。
「啊⋯⋯」阿赫美德拖了長長的音,那尾聲迴盪在不到五人的教室裡。
「柏柏人是阿爾及利亞少數民族。遊牧成性,說方言,與阿拉伯文化自古有著難以切割的曖昧關係。」阿赫美德堆了一個擠滿皺紋的笑,對疑惑的玲解釋。遲到的學生們輕聲敲門,道聲早, 推開椅子,紛紛坐下。
辛西亞面容白皙,雙頰粉嫩。若細看,那經陽光炙烤的淡色雀斑,才會不經意洩漏遺傳的沙漠基因。髮紮至頂,恣意笑時,輕輕搖晃的鬃高馬尾。她是從燦金瀲陽中走來的少女,這是玲對她的第一印象。
「小時候父母把我送進清真寺讀可蘭經,我們跪地朗誦,照上頭母音標示一個字一個字唸,似懂非懂。有時貪睡偷懶,巡檢的伊曼便拿竹竿抽打我們。」報上名字後,辛西亞如是自我介紹。
「不過報紙或書籍上的文體沒標母音,便不會唸了。」聳了聳肩,辛西亞開懷大笑。
「妳為什麼想學阿拉伯文呢?」阿赫美德轉頭問辛西亞正對方的玲。
「不知道。」玲低頭。
「或許,我想做點特別的事情。」她咕噥著,話聲輕飄,像說給自己聽。
辛西亞比玲小七歲,大學新生主修法律。進修班上其他同學年齡懸殊,兩人因此常湊組做對話練習。玲喜歡阿拉伯文的肯定詞,「對」這字像極了用彆扭方式拖拖拉拉發音的,中文的「難」。
「您好,早上好。」辛西亞用阿拉伯語流利開啟對談。
「您好。我的名字,是玲。我,住,巴黎。我,學,阿拉伯,語。妳呢?」 玲緩鈍地,照課本例句回話。
「我的名字是辛西亞,我是法國人,我的父母來自阿爾及利亞。」
「很,高興,認,識妳。」
「很高興認識妳。」
課後,玲跟辛西亞習慣一路寒喧至文化中心旁的聖日耳曼大道再離去。若辛西亞駕駛她父親新購的二手日產車,玲便索性擠在副駕駛座陪辛西亞談天。堵塞車流中兩人耗著,聊生活聊感情,有時隨意轉到中東電台,隨音樂哼哼唱唱,哈比比哈比比,滿嘴我的甜心。
偶爾,兩人會在課外時間碰面,辛西亞開車載她四處逛,那些平時玲隻身無膽踏入的亂區。許多黑人男子在路上隔窗對她們獻殷勤,等號誌轉燈,辛西亞加速離去時,他們會大聲地,對她們拋出各式野蠻髒字,婊子,妓女。辛西亞毫不在意,猛踩油門,右手打方向盤,左手搖窗,伸出她年輕結實的手臂,朝後方比中指。
且看玲大學畢業數年仍闖不出一番事業,父親聘了幾名亞裔工讀生,讓女兒坐鎮櫃檯,指揮外場。一個週末夜,盤點完是日營業額,玲接到辛西亞簡訊:下班了?我在外頭等妳。玲探頭從櫃檯向對街望,熟悉的淡奶色二手日產車在路旁閃黃燈,辛西亞邊笑邊朝她大力摁喇叭。父親伸長狐疑的眼,抄起菜刀,從廚房快步走出。
「我語文課同學。」玲小心翼翼地對父親說。
父親往外瞅,見開車的是名女性,才沒太大反應。
「我外出,晚點直接回家。」玲趁父親還在猶豫之際,推了門出去。她知道父親心底是喜歡她多與法國本地人親近的。辛西亞的白皙膚色,對父親而言,就飽含整座歐洲的意義了。
穿越佳麗村大道,過鞏固爾地鐵站沒多久,辛西亞便催促她趕緊下車。辛西亞興奮地拉玲往協和廣場跑。滿坑滿谷的人,各式各樣,學生工人失業者,或不同地方移民。早春天氣微寒,入夜低溫更劇,大家群聚,身著各種顏色的羽絨外套,或站或坐。玲緊抓辛西亞的袖子深怕走失。好多人分別圍坐地上,前方擺塊木板或拉起自製布條,拿擴音器激昂地對群眾喊話。有人裹睡袋躺地,有人在廣場上搭建簡易帳棚。
「怎麼回事?」玲單手捂耳,朝前方的辛西亞喊。周圍鼓脹著一波波聲浪。
「la nuitdebout。這是我們的反叛,不眠之夜。」辛西亞對她叫,並舉起手機,打開periscope程式,用鏡頭反拍她與玲的臉,她伸中指擠鬼臉,不時切換鏡頭特寫身旁黑壓壓的人群。
「我們抗議勞動法改革。我們要讓整座巴黎,整座六角帝都覺醒。」辛西亞對鏡頭說,她的眼神有光。
辛西亞撐了一年兩期課程,不眠之夜沒多久,不知不覺,她被新來且會自製傳統糕點予同學共食的主婦們汰換了。某個陰濛濛的入冬早晨,辛西亞像失足跌落沉艦大廳的最底最底。手機訊息無人回應。
第三學期,玲獨自敲著鞋跟晃蕩中心底部,阿赫美德來遲,同她匆匆點頭打聲照面,玲拿著保溫壺,獨自坐進那間失溫暗室。雙複數變化,動詞變化,現在式過去式,年份月份星期一到星期天。玲勤奮學習,像在產道上緩慢爬行,從基本句滑過胚胎,著床,住進複詞子句。辛西亞與些反動不羈的回憶,被玲遺忘在失溫胎盤裡。她填塞自己,詞彙片語如養分,從躺,至爬,強迫自己進化為二腳遠行。
若遇餐廳排休,課後,玲用學生價買券,乘電梯至文化中心二三樓常態展廳。博物館區窗明几淨,一掃沉艦底部教學區的陰鬱氣息,展覽通道迴旋又迴旋,一處處玻璃間隔各式器皿,館藏按食衣住行專題分類,簑衣,棉布纏捲,裂紋馬賽克飾壁分門別類於各角。
玲最常駐留在平放檯面或騰空吊起展示的各樣古製手繪可蘭經前。細緻描框的花草蟲虫,完好包夾蛇行蜿蜒字體,材質使用金箔,堆疊再堆疊的金。研究中心落地窗透光,玲有時便久久溶解,漂浮在這近乎永恆的畫面裡。
「將榮耀獻給真主。 al hamdulillah。」玲隔著玻璃,邊用指尖爬沿可蘭經上的黑蛇字,邊低吟,那課堂上阿赫美德時常朗誦的句子。
當阿赫美德初次朗誦這句話時,玲記得她打了顫,像幼時手上爬滿的微小癢疹,久不褪去。
……(文長有刪節,以上為節錄)
少女伊斯蘭
塞納河畔,蘇利橋旁,一幢樓,恍如墜河之船。
玲正式消失前一年半, 她每週固定一天進入這沉艦腹部,大廳左邊轉角第一間房。 每個禮拜六,固定早上九點至十二點,不多不少剛好一節課時間,她在這冷灰而滿盈水氣的房間裡,學阿拉伯文。
一年半前,玲在家上網,下載了課程大綱,隨意揀個作業天,便乘地鐵從所居的佳麗村橫跨整座水域,來到五區,位於左岸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
她在櫃台領了報名表,填寫資料,並預繳半年學費。整套流程不過五分鐘。玲沿前院廣場走。陽光曬著她的無袖臂膀,同時在大樓鏤空花窗撒下立體剪...
作者序
島嶼回返
曾如是急欲逃離這座島,自青春期。出生於冬季的靈魂,彷彿註定與這經年燠熱,悶濕的亞熱帶之地,無所交融。討厭這城滿是灰濛的天,零碎參差的天際線,破建物不堪地批腸掛肚於街,與人們身上毫無個性的低彩度衣著。
每個身穿學生制服的下課空擋,在心裡默念全英流行排行榜或billboard Top 20當季火紅歌詞。密教咒語般虔誠。彷彿念著,哼著,方可日後解脫自己於橫跨數時區的彼岸。如是重複多年,過了二十歲,終於如願以償,居住在不同城市。我的口中嚼著或熱或冷的異國語言。
脫逃島嶼的自己,開心與否?無有答案。出走後,於異國,我刻意與同樣來自島嶼的人們鮮少交際。避開掛著豔紅燈籠飄著油煙味的中國城,亞洲飯館,超市,選擇在農曆年節出趟遠門,或讓自己酩酊暈吐在盥洗室的座桶邊。我眷戀如此決絕的斷裂,享受將自己砸進一段陌生的文化模式,再轉為海綿般飽滿吸收著,並將關於島嶼的記憶層層湮滅。
我與島的唯一連結,是母親。我們安然地每週固定時間通話,隔著遠洋交代近況。遙距讓我卸下心防,較過往,我與母親交心許多。
為了在異地營建新生,我以軀體,砸進男男女女或老或少的起居環境與心理空間。敞開自己,讓他們的故事,際遇與苦難在體內著床,滿盈。我以為相擁時,性交時,便是人與人最緊密與誠懇的時刻了。
卻還是寂寞。很是寂寞。
在所有異地朋友情人返鄉過節的耶誕新年假期,在因為一個詞語無法準確地用另一種語言翻譯的細瑣時候,在某些理念不合的爭吵。而我總在寂寞的巔峰,諷刺地意識到自己是如是地東方。
與精通度無關,語言結構形塑出的思考模式與邏輯,是根深蒂固而無法撼動的。
於我,所有事物的認知,皆處於某種漂浮狀態。中文,英文,法文,俄文以獨自的文化思考模式,各據一隅。詞與詞間,產生斷裂與歧義。法文的時間與天氣同字,俄文的不是天氣意謂狂風暴雨。對他人可能的單一概念,在我腦中,卻化作不同的形式,碎裂。
我意識到自己迴旋,對折,在詞語與詞語隙縫間穿梭的習慣,是異地情人朋友無從理解,甚至不屑一顧的。異地情人朋友們的東方,是薩伊德東方主義的近東:一座虛擬於符號世界裡,想像的,偏差的東方。那是我嫩滑的肌膚,我的黑髮,我的深棕色瞳仁所指涉的所有,而不是個別性的我。
寂寞於是在血裡結了冰。選擇不再談心,純粹肉體等值交換,我還是會用他們的語言聽著他們的故事。那是我意識自己仍然存在的微薄時刻。
寂寞的盡頭,是在重病昏迷後近兩個月,發現自己驚醒於異地加護病房。
全身插滿細密管線,體重直墜至四十三公斤。許是報應?蓄意逃離島嶼的我,最終,在異地賴以維生並乘載過多情感記憶的肉體,依樣逃離。逃離我的我,與被逃離的我,重疊成,躺在加護病房無法動彈的我,與氣切插管無法再訴說任何言語的我。
還好,身旁站著母親,即時自島嶼趕來的母親。她細心照料直至我出院回異地公寓療養。
我想回家。我對母親說。
無法再忍受更多的寂寞與來自他人的誤解。我想說著島嶼的語言,交際著擁有相同思考路徑的夥伴。
回返島嶼的休養期,無有工作,我參加寫作課。我想,我必須習慣以島嶼的語言訴說自身。
女作家上課地點,是公園裡一棟作為受害者紀念館的一樓教室。每個週末早晨,伴隨電腦投影片的切換,坐在淺藍色課椅上,不時可感應從地底呼嘯而過,傳自捷運的輕微晃動,與隆隆聲。我卻感覺更似來自那群受政治迫害而亡的靈,他們紛而龐大的奔竄,與哀嚎。
從最熟悉的事物書寫。女作家說。
時光於是重疊,混淆。地底再度有感晃動,只是呼嘯而過的,是莫斯科宮廷風格環狀地鐵,是巴黎充滿熱烘烘排泄物味道的車廂,是東京JR。奔竄哀嚎的隊伍,陸續加入了巴黎克里奇門站警局辦公室前整排尋求政治闢護的難民,莫斯科地區市場小販飽受歧視的中亞男女,與被消失的亞洲學生們。
常棄島嶼而不顧的我,發現,在創作初期竟無法以第一人稱視角出發,無法以島嶼與其都市為題材。最初作品,皆源自異地生活點滴。
好像外國小說。母親與女作家皆如是評論。
我想找回自己在島嶼的足跡,於是,開始了為期兩年的書寫,那是長長的記憶與情感折返,必須由最遠卻也最熟悉的部分,一步步踏入最近卻也最陌生的領地,那是我的島,與我最想逃避的,來自東方的我的意識主體。
參仿薩伊德東方主義,我敘述,勾勒著西方主義。那是一套將東方人們次等化,被邊緣化,被浪漫主義化的,來在西方世界的虛擬誘因與意識型態工具。中產階級,法語-isme結尾的各式主義與消費文化,描繪政治霸權與經濟干預的所有符指。
史畢娃克曾提問:底層人們有真實發言的機會嗎?
我想那或許來自練習。解構練習與操作既有的刻板印象。解構西方,解構所有權力體系甚至親情,友情,愛情,解構自身。拆解的過程勢必痛苦。若異地居旅經驗對我有任何深遠影響,那應是慣以用最冷峻的眼,最寫實主義的手法,直切必須摘除的病處與傷。
暴力與殘忍作為手段,卻只為更新。
更新成全然的自己,全然而純淨的意識主體。
並榮耀地宣布,我來自島嶼。台北,台灣。
僅將此書獻給我的母親,與作為群體,擁有柔軟內裡卻裹覆層層疤痕的人們。
謝謝袁瓊瓊老師,阿盛老師的提點。一路承蒙《人間副刊》美杏姐(與已轉職的祖胤哥),香港《字花》主編關天林先生、《聯副》、《文訊》、《幼獅文藝》、《聯合文學》諸君關照。
感謝時報出版社思潮線總編胡金倫先生。若無地表最強主編珊珊,此書或將沉寂甚久,我心竄湧的感激之情難以言表。最後同封面設計朱疋,及眾推薦者致敬。
寫於2019,10,臺北
修稿於2021,6,疫情中的臺北
島嶼回返
曾如是急欲逃離這座島,自青春期。出生於冬季的靈魂,彷彿註定與這經年燠熱,悶濕的亞熱帶之地,無所交融。討厭這城滿是灰濛的天,零碎參差的天際線,破建物不堪地批腸掛肚於街,與人們身上毫無個性的低彩度衣著。
每個身穿學生制服的下課空擋,在心裡默念全英流行排行榜或billboard Top 20當季火紅歌詞。密教咒語般虔誠。彷彿念著,哼著,方可日後解脫自己於橫跨數時區的彼岸。如是重複多年,過了二十歲,終於如願以償,居住在不同城市。我的口中嚼著或熱或冷的異國語言。
脫逃島嶼的自己,開心與否?無有答案。出走後,於異...
目錄
〔自序〕島嶼回返
iels-mêmes-伊們
陳熹
Leïla
少女伊斯蘭
象人與虛無者
la frontière-邊界
婊子,十三
intra-muros-我城
情慾齊克果
次女子殘害體系
碎裂,拼貼,編織
〔自序〕島嶼回返
iels-mêmes-伊們
陳熹
Leïla
少女伊斯蘭
象人與虛無者
la frontière-邊界
婊子,十三
intra-muros-我城
情慾齊克果
次女子殘害體系
碎裂,拼貼,編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