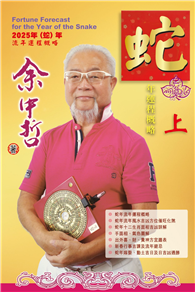【限制級】未滿18歲之讀者請勿閱覽
「酒鬼薔薇聖斗事件」完整始末
前少年A的生命筆記
臺大法律系教授 李茂生 導讀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鄧煌發 序文推薦
馬里蘭大學犯罪學博士 楊曙銘 序文推薦
邪惡是與生俱來的嗎?
如果不是,那麼少年A曾經經歷了什麼?
這本由少年A親筆寫下的自傳裡有最直接的解答。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我,從此不再是我。
那是我從光明世界被永遠放逐的那一天。
所有原本生活中,尋常無奇的一件件零瑣小事忽然間都蒙上了一層莫名象徵的那一天。
「少年A」──成了我的代名詞。
我不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我成為一個無機的「符號」。一個被大多數人當成「少年犯罪」的代表符號,一個跟大家住在不同世界裡、沒有一絲一毫人類情感,古怪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胎」符號。
本書是犯下日本神戶兒童連續殺傷事件(或稱「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的兇手少年A的自傳,可分為兩部。
少年A在書中的第一部陳述自己如何成為「怪物」的過程,以及自己心中對於犯下這樣的罪行有何想法;第二部則描寫結束感化教育之後,他是如何生活並試圖融入社會之中。
我不知道到底求過了多少次,希望時光能夠重來。還沒有犯下罪行前的孩提時代是那麼地溫馨令人懷念。──前少年A
少年A自傳《絕歌》雙書評
1997年發生在日本的「酒鬼薔微聖斗事件」,因手段兇殘駭人且兇手年僅14歲,強烈衝擊社會。多年後,這名「少年A」出版自傳,再度引發輿論譁然。而台灣近年因數起隨機殺人事件,相關現象與制度亦屢受討論。為此,開卷特邀長期關注並參與此議題的精神科醫師與新聞工作者,針對《絕歌》撰評,各依所見所思,提出更深層的生命之問。
走在危機四伏的荊棘路上
⊙胡慕情(新聞工作者)
為什麼讀?要怎麼讀?翻開《絕歌》前,每個讀者可能都必須自問這兩個問題。一如記者報導書寫公共議題時,都必須經過「為什麼寫?」、「要怎麼寫?」的曲折思考。確立框架,有助於觀看距離的形成——區隔,卻不禁絕他者與自我,讓社會學的想像浮現。
《絕歌》是日本駭人聽聞的酒鬼薔薇聖斗事件當事人的自傳。1997年,年僅14歲的少年A,在日本兵庫縣神戶市須磨區犯下連續殺害小學生案件,造成2人死亡、3人重傷,其中一名小學男生的頭顱被割下掛在學校門口,並附上一封挑釁警方的犯罪聲明信件。少年A在事發18年後寫出此書,除自剖犯罪動機與歷程,也描述更生人重返社會的困難,引發爭議。
少年A對事件的分析縝密而富邏輯,沒有學理論述,卻不乏知識痕跡。這是少年A有意識地對事件「再詮釋」。我們或可抨擊少年A藉此合理化自身犯行,如書中提及沙林毒氣等事件形塑社會疏離氛圍;以及少年A精細描述性、暴力及精神疾患的交織如何影響個人。但若將上述詮釋視為少年A對自身犯行的「理解」,書裡呈現的歸因,其實提供我們探索人性混沌,乃至於如何補強社會網絡的線索。
記者工作,需探看苦厄,這才明白心理學第一堂課教授所說「健康很難」意味什麼:人一降生就開始缺損、必須修飾自我符合社會期待,稍有不慎就會離心,所有人都在路上,直至死亡。
暫時按捺常人對暴力與變態的反感來閱讀《絕歌》,會發現「活」是文中核心——「用我自己這雙手,孕育了死。」「所謂活著,就是感受痛苦。所謂給予痛苦,就是觸摸生命。」在讓人作嘔的犯行背後,少年A所描繪與戳刺的,正是每個人都須回應的,輪迴不休、充滿悖論的哲學命題。
而若深探隨機殺人事件背景,更會發現,階級與際遇會影響人的理性選擇能力與可能性。少年A事件雖不同於自小即成童工、受虐、家庭疏離的隨機殺人個案,但他們卻都共同探問:為什麼要活?人為什麼存在、如何存在?
上述問題,向來是危機四伏的荊棘小徑。穿越的方式總是歧異,因為每個人對成長過程所獲支持的詮釋不同。詮釋差異變幻出各種「活」的姿態,使世界不至孤冷扁平。不幸的是,總有人逸出想像常軌,製造逼近絕望的恐懼—人性若有任何高貴,在於願意透過理性與感性抵抗絕望鄉的來臨,而隨機殺人,正是對這高貴人性最大的拷問。
人以及想像的常軌,既是讀者以受害者家屬以外的身分閱讀《絕歌》時的錨定,同時也是我們觀看近年台灣幾起重大隨機殺人命案與思考文明微光的必要刺點。閱讀他者不在於探索歷史事實、淬取犯罪者悔意與追討正義—無論是當事人的自白或旁觀者的「紀實」,在攸關人性的議題裡,真相恐怕是永難抵達的幻境。文明進展裡,殘酷從來難以遏止,問題在於,世界或真有難解、無解的惡之深井,但「我」始終在「我們」之中,人從誕生那一刻就註定與社會鏈結,若對生命戒慎珍惜,思考與我們光譜遙遠的人為何以「死」叩問「活」,是不能迴避的一門課。
人人心中都潛藏著一點少年A?
⊙楊添圍(精神科醫師、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
我們應該怎麼去注視這樣的加害人?又該如何面對一位「前」殺人犯?如果,我們連完整讀完《絕歌》都如此困難。
尤其正值當今好幾位殺人犯犯下難以理解與原諒的行為,卻未獲判死刑的社會氛圍下,在這時候,一般大眾怎可能用道德和人性高度,用寬恕、包容去面對諸多的怨念和恨意呢?
這些,都讓所有試著去面對與理解少年A的心情,顯得更加困難而矛盾。這樣的人有必要理解嗎?他那是禽獸的行為,不是人會做的,何必去理解呢?
但是,他有過平常的童年啊,至少到小學四、五年級為止。他有愛他的父母,和兄弟的關係不錯,他在學校也有朋友,進入醫療少年輔育院後,還讀了村上春樹、杜斯妥也夫斯基。他沒有被虐待、被性侵害的經歷。案發前,他是一位有廣泛性發展障礙者的玩伴—只是這次,他把玩伴變成了被害人。
他不像當時媒體所報導的缺乏關愛。但是,他是個性變態、性施虐者,也是個虐貓狂徒,他喜歡看《沉默的羔羊》以及美國連續殺人犯的電影和故事,他不可能是一般正常人啊。
既然不是正常人,何需理解?如果人可以篩檢、可以預測,只要找對工具,透過篩檢站,設立舉報人,把滋擾分子、壞分子找出來,然後社會就能回歸平靜,人們安居樂業,故事就此完結。我們又何必去理解「那些人」呢?
美國司法精神醫學專家Robert Simon在《壞人所為,好人所夢》(Bad Men Do What Good Men Dream)一書裡不媚俗地直言:我們常認為虐殺和惡行與正常人無關,這種看法忽略了一個基本假設:我們都是人類,有能力達成許多層次的行為,有些是好的,有些我們相當清楚,是壞的。雖然大多數人可以遏制自身施虐、破壞的黑暗面,但是這一黑暗面卻日以繼夜地以不同程度出現與運作著。早期人類以為,月缺時,部分月亮也消失。今天我們知道,月亮的黑闇部分雖不可見,但依舊存在。
漢娜‧鄂蘭提出「邪惡的平庸性」,最引人寒顫的是,那是存在於你我之間的邪惡。當面對權勢與政治時,我們會如何表現?又會如何對待比自己弱勢的人?當言論自由與民主選舉稀鬆平常如空氣時,我們如何想像在威權統治下勇敢而誠實的生活?當飽食無虞時,又如何想像人們會因飢寒而驟起盜心?正如心理學者菲立普‧金巴多在《路西法效應》(商周)中所揭示,任何一位良善正直的公民要成為惡魔,何其容易。
所謂試著理解那些「惡人」,應該不是去「原諒」他們,也不是在被害人身上撒鹽,更不代表主張廢除死刑。而是,勉強自己去注視在每個人心中的黑暗面。或許終有一天,我們可以約略領悟到,原來不只是「他們這些人」會行差走錯,會觸犯法網。
理解是如此艱難,讓我們不忍注視,卻無法忽略。或許,在這樣的檢視之下,我們終於可以對自己多些了解,就那麼一點點。
原載:中國時報開卷版,2016-05-14
作者簡介:
前少年A
一九八二年生於日本神戶市。在一九九七年二月至五月間,犯下著名的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並化名為「酒鬼薔薇聖斗」,在當年六月二十八日遭到逮捕。因是未成年犯,故在日本法律的文件上被稱為「少年A」。於二○○四年三月結束感化教育,二○一五年出版自傳《絕歌》,在日本社會引起極大的爭議。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李茂生教授 專文導讀:我覺得不僅是日本的民眾,包含與此事件毫無關連的臺灣讀者,應該有個正面思考的態度來接觸這本書,並理解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雖然無法確切地定義何謂正常的人際關係,但是必須理解當一個人將自己鎖進別人的眼光會直接穿透肉體,且被絕對地忽視的純粹透明的世界時,是件何等悲哀的事情,任何想要把自己的透明性解消掉,同時回歸社會實體人際關係的努力,是多麼地值得我們容忍與贊同。
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鄧煌發教授 序文推薦:以過去發生的案例,藉諸文學之筆,從這本「絕歌: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透過加害人「少年A」描述自己的細微生活點滴當中,能夠讓即將要結婚,或即將有孩子,甚或已為人之父母角色的人,都能從中體悟到適度的愛、教育、家庭對一個健全人格養成的重要性。看完這本書之後,我改變了過去反對出版類似此書的立場,因為這本書符合了我長年呼籲的一句口號:犯罪預防,大家一起來!
馬里蘭大學犯罪學博士 楊曙銘 序文推薦:這世界上可能有許多潛在的「少年A」但不為人知,在預知犯罪記事之前,我們有沒有可能先從家庭方面著手,讓孩子有機會面對多元的人際刺激,進而發現這些哀鳴的靈魂,或許能減少一位少年A、少聽一次絕歌呢?
名人推薦: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李茂生教授 專文導讀:我覺得不僅是日本的民眾,包含與此事件毫無關連的臺灣讀者,應該有個正面思考的態度來接觸這本書,並理解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雖然無法確切地定義何謂正常的人際關係,但是必須理解當一個人將自己鎖進別人的眼光會直接穿透肉體,且被絕對地忽視的純粹透明的世界時,是件何等悲哀的事情,任何想要把自己的透明性解消掉,同時回歸社會實體人際關係的努力,是多麼地值得我們容忍與贊同。
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鄧煌發教授 序文推薦:以過去發生的案例,藉諸文學之筆,從這本「...
章節試閱
第一部
失去名字那一天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我,從此不再是我。
那是我從光明世界被永遠放逐的那一天。
所有原本生活中,尋常無奇的一件件瑣碎小事忽然間都蒙上了一層莫名象徵的那一天。
「少年A」──成了我的代名詞。
我不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我成為一個無機的「符號」。一個被大多數人當成「少年犯罪」的代表符號,一個跟大家住在不同世界裡、沒有一絲一毫人類情感,古怪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胎」符號。
不管好或壞,我沒有任何地方比別人突出。我從來沒想到過自己會變成什麼東西的象徵。
請回想一下您國中時的同班同學,您一開始會想起誰?是不是那個成績優秀、運動萬能而且長相也很受老天爺眷顧的班長?
第二個會想起誰?是那個天生好笑、說話風趣總是帶動現場氣氛的活寶?
第三個呢?是那個染了頭髮、叼根菸、一天到晚鬧事,有時好像咬到嘴脣一樣露出一臉俏皮笑容的同學吧?
大家都到齊了。好了,現在請您再把眼睛轉向教室的角落去。看,那裡不是還有一個人?一個您連名字跟長相都忘了的人。您根本也忘了曾經跟他同班過吧?
不會念書、不會運動,也不太能跟別人好好講上幾句話。走進教室時沒有人會看他,在走廊上跟他擦撞時沒有人會回頭。沒有人會叫他的名字。他在或不在都沒有人會在乎。那個人就是我。
這樣一個無論在任何學校、任何班級裡一定都會出現幾個的屬於校園階層裡頭最底層的「無臉人」,從那一天起,成了少年犯罪的「象徵」。
清晨,我感覺有人搖晃我的肩膀,睜開了眼睛。惺忪的睡眼裡,映入了父親的臉。
「警察來了。說什麼有事情要問你……」
父親說。他看起來好像還沒有搞清楚發生什麼事,一臉疑惑。
我什麼話也沒說,默默把枕頭旁堆成要塞一樣的小狗、鴨子、哥吉拉、鱷魚之類的玩偶推倒,從棉被裡爬出來。慢吞吞穿上牛仔褲跟棉質運動上衣後,從二樓走下一樓。玄關裡站了兩位刑警。一個禿頭有啤酒肚,一個一眼看來就是個柔道練家子,耳殼變形、體格壯碩。
「我們有事想問你,跟我們來一趟吧?」
禿頭的刑警這麼說。他臉上露出和善的笑容,眼神卻像獵人瞄準獵物一樣凌厲地揪著我。我默默點了頭。
走出家門時,我沒有看父親的臉。母親當時在後頭,不在旁邊。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當時能看一眼父親的臉就好了。叫母親來,也看一下她的臉。我想用這雙眼睛牢牢記住,他們把我當成不成才的「自己的孩子」看的最後瞬間,不是「殺人犯」也不是「怪物」。如果當時我能把亂長的頭髮撥一撥,抬頭看看天空就好了,因為在那之後,我好幾年都待在不見天空的房間裡……
可是我卻只是一如往常地低著頭。我不想看任何人,也不想被任何人看。
就這樣,我從家人面前、從光明的世界消失了。
之後,我的時間便靜止在十四歲。
抵達成立了土師淳君殺害、棄屍事件搜查本部的須磨警署後,先進行了簡單的搜身,接著便把我帶去偵訊室。那裡已經有兩位刑警等著。一個大塊頭的刑警大開雙腿,站在室內正中央,雙手插在口袋裡。一頭捲毛夾雜著白髮,鷹勾鼻,眼神像猛禽般銳利,稍黑的膚色透露出他年輕時曾在許多現場衝鋒陷陣過。
另一個站在旁邊的刑警頭髮抹了髮油,側分。眼鏡後有雙瞇瞇眼,穿件邋遢的襯衫。
啪嗒一聲,偵訊室的門闔上。
「坐那裡!」
刑警指著椅子。我一坐下來,他便隔子桌子坐在我對面。另一位刑警站在門口。桌上擺著厚厚一疊檔案。
刑警直勾勾地盯著我的雙眼質問:
「你知道淳君的事吧?」
「我在電視上看到過。」
「三月時不是還有另一個小女生被打死嗎?那是你幹的吧?」
「什麼?」
我故意裝傻。
「同一天不是也有個小孩子被刺傷嗎?我們給她看了你照片,她說就是你。你忘啦?」
「我不知道耶。」
他一邊問,一邊探身往前盯著我的眼睛。
「真罕見哪~難得有人說謊,臉上居然都看不出來。難怪大家都被你騙了。淳君的事要怎麼說?有人說看見你跟他走在一起唷。」
「淳君是我弟的朋友。有時候會來我家玩。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兩個人單獨玩過。看錯了吧?」
就這樣問問答答之間,我心底開始受不了。
──好想馬上認罪。最好趕快把我送上死刑臺,結束這一切。
那時候的我,已經不能控制我自己了,所以只能寄望有誰能來阻止我。
「啊──我累了耶,有沒有什麼物理證據啊?」
聽我這麼一說,刑警馬上發飆。
「你這個小孩子不要隨便看不起警察!我們沒有什麼證據還可以把你拉到這邊來啊!」
他怒吼著兩手按著桌面猛然站起,拿起放在一旁的厚檔案夾在我面前拍打。打開檔案,他一邊啪啪地翻頁給我看,一邊逼問。
「這是你在學校寫的所有作文!我們找專家鑑定過筆跡了,跟寄到神戶新聞的聲明文百分之百出自同一個人之手!怎麼樣,該認了吧!」
眼前的確是一堆我從前寫的作文跟送到神戶新聞社的犯罪聲明文的彩色影本。
忽然被攤出了小學時寫的作文跟犯罪聲明文,宣稱「筆跡鑑定一致」,實在很難不相信。
──終於被找到證據了。結束了。終於可以結束了。
我心裡這麼想,可是並沒有馬上認罪,反而還使盡全身力量惡狠狠瞪著那個刑警。我心裡一邊想被逼到極點,一邊也想頑抗到最後一秒鐘。因為除了那以外,我已經沒有任何要拚命的事了。
後來那刑警被叫去家裁召開的審判時,提到他當時看見我的眼神心裡一寒。我雖然不知道自己當時瞪他的眼神到底怎麼樣,不過大概很恐怖。
我一邊瞪著他,腦中忽然閃過了母親的臉。
如果就這樣一直不講話,他們最後會放我回家嗎?回家後,要怎麼跟母親解釋?又要對她說謊了,又要再騙她。她一定會完全相信我的話,一點也不懷疑吧。我就是受不了這樣。
就那樣瞪著那刑警好一會兒後,淚水忽然抑制不住地冒了出來。
──我怎麼能承認?我怎麼可以輸?
──我想認了。我想讓一切都結束了。
兩種完全相反的情緒從腳底緩緩襲上,像油跟水般彼此不容卻又強勁攪拌在一起,沿著膝蓋、腰、胸、肩一路往上,終於到達了下眼瞼溢了出來。
這麼一來就結束了。已經不會再有人受傷害了。
「是我幹的。」
我開始自白。
第一部
失去名字那一天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我,從此不再是我。
那是我從光明世界被永遠放逐的那一天。
所有原本生活中,尋常無奇的一件件瑣碎小事忽然間都蒙上了一層莫名象徵的那一天。
「少年A」──成了我的代名詞。
我不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我成為一個無機的「符號」。一個被大多數人當成「少年犯罪」的代表符號,一個跟大家住在不同世界裡、沒有一絲一毫人類情感,古怪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胎」符號。
不管好或壞,我沒有任何地方比別人突出。我從來沒想到過自己會變成什麼東西的象徵。
請回想一下您國中時的...
推薦序
導讀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李茂生教授
一九九七年五月,日本神戶市發生了令人咋舌的驚悚事件,有人將一位小學男童被切下並清理過的頭顱置於某中學的校門口,面向街道,頭顱的口中還塞了一張挑釁的字條。起初,警方還認為是患有精神疾病的成年人所為,不過經過抽絲剝繭的偵查後,發現這是起連續的殺傷國小幼童的事件,而犯人竟然是位十四歲的國中生。事件的經過如下:
一九九七年二月到五月間,日本神戶市須磨區發生了多起小學生遭刺傷以及殺害的事件(二死三傷)。其中一名女童「彩花」在校園廁所內被以鐵鎚攻擊顏面,受重傷,並於醫院內過世。另一名則是兇手所熟識的男童「淳」,他被帶到住家附近的山丘勒斃後,頭被割下來。數日後行為人寫了聲明,並將聲明置入署名為「酒鬼薔薇聖斗」的信封內,塞在被害男童頭顱的口中,本想將之懸掛於附近的國中校門口,因為掛不上去,只好置於門口。這個挑戰書上寫著:「遊戲就要開始了。各位愚蠢的警察,嘗試著來阻止我吧。就殺人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愉快。好想看到人的死亡。用死亡來制裁骯髒的蔬菜吧,用流血來審判我經年累月的怨憤吧。——SHOOLL KILL學校殺死之酒鬼薔薇。」用蔬菜來比喻人命,彰顯出對生命的蔑視,而錯誤的英文拼字也透露出犯人所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內文的署名是「學校殺死の酒鬼薔薇」這個不成日文的日文,與其說是學校殺手,倒不如說,從日文將動詞放在最後的文法而言,這應該是殺死學校的酒鬼薔薇。
其後,因為媒體將酒鬼薔薇(さかきばら)誤讀為鬼薔薇(おにばら),所以犯人又向神戶新聞社寄出挑釁的信件。信中除了表達對媒體讀錯其名字的憤怒外,另外也批評了創造出他這種透明人的義務教育,他期待透過驚悚的殺人事件,至少在人們的幻想中可以成為實際存在的人。
同年六月少年A被捕,在少年觀護所經過精神鑑定後,認定其有性虐待傾向(sadism),且有人際溝通上的障礙,據此裁定將其移送到關東少年醫療輔育院接受治療,其後又將之移送到東北的中等少年輔育院(收容較年長少年犯罪者的輔育院),一直到二○○四年時,才停止執行感化教育,在附保護管束的條件下,回歸現實的社會。少年A當時已經二十一歲。數個月後,保護管束亦被免除。二○○五年一月一日,「少年A」以實名或假名重生。然而,事情並不是這麼單純。
事件發生的當年年尾,被害人之一彩花的母親寫了一本書「彩花──謝謝妳給予的生命力量」,書中道盡一位喪女的母親,如何從絕望中再度振作的辛酸,引起讀者極大的回應。隔年十二月為了回應讀者,又出版了第二本書,感謝女兒繼續遞活存在無數人的心中。同年九月,另一被害者的父親也出版了一本書「淳」,雖然書中談到了兒子的成長過程,以及事件發生後的驚慌等,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談少年法中對於被害人家屬不公的規定。這三本書都成為暢銷書,讀者大都以正面的情緒,閱讀著這三本書。
然而,隔年,就在彩花的母親出版第二本書後不到半年,事件發生後兩年以來都沉默不語的少年A的父母親寫了一本「生下少年A──父母的悔恨手札」,書中詳細地記載了與少年A的生活以及事件前後少年A的情形。於書中並無法察覺到多少問題家庭的痕跡,反倒是呈現出一個正常且平凡家庭的氛圍。當時立即引發一陣恐慌,因為大家從來沒有想像過這類的家庭會教養出殺人惡魔,而且殺人的時候才十四歲。這本書出版後,至今暢銷五十萬冊,版稅七千萬日圓悉數捐給被害人家屬。
其後,雖然一些媒體還有在關注這個事件,但大體上而言,幾乎都已經沉寂。一直到事件發生十八年後,透過本書的出版,這種被壓抑下來的不滿與不安又再度攪翻了整個日本社會。此時,少年A已經三十三歲,不能再稱之為少年了。
本書初次印刷十萬冊,不久銷售一空,出版社立即加印了五萬冊。現在第三刷,共銷售了二十五萬冊。原先是另一家出版社找到少年A,並簽約書寫自傳,但是出版的預告才剛公布,就遭到各界的反對,不僅是被害人家屬,連該出版社所屬人氣作家也出面反對,並揚言如果出版則對出版社採取抵制態度。其後,又因出版社要求少年A必須以實名出版,且在書中應表達懺悔之意等事項,引發雙方間的爭執,進而合意解約,並轉由現在的出版社出版此書。
出書後數月,在日本媒體的不斷追索下,發現少年A在東京靠打零工過活,日本有名的雜誌《週刊文春》的記者並於東京某處拍下少年A的影像。據報導,他發現記者在拍照時還出言恐嚇說,你的名字和臉我都記住了。這個報導引起社會譁然。除此之外,少年A也設置了他自己的官網(http://www.sonzainotaerarenaitomeisa.biz/),刊登了書籍訊息與一些隨筆、圖片,被認為是想替《絕歌》一書打廣告。不久,日本的另一個雜誌《週刊Post》刊登訊息,除揭露其真名外,還刊載了其犯案當年的大頭照。
至此,當年案發時尚且存在的另一種聲音,亦即認為升學壓力、學歷菁英主義、教養方式、媒體渲染惡習等是造成悲劇的主因之見解,幾乎都已經銷聲匿跡。整個日本社會罵聲一遍,但是奇妙的是縱然許多人一開始就拒絕購買此書,卻有更多人購買閱讀後,再開罵。書籍銷售長紅,少年A版稅收入益豐。未得受害人家屬的同意,就擅自消費被害人及其家屬,而且狂賺版稅估計一千五百萬至兩千萬日圓,至今仍沒有將這筆錢交給被害人家屬當成賠償金或予以信託(少年A背負了上億日圓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這些都受到眾多的批判。為抵制此事,媒體開始報導少年A違法擁有兩本護照,想利用版稅逃往國外等無法證實的事情,但此又刺激了買氣。
到底本書有多大的魅力?其中的論述是否消費了被害人以及其家屬?排除掉激情,本書到底替我們帶來怎樣的訊息?這些都是讀者除了獵奇以外,必須去深思的事情。
本書共分成兩部分,第一部描述了少年A的時代,重點置於其成長、犯行至審判的過程。姑不論此一部分是否為自我脫罪的藉口,也不去讚嘆其文筆的優美,只要不被殺貓的那一段敘述弄到噁心而無法繼續閱讀,讀者應該可以察覺少年A心中的矛盾與衝突。將自己關在一個小領域內,而這個領域本來是個不讓別人侵犯也不侵犯別人的聖域,然而突然間在祖母去世時,奇妙地變成性與死亡的連結,少年A開始步入沉溺於死與性欲的扭曲心理境界。或許是因為效果遞減的關係,少年A從殺害動物發展到殺人,這點尚能夠理解。然而針對被害人中唯一的男性學童的案件時,則應該不是這麼「單純」。
除了死亡與性欲的扭曲連結外,熟識的男童或許因為是發育遲緩兒,清純到不受世俗的任何汙染,所以才會被少年A當成絕對不允許他人侵犯的聖域。但是同時少年A又在聖域中看到了醜惡的自我,所以他才會以殺害男童來排除自我毀滅聖域的可能性,並且在男童頭顱的眼睛部位,用刀割出X字型的傷痕。這不外是在男童的眼睛的反射中,少年A看到了自我的邪惡,並想以否定的方式否定自我的宣示。聖域代表了不得侵犯的意涵,而侵犯聖域的竟然就是自己。殺死男童,並對其頭顱自慰,這顯然是個性倒錯的顯現,但是除此之外,難道沒有其他的意涵?殺死小女孩與殺死小男孩之間有所差異。雖然少年A仍舊對於殺害男童的事情不願意多說,但是想把映照在小男孩眼中邪惡的自己殺掉的描述,應該不是一個單純的辯解,而是另有其他的意涵。否則,為何少年A在本書中,幾乎沒有就另一女童彩花殺害事件多做論述的理由,即令人費解。
如果能夠理解到整個事件中,男童淳君所代表的意義,或許就更加能夠理解本書後半部的意義。雖然許多日本的讀者都認為本書的後半段是個非常自私的表述,充滿著自我感覺良好的期待,但是去除掉先入為主的想像,或許更能理解去除掉少年A的標籤,以另一個身分重返社會時,聖域的解除與人際關係重建間的相當關係。從一個透明人,重新創造人際關係間的實體的努力,已經在本書的後半部充分地表達出來了。而對於本書出版後本人不斷挑釁社會大眾的舉動,也應該可以從捍衛實體人際關係的角度來加以審視。
日本著名的精神科醫師片田珠美(《無差別殺人的精神分析》這本暢銷書的作者)說少年A是個典型的性倒錯患者(性虐待狂),這類的病患有時會因為性幻想而做出殺人的行為,如果不想要讓奇妙的性幻想化為實際上的行動,那麼繼續不斷地書寫,把心中的特異性幻想用文字發洩出來,或許就是讓他們不把幻想化為行動的良方。可惜的是,在一陣騷動與謾罵後,少年A又開始銷聲匿跡。
我覺得不僅是日本的民眾,包含與此事件毫無關連的臺灣讀者,應該有個正面思考的態度來接觸這本書,並理解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雖然無法確切地定義何謂正常的人際關係,但是必須理解當一個人將自己鎖進別人的眼光會直接穿透肉體,且被絕對地忽視的純粹透明的世界時,是件何等悲哀的事情?任何想要把自己的透明性解消掉,同時回歸社會實體人際關係的努力,是多麼地值得我們容忍與贊同。
《絕歌》這個書名到底傳達出怎樣的訊息;絕情之歌、絕望之歌?還是與過去斷絕之歌?這些都留待讀者自行解讀。
推薦序 從日本的「少年A」到臺灣的「少年B」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鄧煌發教授
上完課,一如往常踏進研究室;桌上的手機夾著震動聲響,驚擾小憩的欲求。回應後,原來是某一暢銷大報的知名社會記者來電詢問發生在南臺灣鄉間一件虐殺幼狗事件的行為人的心態,我當下為這不知是誰(少年B)的行為動機嚇出一身冷汗,驚呼:受害者還好不是人,但又有何異呢?
純樸的雲林鄉間,一隻母狗正細心地舔舐被斷頭的幼狗頸部滲出的血,從牠那無奈的低吟聲,更確定倒臥的是牠心愛的幼子……;昨天牠們還一起結伴到隔壁村莊冒險。記者說:「有一天,『少年B』經過牠們家附近,因懷恨被母狗追,遂計誘擄獲幼狗,將之殺害後,故意丟置在母狗身旁…。為什麼會有這樣心狠的人,他的心態到底是什麼?」
當時,心中閃過一九九七年日本「酒鬼薔薇聖鬥事件」的主角,那背負日本保守教條要求,以及滿載著父母過度期望的「少年A」(東真一郎,十四歲),其幼時不也是經常以虐殺動物的方式來發洩心中的鬱悶;稍長時,卻演變成以虐殺學童為快樂泉源的「惡魔」嗎?臺灣的「少年B」行徑,難道是日本「少年A」的翻版?
站在犯罪學者的立場,我並不贊成臺灣出版界一味仿效日本出版「絕歌」一書。為什麼?因為類此詳實地描述加害人內心,以及鉅細靡遺地講述殺人的伎倆的書,將可能提供部分人以極端行為(例如隨機殺人),作為不滿臺灣的對立、矛盾、衝突、憤恨等社會氛圍的抒壓管道。這些現象一般稱為犯罪學習、犯罪感染,我怕的就是這個。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發生在內湖的隨機殺人事件,一位天真無邪的四歲女童,在光天化日、母親陪伴在旁的極度平常的情況下,竟遭一名三十三歲的王姓嫌犯斷頭橫死街頭。經初步檢警犯罪偵查資料指出,王嫌具有精神極度不穩定的跡象,類似「少年A」的生活細瑣事件,也陸續出現。臺灣經歷了九件隨機殺人的肆虐之後,「重刑化」的聲潮不斷。個人以為,民眾過度依賴刑事司法的力道,並無益於改善現狀,因為他們是極少數「不知死」、「一味求死」、「享受死」等異於常人的「無理性」之人,「死刑」只是他們尋求「解脫」的方法之一。
因此,以過去發生的案例,藉諸文學之筆,從這本「絕歌: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透過加害人「少年A」描述自己的細微生活點滴當中,能夠讓即將要結婚,或即將有孩子,甚或已為人之父母角色的人,都能從中體悟到適度的愛、教育、家庭對一個健全人格養成的重要性。看完這本書之後,我改變了過去反對出版類似此書的立場,因為這本書符合了我長年呼籲的一句口號:「犯罪預防,大家一起來!」
鄧煌發 謹誌於桃園龜山犯罪預防工作室
二○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推薦序 為了不要再有少年A的絕歌
馬里蘭大學犯罪學博士 楊曙銘
十多年前,為了進行論文研究,我訪談了十六個少年殺人犯,在一次次的訪談中,探索事件發生時他們的心理狀況,以及家庭情形。絕大多數的少年是在打群架時犯下殺人罪,在同儕壓力下,集體鬥毆,若非警察找上門來,他們渾然不知自己已犯下殺人罪行。然而,在我訪談過的個案中,有很少數的少年,他們具有一些不同的特質;他們並非來自破碎家庭、也不屬於低學業成就、或是生長在弱勢家庭這些常被引用的高風險因子,而且他們在犯下殺人重罪時仍有自我意識,雖然多半是扭曲的。
這個差別絕對不是簡單的「邪惡」兩字可以概括。有更深層的因素,讓這些少年與周遭環境之間存在一層不容易交流的無形薄膜;也許,是同樣的原因,讓這些青少年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
從那時起,我便時時刻刻思索造成這種差異性的主要原因。每次聽到社會上有駭人聽聞的殺人案件,在哀傷之餘,我的思緒又會回到當初那些少年告訴我的生命故事中,想要找出一個解答,一個可以有效的防範類似事件發生的對策。
然而,這樣的事件仍然持續發生。閱聽媒體的強力放送,對細節多所渲染,造成人人自危;社會氛圍多半一面倒的支持「治亂世用重典」,相信極刑可以防止這種事情再度發生。
我抱著尋找答案的心情來讀《絕歌》,書中少年A說到被逮捕後的心情:「那時候的我,面對『生』毋寧比『死』更讓我畏懼千百倍。」
看著少年A的自白,對照著接觸過的少年殺人犯,我更確定極刑對這樣的犯人,沒有嚇阻的功效,也許反而可能是他們渴求的精神鴉片。
精神醫學專家Dr. Stuart Brown在研究許多犯下重大罪行的連續殺人犯時發現,這些殺人犯雖然家庭背景與社經地位不一,但是在幼年時期,都沒有機會與同儕一起「遊戲」,有些是因為家暴、有些是父母保護過度、家教甚嚴,因此被限制在家中不得外出。布朗博士強調,這些缺乏遊戲經驗的孩子無法建立與其他社會個體有效的溝通方式,也未曾因在不具惡意的打鬧中受到傷害(或是讓對方受傷害)而發展出同理心;也因此,長大後他們與外界無法在情感方面有效溝通,長期面對無法被理解(自己也缺乏理解他人的能力)的孤獨感,並傾向於建構出自己的安全世界。當離開家庭進入社會化情境時(例如學校),情感面的不成熟造成人際互動的困難,久而久之,自己所建構的世界被外界的刺激衝擊,平衡終究會崩毀。此時,如果本身又擁有優越的智能以及良好的運動能力,所造成的後果會更具破壞性,例如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槍擊案件。
少年A的成長歷程也有類似之處,他的原生家庭看似完整,然而,幼年期間多半與溺愛他的外婆相處,這種予取予求的單向索討,並不能取代幼童所需的社交刺激,以及透過人際互動所得到的社會經驗。在人際關係疏離的現代社會中,直升機父母所拿走的也許不僅是孩子受傷冒險的機會,過度的保護可能反而造成孩子無法正確理解社會互動所需的有來有往,也讓孩子無法發展完整的同理心。
這世界上可能有許多潛在的「少年A」但不為人知,在預知犯罪記事之前,我們有沒有可能先從家庭方面著手,讓孩子有機會面對多元的人際刺激,進而發現這些哀鳴的靈魂,或許能減少一位少年A、少聽一次絕歌呢?
導讀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李茂生教授
一九九七年五月,日本神戶市發生了令人咋舌的驚悚事件,有人將一位小學男童被切下並清理過的頭顱置於某中學的校門口,面向街道,頭顱的口中還塞了一張挑釁的字條。起初,警方還認為是患有精神疾病的成年人所為,不過經過抽絲剝繭的偵查後,發現這是起連續的殺傷國小幼童的事件,而犯人竟然是位十四歲的國中生。事件的經過如下:
一九九七年二月到五月間,日本神戶市須磨區發生了多起小學生遭刺傷以及殺害的事件(二死三傷)。其中一名女童「彩花」在校園廁所內被以鐵鎚攻擊顏面,受重傷,並於醫院內...
目錄
導讀
推薦序 從日本的「少年A」到臺灣的「少年B」
推薦序 不要再有少年A的絕歌
第一部
失去名字那一天
夜泣
生存的希望
水池
各自的儀式
裂錨
原罪
斷絕
GOD LESS NIGHT
蒼白時代
父親之淚
新城的天使
精神狩獵者
咆哮
審判
第二部
重新站在天空下(二○○四年三月十日~四月初)
更生保護設施(二○○四年四月初~四月中)
鯨鯊先生與螳螂先生(二○○四年四月中~二○○四年五月中)
最後住處(二○○四年五月中~二○○五年一月)
踏上旅途(二○○五年一月~二○○五年八月)
新天地(二○○五年八月中~二○○七年十二月)
各地飄泊(二○○八年一月~二○○九年六月左右)
一隅之地(二○○九年九月~二○一二年十二月)
渺小的回答(二○一二年十二月~)
路(二○一五 春)
謹致被害者家屬
導讀
推薦序 從日本的「少年A」到臺灣的「少年B」
推薦序 不要再有少年A的絕歌
第一部
失去名字那一天
夜泣
生存的希望
水池
各自的儀式
裂錨
原罪
斷絕
GOD LESS NIGHT
蒼白時代
父親之淚
新城的天使
精神狩獵者
咆哮
審判
第二部
重新站在天空下(二○○四年三月十日~四月初)
更生保護設施(二○○四年四月初~四月中)
鯨鯊先生與螳螂先生(二○○四年四月中~二○○四年五月中)
最後住處(二○○四年五月中~二○○五年一月)
踏上旅途(二○○五年一月~二○○五年八月)
新天地(二○○五年八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