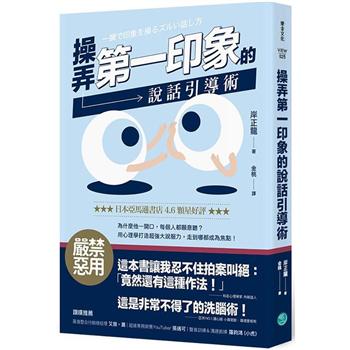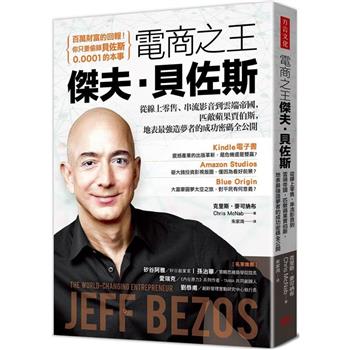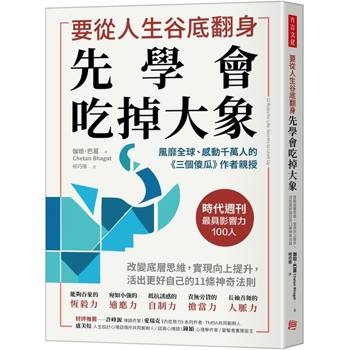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4 項符合
翻轉你的數學腦的圖書 |
 |
翻轉你的數學腦:數學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作者:斯蒂芬.布伊斯曼 / 譯者:胡守仁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0-1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52 |
數學 |
電子書 |
$ 252 |
數學史 |
$ 270 |
數學史 |
$ 270 |
Books |
$ 284 |
數學總論 |
$ 284 |
中文書 |
$ 284 |
Books |
$ 284 |
Books |
$ 284 |
數學總論 |
$ 284 |
Books |
$ 284 |
普及科學 |
$ 317 |
數學 |
$ 324 |
科學‧科普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翻轉你的數學腦
改變世界對數學思考方式的奇才,
不用公式、不教計算,
用生動的故事轉變你對數字與數學的思維方式。
正常的情況下,很多人都盡量逃避數學,即便我們都知道數學很重要。
數學究竟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微積分、圖論、統計學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大家又為什麼要在學校學那麼多公式,這答案卻沒有多少人知道。
斯蒂芬‧布伊斯曼在20歲獲得博士學位後,已成為最受歡迎的數學教育專家之一。他在本書中帶著讀者橫跨數千年,踏上環遊世界的旅程,探訪那些對數學有著全然不同概念的傳統社會、原始部落,讓大家知曉不同數學領域意想不到的起源,以及數學有什麼用。
布伊斯曼在幽默風趣的敘述中讓我們看到數學的重要性,並以簡單易懂的方式讓我們理解微積分如何應用在自動駕駛、自動溫控,還有圖論如何讓Google 地圖與Netflix越來越好用,以及大數據年代,統計學如何動搖我們的認知……幫助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對數學能有更好的掌握,並深刻感受對數學有更好的理解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這個世界。
作者簡介
斯蒂芬‧布伊斯曼(Stefan Buijsman)
十八歲時就在荷蘭萊頓(Leiden)大學取得碩士學位,隨後赴瑞典攻讀博士學位。他用18個月(而非通常的四年)的時間就獲得博士學位,使他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博士學位畢業生之一。他目前從事數學哲學方面的博士後研究工作。
譯者簡介
胡守仁
芝加哥大學數學博士,曾任淡江大學數學系教授。譯有《數字奇航》、《毛起來說三角》、《隨機法則》、《希爾伯特的23個數學問題》、《連結》、《最ㄅㄧㄤˋ的數學公式》、《妙不可言的數學證明》、《數學家是怎麼思考的》、《醉漢走路》,與《打開魔術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