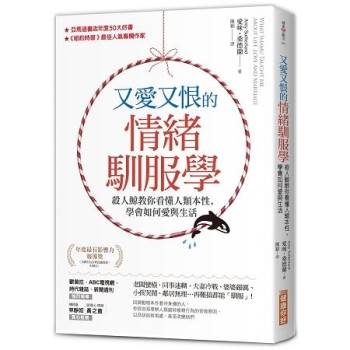咖啡因萬歲!
沒有咖啡,便沒有文明!
「我們有如此進步的社會文化,應該歸功咖啡的出現!」——朱爾.米榭勒
小小咖啡豆,翻轉世界文明八百年!
咖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儼然已成為一部分人的必需品,也是社交的代名詞,便利商店、咖啡廳、餐廳,甚至辦公室茶水間都能看見它的蹤影。如此日常的飲品,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卻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它啟蒙西方文明,也改變人類歷史走向。當阿拉伯人開始種植咖啡,他們的文明發展比其他民族更快:當鄂圖曼王國掌握咖啡豆大權,他們便成為世上最有勢力的國家;當咖啡在英國出現,便掀起國家爭霸與征服世界意志;而法國大革命,也是起於巴黎咖啡館興盛之時。
咖啡曾經是藥物、祭祀物品,被回教徒視為惡魔的飲料,但由威尼斯商人引入歐洲後成為十七世紀城市文化象徵,二十世紀初又因文人聚集咖啡館,成為知識傳播、辯論公共議題的時尚飲料。
作者為了揭開咖啡的謎團,從咖啡發源地衣索匹亞出發,途經阿拉伯、埃及、伊朗、土耳其到歐洲,走遍了四分之三的世界,踏上各種有趣、危險、驚心動魄的旅程,嚐遍了各式各樣的咖啡,也走訪過去咖啡豆被運往葉門的路線。
他不畏危險穿越邊界禁地與危險區域,到衣索匹亞調查咖啡的祭祀儀式,再穿越印度尋找咖啡豆種子來源,還經過薩伊奴隸以前走過的咖啡樹路徑、巴西以前關奴隸的咖啡種植農場。在伊斯坦堡小巷,在維也納、倫敦與巴黎咖啡館,都有他的足跡。
透過本書,跟隨著作者的見聞與歷史爬梳,你將更了解咖啡對世界文明帶來的巨大影響!
各界好評・一致推薦
・專文導讀・
韓懷宗|咖啡學系列作者
・一致推薦・
余宛如|生態綠董事長
馮光遠|國寶級白目作家
馬世芳|廣播人、文字工作者
宋世祥|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創辦人
陳志煌|Fika Fika Cafe 創辦人
各界一致讚譽
◆ 「貫穿歷史又已經全球化的咖啡,無疑是我們認識人類過往與當今世界的最佳探針。這本《咖啡癮史》豐富的歷史爬梳與文化紀錄讓每個人都成為咖啡杯裡的人類學家。」── 宋世祥|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創辦人
◆ 「剛左派飲食文學的代表。這部作品巧妙融合咖啡狂熱者的歌誦,與真正的行家觀察。」──《出版人週刊》
◆ 「本書非常的有趣、迷人與豐富……作者一手『釀造』的『濃醇』內容,絕對會讓你上癮!」──《柯克斯書評》
◆ 「這是一本完美有趣的作品,作者精采編織咖啡的傳播史,爬梳西方文明的重要歷程。」──《華盛頓郵報》書評
◆ 「一段有趣的探險,成就這本書的重要地位。」──《獨立報》書評
◆ 「非常有趣……我再也不會以同樣的態度看待早餐的咖啡了。」──傑夫.格林瓦德(著名旅遊作家)
◆ 「非常好玩的一本書。作者為了追求完美咖啡,帶領讀者走過衣索匹亞、巴黎,再從土耳其的芳香小屋直到巴西。這杯香濃的咖啡讓你品嚐到最後一滴,都會覺得很棒!」──馬克.羅森布倫(歷史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