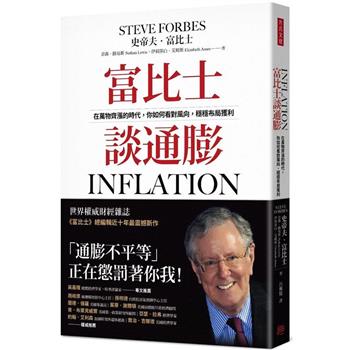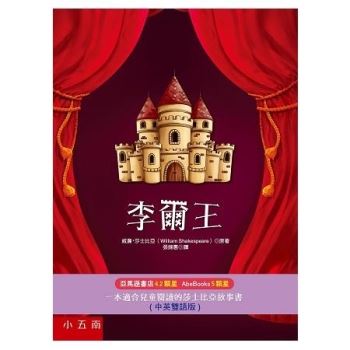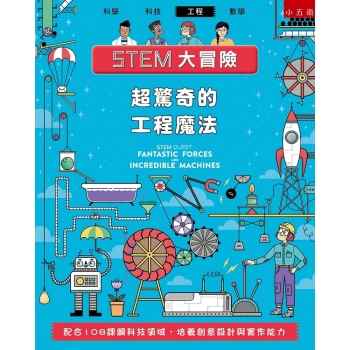暢銷書《達賴喇嘛的貓》作者大衛米奇,最新作品。
堪比《達文西密碼》的懸疑之作
堪比《達文西密碼》的懸疑之作
最黑暗的時刻,最艱鉅的任務
被盜走的佛像、人人覬覦的古老典籍、神祕難解的伏藏
多傑與馬特,一九五九年與二○○七年
一名藏人,一名英國人
命運交織,橫跨時空的祕密,究竟是什麼?
一九五九年,當中國紅軍侵入西藏,這個國家最黑暗的時刻來臨,年輕的僧侶丹僧多傑,心中升起了無比的使命感。他接受了一項任務,即將穿越喜馬拉雅山,與慈林喇嘛和旺波一起,面對重重危難,將古老的祕密典籍,帶到安全之地。而另一位主角,馬特,則從倫敦到美國工作,在美期間,遇到隔壁住著一位僧侶,各種神祕的巧合,密密交織。
多傑與馬特,一九五九年與二○○七年,一名藏人,一名英國人,橫跨時空的祕密,究竟是什麼?
本書在真實的歷史背景之上,融入佛教的世界觀,架構出極具張力的懸疑小說。從中國入侵西藏開始,一連串與生死搏鬥的危機,被盜走的佛像、人人覬覦的古老典籍、神祕難解的伏藏。以現代而細膩的小說筆法,打造具有佛教文化色彩的魅力之作,是一部超過宗教限制,劇情起伏堪比丹布朗《達文西密碼》的傑作。
劇情簡介──
量子科學家馬特,終於發現自己的身世之謎,來到了不丹虎穴寺,為打開千年傳承的伏藏預作準備。然而就在開啟伏藏的前夕,慈林喇嘛卻被人殺害!珍貴的藥師佛像也不翼而飛,而佛像裡頭藏著的蓮師伏藏也隨著佛像被盜走了。
馬特由不丹來到加德滿都,企圖尋回伏藏與藥師佛,不料卻被惡人盯上,邪惡之人的目標,究竟是佛師佛?還是伏藏?還是馬特的性命?馬特為了擺脫惡人,從加德滿都,來到杜拜,再到都柏林,與學者愛麗絲會合,令人驚恐萬分的是,愛麗絲也遭遇危險!愛麗絲的研究計畫,竟然阻礙了藥廠的龐大利益!兩人再度逃亡,而逃亡其間,也漸漸發覺,愛麗絲關於身心醫學的研究計畫,與伏藏之間,有著一絲隱密的關聯。
作者的話──
《馬特萊斯特的奇幻旅程》是一部虛構小說。如果其中的角色、情節和主題令人不禁信以為真,那是由於我將現實的元素依據我個人的經驗、加上我的想像力,編織在這個故事裡的緣故。
讀者們有必要知道的部份是,小說中關於藥師佛修行儀軌的部分全然屬實。作為事部密續(Kriya Tantra)傳統中的一部分,藥師佛的存在難能可貴,祂的修行儀軌可以大大地增進我們的禪修,尤其是當我們專注在療癒自己或他人時。世世代代以來,這項修行儀軌已經深切裨益了無數個世代的禪修者。藥師佛心咒已經傳唱了數百年,就如同小說裡描述的一樣。我衷心地希望,藉由創作這本小說,能激起許多人對這項非凡的修持方法的興趣,樂意去深入瞭解它所帶來的轉化力量。
名人推薦
吳佳璇 精神科醫師
洪仲清 臨床心理師
楊重源 精神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