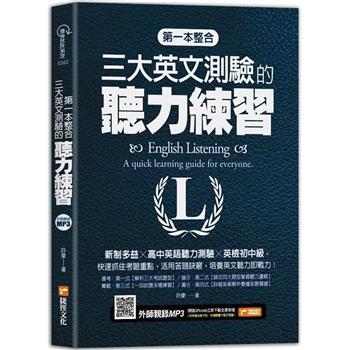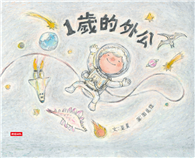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從文化到文創的圖書 |
 |
從文化到文創:迎向數位、佈局全球的文化政策與文創產業 作者:洪孟啟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1-1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41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94 |
設計 |
$ 331 |
中文書 |
$ 332 |
觀念/趨勢 |
$ 332 |
Books |
$ 332 |
Books |
$ 332 |
Books |
$ 332 |
社會 |
$ 370 |
社會 |
$ 37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文創產業融合營銷觀念與生產技術雙改變的趨勢,也是通俗文化與數位科技的黏著劑。現已步入以人為中心的「營銷3.0」階段!
文化全球化已成必然,文化創意產業隨著科技進步,逐漸成為生活文化最重要的產業之一,更被各國視為未來具有大幅成長潛力的產業。
本書以學理為基礎,以案例為佐證,暢談台灣如何在全球文化的衝擊下,仍能保有在地文化特色,並打造一條創意經濟的道路。
先自全球地緣戰略環境來看,近六百年來,人類文明的推展是以歐美為中心,從歐洲中心到國際化,再到全球化,人類的命運日益唇齒相依,全球化的壓力,極端氣候所引發的生存危機、經貿發展所帶動的區域競合、人口結構變化所影響的產業發展、資訊革命所激起的新一波生活形態、民粹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合流所淺藏的動亂陰霾乃至層出不窮的病毒,似乎皆再再告示人類社會已經走到了一個不得不合作分享的境地,也預示必要重新組合時代的來臨。
次從數位時代環境來看,資訊與智能科技推動的第三、第四兩波產業革命,的確嘉惠全球,並且實質上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然而也另有先天下之憂的自擾處。
在生活中,個人的選擇不再是個人,而是依從周邊網絡關係,商品的行銷策略也作了大轉彎,主攻網群,藉網路行銷攻城略地,培養網軍取代原本的廣告銷售網,不只商場如此,就連政治戰場亦如此,原本有機社會關係之下的社會忠誠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部落形式的同儕忠誠,商場上以品牌忠誠為核心,政壇則以幫派關係作鏈結,幫規取代黨規,幫派利益高於民眾利益。
個人為了不被群體拋棄,也為了自身安全利益,自願也不自願、半推半就的接受監控,有如浮士德和魔鬼交換靈魂。資本主義體系重組,其結果不是資本主義體系變得沒落,而是更強大,監控資本主義體系形成,在充分掌控監控力之後,更藉數位聚合功能,它如虎添翼地站上另一個獨孤求敗的高峰。
末由文化環境來看,文化創意產業不是單一文化和產業現象,猶如其多雜性(multiplicity)本質,多雜性也是文創產業的最大功效,它提供了更多樣的工作選擇機會,相對的也給予年輕人更廣的適性發展空間。
文創產業在心態上必須不斷調適瞬間變化的時間,不把自己困在給定的時間,要勇於突破時間牢籠;另外於空間上要吸納各種技術工具,以現下言即是數位科技;要善用各種文化工具,諸如展演工具,總合而言是要宏觀、微觀能力兼具。
文化發展是迢迢漫長路,隨著時空與日常生活不斷變化,文創產業有過之而無不及,並且強韌的調適能力與執行力即更為關鍵,無論觀察、理解與執行亦皆宜掌握全球化趨勢的三大環境:全球地緣戰略環境、數位時代環境和文化環境。
文創產業已然成為文化與產業雙發展的全球共同趨勢,面對全球在地化、消費全球性結合地方特質,文創產業的發展,將更依恃深厚的文化底蘊。
區域經濟合作、維繫生態共生體系、全球性的政治合作與去意識形態,是必然方向。文化發展隨時空與日常生活不斷變化,文創產業如何透過強韌調適能力與強化執行力更為關鍵,無論觀察、理解與執行,皆應掌握全球化趨勢的三大環境:全球地緣戰略環境、數位時代環境、文化環境。
台灣本身富含多元豐盈的文化資產,同時包容與快速吸收外來文化,當各地文化已藉全球化浮出水面,台灣亟須將文化視為戰略的一環。
面對新趨勢的戰略設計,本書以文化論述為根本,以草根文化人為師,從第一線文化工作者,反思文化不在象牙塔內,而是滲入草根、浸透血脈。當文化扎根回歸文化初衷,打造由下而上的肥沃土壤,每一顆民間的文化種子,都能夠著床與開花。
作者簡介
洪孟啟
出生
民國36年4月20日,出生上海市。
學歷
政治大學東亞所法學博士、政治大學東亞所法學碩士、淡江大學歷史系文學士
經歷
文化部部長
文化部次長
臺灣省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台北縣政府秘書長
台北縣政府副秘書長
銘傳大學秘書長
銘傳大學助理教授兼公共事務處處長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處長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副主任
臺灣省政府文化處副處長兼處長
台北師範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台北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佛光大學兼任副教授
日本橫濱美術大學特聘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兼任副教授
東海大學兼任副教授
臺灣省政府參議兼外事室主任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駐美秘書
中央日報地圖週刊主編
交通大學兼任講師
政治大學法律系講師
清華大學講師兼課外組主任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現職
銘傳大學講座教授
文化臺灣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中華文教經貿創意恊會榮譽理事長
考試
75年甲等外交特考優良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