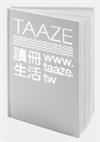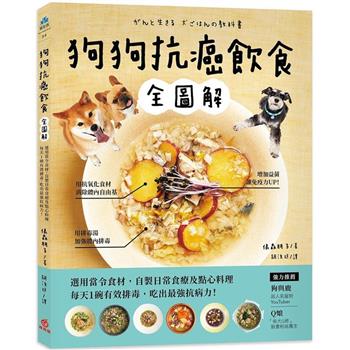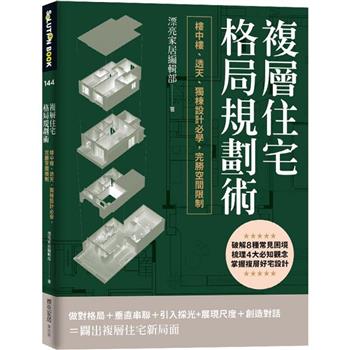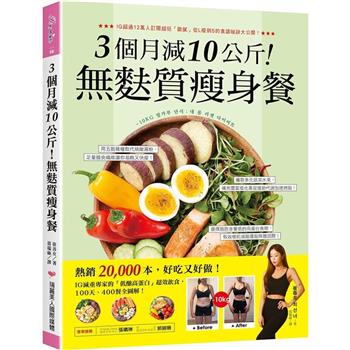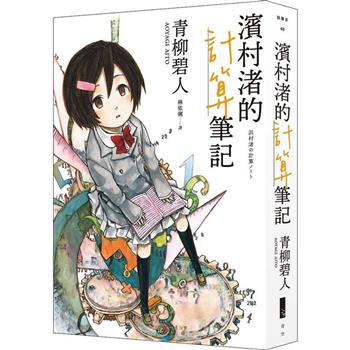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平)-三民文庫052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三民網路書店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平)-三民文庫052
- 圖書簡介
管子七臣七主:「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言復興中華文化,則創新我國之法律,亦係當今要務之一。但從事者須通曉孕育我國法系(Geneology of Law)之我國傳統文化、背景及精神,纔能在法制上著眼,法律上著手。陳顧遠教授這部著作,詳釋我國文化與我國法系之間的母子關係。怎樣將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華法系形成更活的法系,這是本書的著眼 所在。
- 作者簡介
陳顧遠
1896年生陝西三原人北京大學法學士現任台大、政大等教授 - 序
序
文化不是出自個性,而係創自群性,不是天才個人所能獨創,而是大多數人不斷努力的結果,這就和鳥做巢,蛛結網本於自然現象的個體行動不同。大思想家的創宗立說,必直接間接有其所承,大科學家的發明器物,也必直接間接有其所取。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並與賢士大夫遊,才能集大成而創立儒宗。瓦特發明蒸汽機,牛頓發明地心吸力,絕不是毫無前人的影響,祇看見壺裡水開,蘋果落地,就會有這檨的成效。而且其思想、其發明,若無多數人的領悟傳播,也不能成為文化的主要部分而有助於人生。文化既然是多數人努力的結果,必須有了社會,彼此共同相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因社會的產生並不斷地發展下去,法律便應運而起,不問其形式,不問其內容,不間其為禁令,不間其為約章,法律的核心總是社會生活的規律,而為社會心理力所表現的。所以有些學者,就說「有社會即有法」,或者說法先於國家而存在。當然了!有這種法的社會,雖然不是國家,卻是多少有公權力存在的社會,如氏族,如部落是。文化不是處在靜止的狀態,而是在動的狀態中求發展,縱有迴瀾也可望其復興。所以有人說文化不是一種「存在」,其本身乃是一種「演變」;倘若不能演變而衰微而靜止,便成了死的文化,也就失去了文化對人生的價值。這和蜂群居而釀蜜,蟻群居而生活,萬古不變的情形又有何異。論其變動雖然不像自然方面有一定不移的規範,有確定無貳的路線,但其動而不忘其本,變而能廣其效,雖在變動中,還得同時要靠變動中的法律,與其配合為其支柱。否則一般文化已有變動的跡象而法不變,這便是惡法,祇有我國法家和西歐分析法學派說它是「惡法勝於無法」。反之,一般文化尚在慢慢演變中,而法突然變到簇新的地步,也是不行,王莽的變法,洪秀全的建制,都歸失敗,就是這個緣故。總而言之,在文化的演變中,也須要有演變的法律助其演變方可。有人說,教育是擔負了保持文化延續文化等等責任,實則法律也同樣有這種責任。因為沒有演變的法律扶助文化的演變,這種變動都是不易成功;況且教育的所以能達其功效,也是靠了法律能維持社會秩序,乃可弦歌不輟,避免了最後一課的不幸,以教育學術等等與經濟政治法律作一個比喻,更見得法律及一般文化在其進展中有密切的關係。教育學術好比文化的腦髓神經,沒有它們,全身失靈,等於肉偶;經濟好比血液循環,沒有它,滋養無著,衰弱不堪。政治法律好比體軀,乃是腦髓神經和血液循環所託的部分;而政治仍只算是皮肉,法律才是骨幹,同樣是不可或缺的。一個人祇有體軀而無生命靈魂,自然不行,但是體軀──尤其骨幹──而不健全或有異狀,也就影響了其它部分在其效能上的表現。除了上述法律對於一般文化的作用外,再從文化的本身而言,尚有一種狀態,不可忽略,那就是文化對於法系的關係了。因為文化不是以某一個生活圈為中心而延展於全人類,也不是開始即係有意識的為人類全面性的集中發展,多少是具有民族性的。雖然在最初的神權階段,各民族的文化似乎大同小異,然而這種「同」,既非由於共謀,且各有其本色,更非即向同一目標發展,故仍各有其民族性;必須由各民族的文化相交流,乃可逐步融合而建立人類的共同文化。這是人類分佈於全球各部分,受了自然環境影響及彼此相互模仿,致與他部分人經久隔離的事實,無可如何者。然而有人說文化是人性的發展,沒有東西的根本差別。就人類文化的本身而言,當然如此;因為各民族文化的內容,雖然如何不同,都是人類所創造,都是人類的文化,都是因「人的所以為人」有其共同點,然後各民族間彼此的文化才可以交流,才可以吸收。一如中國文化始終是中國文化,然因時間的不同,也不妨有殷文化、周文化、秦漢文化和唐宋文化等等區別。那麼在人類發展的事實上既係分區而居,分族而處,形成了許多民族,各民族也都各有其自動的單獨創造文化的能力,漸次發展演變各自成其體系了。依前所述法律是社會的安定力,是隨著文化的演變而演變,以助長文化的演變,文化既多少具有民族性,而在同一民族生活的單位上,自然也不能離開法律,甚或藉法律的力量而使其文化傳播甚遠,一如由文化的傳播而將法律的精神傳播它處一樣。因而在國際法以外各有其國內法;在世人夢想的「世界私法」以外仍各有其國內私法。並因文化的表現於法律方面,初則各樹立其民族生活單位的規律,繼則彼此間的規律亦或交流而融合,於是就有所謂法系的建立。一個法系對於另一個法糸而言,仍然多少帶有民族性在內,尤其是由眾多民族構成一個大的民族生活單位,而自創立的法系如是;或一個大的民族分成數個生活單位而屬於同一法系如是。所以一個法系廣被於多數國家,也可以說是有助於各該國家彼此間文化的交流,逐漸收取融合之效。法律對於一般文化的建立和發展,雖然有極大的作用,然而法律畢竟是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個民族生活單位的文化所指示的整個趨勢之下,它也不能反其道而行。如若不是這樣的法律,其法律也就不能扶持其文化,甚或摧殘了固有的文化,今日大陸上匪共的法律就是這樣。因而在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團體,有某種文化,便形成某種法律。最好的立法並不是憑著自己的意識創造某種法律,祇是憑著自己的智慧選擇出某種法律是民族所需要的,是社會所期望的。各種法律的分佈在全世界,也就是表明了民族文化的不同、或在眾異中而有其小同。同時,某一法系的昌明,至少可說某一體系的文化在法律的表現上有其優勢;反之,某一法系的衰弱,若在其固有的一個民族生活單位方面,也可說是其固有的一般文化走向消沉之道。所以提到中國固有法系便不能不談到中國文化,由中國固有文化而為中國法系的觀察,乃為探本追源之論。中國文化如何影饗到中國固有法系,而中國固有法系如何對中國文化起反應,這就是本來要說的話了。本書共列六篇論文,雖篇章各有所指,而精神實屬一貫。首篇標題為「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乃一總名,包羅甚廣,係從中國文化本位上論中國法制及其形成發展,並予以重新評價。可說是著者數十年來潛心這一問題的現有結論。第二篇為「從中國法制史上看中國文化的四大精神」,這與前篇所採的觀察角度不同,更能探知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之真諦所在,並將中國文化歸納而為四大主流,足為前篇的補充資料。第三篇為「中國固有法系之簡要造像」這又是對於中國固有法系的精神作了另一種畫面的描寫,而其所根據的背景,當然是中國固有文化了。第四篇為「中國政制史上的民本思想」,這是專文研討中國文化四大精神中的「扶弱抑強的民本思想」,足見中國固有文化,雖缺乏整個的民主觀念,但對於民有民享觀念,卻有深入的研究領悟。第五篇為「中國現行法制之史的觀察」,這是因為論古的目的在於通今,文化的價值在於實證,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的真正價值,並非祇為空論,儘可從現行法制上證實出來,所以便插入了這篇論文。第六篇為「中華法系之回顧及其前瞻」,也許可說是本書的一篇結論了。從這六篇論文看來,當能對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問題,有其徹底的瞭解,而文化本身與法律方面的密切關係更或有了一個相當的證明。是為序。陳顧遠序於臺北市雙晴室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 目次
序
從中國文化本位上論中國法制及其形成發展並予以重新評價
從中國法制史上看中國文化的四大精神
中國固有法系之簡要造像
中國政制史上的民本思想
中國現行法制之史的觀察
中華法系之回顧及其前瞻
附錄 (一)陳著「中國法制史」日文本譯者序 西岡弘
(二)陳著「中國婚姻史」日文本譯者序 籐澤衛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