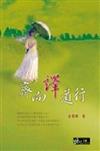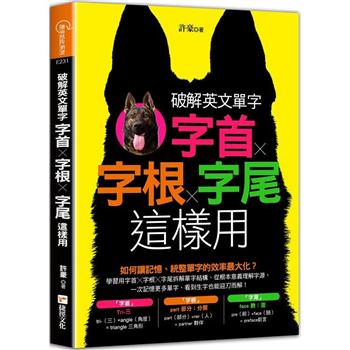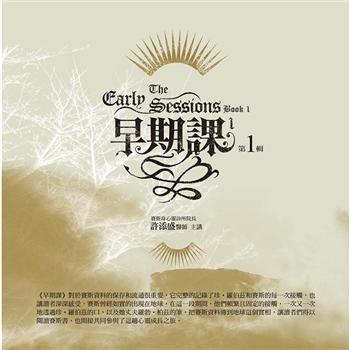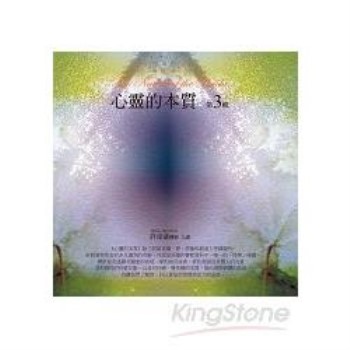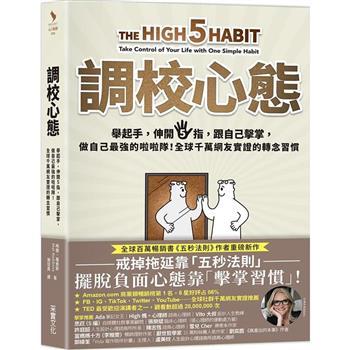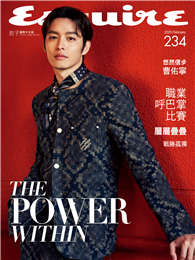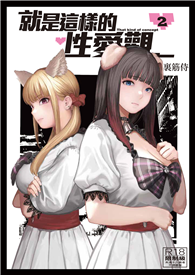自序一
無時無處不翻譯
收到三民書局快遞寄來金聖華教授有關翻譯的新著《齊向譯道行》樣版時,我正在書寫一篇有關利用外文資料以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演講稿。那講稿的題目是:『〈歸鳥〉幾隻?』〈歸鳥〉是陶淵明的四言詩題目。西方漢學家James Robert Hightower和Burton Watson都曾經翻譯過這首詩,但二人譯筆下的鳥,卻有單數與複數之別,觀其譯題便可知。Hightower譯為Homing Birds,Watson則譯為The Bird Which Has Come Home。我想透過這兩種不同的英譯詩,以及其他實際的英、日文翻譯及學術論著,從另一個方向來做說明。有時參考外文的翻譯或研究資料,會更有助於反省,而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產生更進一步的深層的瞭解。事實上,過去教書時,我時常會盡可能提供學生們這方面的課外資料的。
金聖華大學時代讀的是英語系,其後留學法國,多年來她擔任翻譯系的教授,又致力於推廣翻譯工作。我雖讀的是中文系,教授中國文學,但由於生長背景而具備中、日雙語能力,也實際上做過一些翻譯工作,兩人的興趣和關注點接近,使我們在公私的場合上都有許多說不完的話。
此次藉為聖華這本新書寫序的機會,得以先睹為快,拜讀了她這四十篇有關翻譯的文章,更進一步認識了相對晤談時她所沒有表現出來的一面。四十篇文章多為發表於《英語世界》刊物的專欄作品。大概是受到版面的規定,看得出當初執筆時篇幅須得節制,內容或有割捨,而未能暢所欲言;但有幾個主體分為兩期續撰,仍能了遂心願。
做為翻譯系的教授,聖華長期在學院內主持「翻譯工作坊」,認真教學,作育英才。除了理論根基,她更重視譯事的實際推敲斟酌,不放過一字一句,舉凡花草色彩、眉目五官,乃至於篇名書名、作品雰圍、文化異同,均予細究。她舉出學生們的優、劣作業,分析所以,更以自身的翻譯經驗,及古今名家的業績提供比對佐證,把譯事的發生,以及不斷的修飾過程,終至於滿足定稿,或雖非十分滿足卻不得不暫時定稿的憂喜告訴了讀者。那個讀者,可能是一個有志從事翻譯的年輕學子,他們將會從這些實例中,得到諄諄善誘的良師一一指點而受益匪淺。那個讀者,或可能是一個也有翻譯經驗的同道,他們將會在書中所言及的各種細節,例如在組頭韻(alliteration)的費心上,或定調前後的顧左盼右,甚至於為了一個名詞而遍查《辭源》、《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辭典》、《中華食用植物》等片段,感到於我心有戚戚焉。
難得聖華把許多的翻譯問題,用散文的方式書寫出來。原先是寫雅典奧運的文章,講田徑、講劉翔、講他的成績,怎麼忽一轉就變成了討論morning、afternoon、nightingale?明明是寫上海的城隍廟之遊,夏日炎炎,遇著陣雨,手中無傘,尋找目標,卻找來「老」字的英譯,該當aged、grey with age、hoary、grey-headed還是white with age呢?
大概都是因為金聖華關心翻譯,喜愛翻譯、樂在其中,生活裡也就無時無處不翻譯的緣故吧。
自序二
教學相長談翻譯
《齊向譯道行》原是一個專欄的名稱,刊載於一本北京出版,行銷各地,並深受年輕人歡迎的刊物《英語世界》上。
2003年,在北京跟名翻譯家徐式谷先生晤面的時候,談起了翻譯的種種問題。徐先生力邀我為《英語世界》撰寫翻譯散文,遂於2004年1月正式開欄,此後每月一篇,刊載迄今。
徐先生在開卷語之前,對拙欄介紹如下:
「為了幫助提高翻譯水平,我們特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金聖華教授在本刊開設『齊向譯道行』講座,以她多年來從事翻譯實踐,翻譯教學和翻譯理論研究的心得,採取不同於高頭講章的隨筆形式,把她的經驗之談娓娓道來。」
徐先生的美言,我固然愧不敢當,但是,拙欄的確是以散文的形式來談翻譯,而所談的也多半是個人的實際經驗。自2004年開始,到目前為止,所撰的翻譯散文已超過四十篇,逾十萬字,也該是結集出版的時候了。承蒙徐式谷先生惠允,更承蒙臺北三民書局劉振強董事長不棄,拙文得以由信譽超卓的三民書局出版發行,並以今日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
本書共收四十篇文章,除第二十篇〈別開生面的英語詞典〉原載《明報月刊》之外,餘皆出自《英語世界》,在此,特向雜誌社孟繁六社長及徐式谷主編致以由衷的謝意,沒有他們的不斷鼓勵,我絕不可能在繁忙的日程中,找出時間來寫下這些文字。同時,劉振強先生多年來對我的關懷支持,也是本書得以順利面世的動力,謹此致謝。
本書討論的內容,有不少是多年來在課室中與研讀翻譯的學生交流切磋的心得,翻譯之道,浩瀚無涯,能夠教學相長,的確樂趣無窮。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學生以及所有喜愛翻譯的朋友。
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