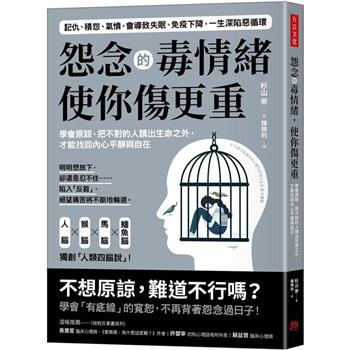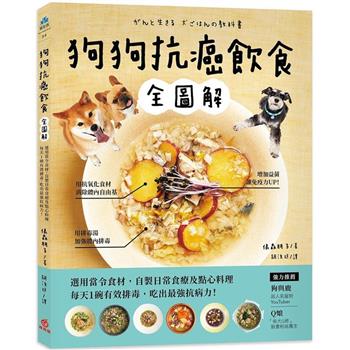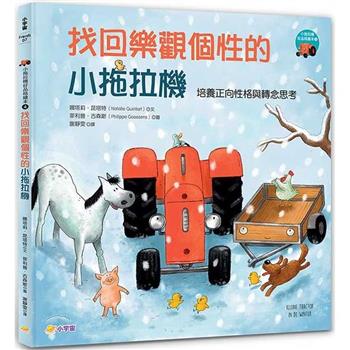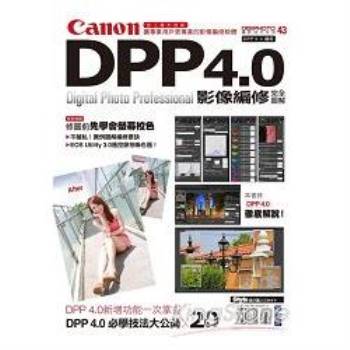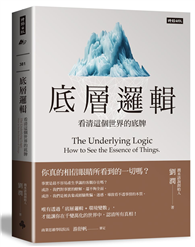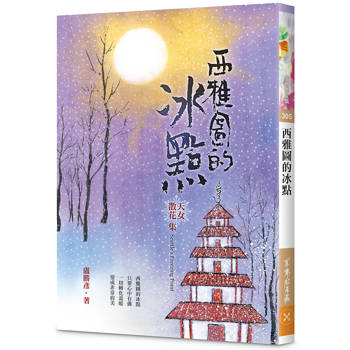一、傳統‧現代‧這一代
在英文裡有兩個字都是意味著現代的:一個是modern,另一個是contemporary。這兩個字,前者譯成「現代」,後者卻譯成「這一代」或同代人,同時代的,當代的等等。在中文裡現代的和當代的都含有相似的意義,也就是說它們都是指最近發生的事件或於我們今天所生存的日子而言。而事實上,這兩個字在英文裡有著極大的差別,modern可以概括contemporary,但contemporary卻不能包括modern。
在時間上來說,modern不一定是指現在而言,也許是指十年、五十年前的年代,我們看西洋很多叢書,可能有遠自十九世紀末葉的作品,至今仍然被列為現代叢書。十九世紀時代的作品,對十九世紀當時來說是「現代的」,今日我們仍然稱它為「現代的」,是因為它具有現代的精神,也許對十九世紀的本身來說,它已經超越了十九世紀,所以它是現代的。但若要說「這一代」或「當代的」,我們就僅能指我們自己這年代的作品。正如十九世紀的作家可以稱他那個年代的作品為「這一代的作品」,卻不能讓我們叫作「這一代的作品」。這一個基本觀念,常常被國人誤解,總認為「當代的」就是「現代的」。
由於時間上的指涉不同,故在空間上也就有了很大的區別,「現代的空間」較為遼闊、廣大,而「這一代的空間」較為狹小。
今天我們談「現代」與「傳統」的問題,我想不是簡單幾句話所能闡述清楚的。不過,我個人不想從兩者的名詞上作任何的闡釋,因為我始終認為:「今天的存在,就是明日的傳統。」而我們今天所要爭執的並非「現代」與「傳統」某些觀念上的問題,而是原則上的問題。一般人認為現代的都是新的,新的都是好的;而傳統的是舊的,凡是舊的都是落伍的,所以它是不好的,這種二分法的邏輯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部分年輕的一代,一昧學時髦,學現代,再加上部分盲從心理,認為西洋的都是新的,凡是新的都是好的。這一點崇洋心理可能與國人向來受窮困威脅有關,因為今天很多事物都被決定在金錢的條件下,早年英國詩人斯班德(Stephen Spender 1909-1995)也說過:「每一個人都看到這一明顯的事實,我們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太不詩意了。我們處處被逼著去認識,我們的文化是建築在金錢上的,金錢到處能產生一切有效的價值,沒有金錢就不能夠獲得即使是最起碼的一點滿足。於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現實和我們從小從教育中得來的對於詩的理解,大不相同了。」今天的社會趨勢,逐漸被物質文明所壟斷,文化這一支柱已顯得岌岌可危,而年輕一代所看到的也僅僅侷限於那些提著美鈔、法郎、英鎊的皮包,並沒有想到那些美鈔、英鎊都是替外國人洗盤子、清水溝苦出來的。那豆大的粒粒汗珠淌在外國人餐碟上的悲哀,你能想像到那種出賣自尊的苦楚嗎?你能想像到那種卑躬屈膝的卑微嗎?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有些莘莘學子,的的確確到外國學了一點東西回來,但有大多數卻是莫明其妙的,在國內不但是學歷史,學中國文學的,甚至有些已經在大學裡執教多年文史的人,還設法到國外去替外國人洗碟子。如果他真正去洗碟子,目的只是為了賺錢,實在也無可厚非。可是,他居然在洗碟子之餘去改學物理、化學,甚至於核子科學,像這種捨本逐末地求學問,我不知他們是否真的是天才,能夠學貫天文、地理、科學、哲學各大學問,如果真有這種天才,我們也只好說聲:「錯怪了!」否則,我認為這些人實在太重視金錢的價值,而忽視了比金錢更為珍貴的精神價值。
崇洋最原始的心理要素,就是因為金錢作祟。假定每一個留學生回來以後裝滿的都是學問,而不是美鈔、英鎊,我想咱們這一代的前途就非常樂觀。相反的,如果個個留學生裝回來的都是大綑大綑的美鈔、英鎊和洋貨而不是學問,那我們這一代就很悲哀了。
我們今天談「傳統」與「現代」,首先我認為大家要先站在本位上來談,不要拋開本位去空談那些毫不著邊際的問題。我們今天最值得重視的也就是所謂「現代」這個時髦的名詞,所帶給年輕一代的影響,譬如很多中學生或大學裡的一二年級學生,常常口口聲聲喊著沙特、卡繆、卡夫卡的名字,學著他們的苦悶、嘔吐、迷失等等,但我們捫心自問,有幾個人真正看完過沙特、卡繆的全部著作?有幾個人是真正下過苦心研究過他們的時代背景,思想淵源的?我們只知道沙特的苦悶、嘔吐,從來就沒人注意到當年沙特參加地下工作,馳騁疆場,堅決反抗德軍艱苦戰鬥的行動,以及他早年發表的反法西斯主義論文、小說等等,都是具有強烈的戰鬥意志,和積極的人生觀,他並不是靠那麼一點「嘔吐」就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我們看到他當年在德軍俘虜營裡的苦難,看到他那時不顧生命的威脅,去為祖國效忠的精神,實在不是那麼一次「嘔吐」,就能把所有的積鬱嘔完的。
今天有很多年輕人,連礮聲都沒有聽過,居然也學著別人的口吻去謳歌戰爭,或者詛咒那因戰爭而帶來的死亡和災難,我不知他真的經驗了戰爭以後會有什麼感覺,是否還會有那種雅興,是否還會有那種輕鬆的心情。總之,我覺得我們的年輕一代太缺少自身的經驗,無論對現實,對整個人生,都缺乏正確的體認,只是學了一點皮毛,就認為自己懂得了天下事。譬如對西洋的東西,只認識了別人扔在字紙簍的一點點碎片,我們就自以為「權威」,這是多麼幼稚又可憐的舉動。同樣的,我們對於上一代的遺產根本沒有作過苦心的整理,就斷定那些都是陳舊的,不合潮流的,所以必須把它們一腳踢開,我們為什麼不在提腳踢它之前,先虛心認識一下它們的面目。我們老是責備老一代不成器,難道我們就成器了嗎?這些年來,我聽得最多的是責難我們的上一代沒有留下豐富的遺產,使我們無法在世界上揚眉吐氣。其實,上一代有上一代努力的代價,上一代有上一代留下的遺產,只是我們不覺得而已。我們大都受到「外來和尚會念經」的變態心理的作祟,使我們忽視了自身的重要性。因此,在強調「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給年輕一代的思想要件上,我個人認為首先要讓年輕一代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讓他先認知自己的本位。作為人不是先有世界的經驗始能存有的,而是他個人自覺自己的存有,即已存在。沙特認為「人永遠在他本身之外;在投射、遺失的時候,他使人存在。因為,人是如此自我超越的,也只有在自我超越中才能抓住東西,他自己才是先驗存在的中心。」而我不是這種想法,我認為人必須在自我認知的自覺存有中,才能存在,超越自我只是對另一個自我的慾求,它不一定能成為真我。所以「超越」的本身含有一種慾望的追求,人是存在於不斷的創造和肯定中。
我們稍微注意一下我們這一代,包括比我們更年輕的一代,有幾個人能真真實實地認清過一個「真我」?我們在咖啡廳、電影院、街頭、音樂廳、夜總會,舉目所見的,不是頹廢,就是迷失。他們抽著外國香煙,喝著大口大口的洋酒,喊女人的小名,認為自己已經是迷失了,認為上一代沒有給他指出一條光明大道,所以只好用享樂來麻醉自己,他們根本就忘了自我存在的價值,他們根本就忘了建立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體系。一切依賴於上一代的法則,依賴於上一代的繩規,認為嚼著上一代成仁的光榮是理所當然,根本不認為那是一種恥辱。試想這樣我們能成為「這一代」嗎?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應該考慮到,也必須考慮到的,就是我們自己也會有被稱為上一代的一天。那時候,他們指責他們的上一代(我們這一代)不爭氣,沒有給他們留下豐富的遺產時,我們難道有地可容嗎?因此,我認為不管誰要否定傳統的價值,必須先具有自己能真正否定的理由。否定,並非是叫叫嚷嚷就行的,它必須具有足以否定的條件。而要人承認「現代」,也必須具有令人相信為現代的理由。並非在咖啡廳、夜總會端著酒杯喊出來的。今天的確有很多理由,可以使我們相信「現代」的存在價值,但也同樣的有很多理由,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傳統」的價值。關鍵在於我們自己有沒有理由,使人相信而又能承認「這一代」的成就。
「這一代」的成就,就是這一代的功績,這功績並不是靠咱們叫叫嚷嚷一陣子就能獲得的,必須靠我們的心血和生命去換取。因此,我個人不主張批評「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價值問題。我認為只要是能歷經多少個年代的篩漏而仍能遺傳下來的,都是不朽的作品。只要是不朽的都是好的,試看我們今天的作品,有幾部能經得起半個世紀時光的透視,而不致變質的呢?我們有幾部作品能經得起半打知識分子的檢視而仍能呈列在文化櫥窗裡的呢?我們口口聲聲喊著「現代」,卻完全忘了「這一代」的重要性。因此,我個人認為與其爭吵「傳統」與「現代」的價值,倒不如去努力創造「這一代」的成績。今天的存在就是明天的歷史,歷史的篩漏是最無情的,它留不下任何一點贋品。我們能不能在歷史上佔一席位,完全要看我們這一代自己的努力和奮鬥。所以我認為去爭「傳統」與「現代」,反不如去看重我們「這一代」的努力,看重「這一代」的成績,這樣比什麼都光輝而恆久。
二、論現代小說的語言
語言是人類的心意的記號或符號的現示(表達)的一種工具,無論其有無聲音,都足以傳達人心裡的意義。如畫家的光、色、線條,音樂家的音符,甚至於舞蹈家的動作……這些都是傳達其心意,但不需要發出任何聲音,而又能呈現其真實的語言。故語言乃是一種圖式,一種記號,一種人類內在心意的表達工具。
(一)
語言是表達人類內在心意的一種手段,也是溝通人與人之間接觸的一種工具,我們從人類學上可以看出,只要我們發現有人,我們也就同時發現他們有語言的能力。有了語言,自然就有意義的傳遞。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在他的名著《人類理解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中說:「儘管人們有著千變萬化的思想可用以增益他人和增益自己,愉悅他人和愉悅自己,不過這些思想隱在心中,不為他人所見,自己也無法弄清晰。沒有思想的交流,則不能獲取社會的安樂和利益,因此人們必須拿出一些外表可見的記號,來將構成思想的意念傳達給別人。」人與人之間思想的交流,心意的傳遞,其最原始的工具就是語言記號,而語言記號是始於人類意念之展示。因此,最原始的語言,也是最曖昧的。我們經常可以發現初生的嬰兒用其特有的簡單聲音記號(語言),來呼喚他的母親或褓姆,在他使用這些聲音記號時,他也許已知道這必將能滿足於他的需求,達到他語言記號的傳遞效果。如嬰兒的啼哭,可能是現示其饑餓本能的需求,而他的母親必感知其所需,因而達到其哭聲傳遞心意的效果。德國哲學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說:「語言必須被當作一種能力,而甚於一個成品。它不是一件現成的事物,而是一個連續的歷程;它乃人心一再重覆的苦工,運用有音節的聲響來表達出思想。」1
卡西勒這個觀點是說明語言本身是人類一連串意義的連續表現。而事實上,我們今天對語言的認識,已不是簡單的符號作用,也非單純的心意之現示。義大利美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認為語言學與美學是同一事件。他說:「任何人研究普通語言學或哲學的語言學,也就是研究美學的問題;研究美學的問題,也就是研究普通語言學。語言的哲學就是藝術的哲學。」接著他又說:「如果語言學真是一種與美學不同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就不會是表現,這在本質上是審美的事實;那就是說,我們必須否認語言為表現。但是發聲音如果不表現什麼,那就不是語言。語言是聲音為了表現而經過連貫、限定,和組織。」2美國哲學家阿爾斯通(William P. Alston 1921-2009)也說:「如果我們只將自己的思想保留心中就已滿足,則語言可廢矣。就因為我們有彼此傳遞思想的需要,於是不得不使用公共可見的記號來表示穿掠在心中的私有意念。一個語文表式就在這樣充作指引中獲取了它的意義。」3近代大多數的語言學家都認為語言是人類後天經驗所塑造的意念之表達,而英文裡,被國人譯成「意念」的這個idea,含有觀念、想像、概念、心像、表像、意識內容,較接近於語言學家意見的是觀念和想像,較接近於心理學家意見的則是概念、意識內容。語言學家認為人心本是一片渾沌,後來經過對具體事物的直覺與認識,而後藉習慣性的聲音相混合,最後形成一個個意念,這個意念就是人心裡最原始的語言。心理學家認為語言是人類「意識內容」的呈現,但生物學家他對語言的觀點又不同了,他認為語言是動物本態對外伸展的能力,只要是動物都有語言的成分。而我個人認為人類語言,是以自我表明事象的一種表式。我們試圖將我國文字中的「語言」兩個字重新組織一下,改為「言吾言」的形式,可以發現前面的「言」字為動詞,而後面的「言」字為受詞。如果我們再用另一種語式來表達它的意義,則是「說我說的話」。我們任誰使用語言這一工具時,都是「說我說的話」,換句話說,我們的任一句語言都是表達自己的意志。莊子在《外物篇》中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其中的「意」就是「言」的代表,而「言」是「意」的表示。
以上所引的諸家之說,說明了語言是人類呈現心意的一種工具。而我們同時也可以推演出人的語言與其他動物的語言之間,具有某種本質上的共相,或者說是同質性。譬如我們對一隻狗或一隻貓,經常呼喚一種習慣性的聲音,那麼久而久之,牠就有適應這種聲音的反應。同樣的,如果我們能經常聽狗吠或貓叫的聲音,久而久之,我們也同樣可以感知牠所吠的聲音是代表什麼意義。譬如在鄉間,深夜裡有狗吠的聲音特別急促,我們很可能意識到將有陌生人路過或其他的事故發生,這就是人與動物之間,一種語言本質上的共相性。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在動物的發聲與人類的語言之間,有一種很大的差異情形存在,所謂「人為萬物之靈」,這也正意謂著人的語言有別於其他動物的發聲。事實上,動物的發聲,是完全主觀、直覺的,它表示諸多不同的感情狀態,但並不指涉什麼。而人類的語言,似乎自始就有其「意謂」或「指涉」的對象。在初民的狩獵生活中,常常發出近乎野獸般的呼喚,這種呼喚很難有它的正確意義,但有一定的對象,那就是對野獸的嚇阻或震驚的作用。
從初民的語言演變到今天現代人的語言,這其間的變化是極大的,是從不斷的泯除與不斷的增長中演續下來的。卡西勒說:「人類一切形式的語言都是完美的,只要它們能夠在一種清楚和適當的方式之下,成功地表達人類的感情與思想。所謂原始語言,和原始文明情狀以及原始心靈的一般傾向相合,其一致的程度,並不亞於現今語言和今日各種精美文化的高度相關性。」
(二)
語言的演變是由渾沌,漸趨以有秩序、組織的呈列;是由曖昧的,漸次以清晰的現示;是由一己意義的表現,漸趨於形成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情感之交換的工具;是由自然的,發展成為某一特定的意義。在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社會中,語言成為一種固定的、具體的,而有實際目的所用的工具,成為他們在大型政治鬥爭中最有力的武器。於是,某些抱有政治野心的領導者,為了扮演一個重要的領導者角色,不得不一再地修改自己的語法,使自己說的話更動人。這可能是修辭學最早的創始。修辭學的發現,使語言邁入了另一個境界,那就是最普通的語言,也能修飾得更潔淨,更完美,更動人。
現代語言,已在不斷的修飾與創造下,進入一個極其完美的境界。然而現代人的心靈意識日益複雜,對心意的現示,已非某一固定的語言形式所能滿足,而必須倚靠多種語言形式。譬如他們要說明一件物理現象,可以用一般慣用的語言形式,把那件物理現象解說清楚,即達到目的。但如果我們要現示一種人心裡的真實,我們就必須靠文學的語言,如詩、小說等等。這種語言形式,不一定能讓人人都懂,也不一定能讓人解釋。這種語言形式給人的感受是多樣的,因為它是一種情緒的、想像的語言。每一個讀者有每一個讀者的情緒與想像,而每一個讀者也有每一個讀者的感受力與被感受力。所以文學的語言是異於任何著作的語言,英國語言學家理查茲(I. A. Richards 1893-1979)在他的《文學批評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中說:「說明事象與傳達事象所用的語言,二者各有其技巧。前者為要使人認清某種事象,後者則為語言本身的技巧。易言之,前者是『實用的文學』之語言,後者乃是『純文學』之語言。」而事實上,在實用的語言中,也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日常生活中各個事件之自然的關係,例如聽見狗吠而知道牠將要咬人,聽見雷聲而知道將要下雨等等。凡屬這種意思的領悟,都是從我們習得的經驗與某一刺激物相結合而成立的。另一種則是經過社會同意而發展為某一特定的意義,像十字街口的紅綠燈,足球裁判員的銀笛,以及我們書寫的文字等等。」4哈克將我們書寫的文字,作為經過社會同意而發展為某一特定意義是正確的,但文字本身的意義雖為固定,由文字所組織的語言卻是變化的。此外我們說文字本身不具有任何意義也是對的,因為文字本身是由人類共同意識所造成的一種特定意義始存在。卡西勒說:「如果二者之間沒有一種至低限度的相同,一個字便不能夠『意謂』一件事物。符號和其對象之間的連繫,必須是一種自然的連繫,而不僅僅是一種約定俗成的連繫。沒有了這樣一種自然的連繫,人類文字的語言便不能完成它的工作—它將成為不可解。」
文字的特定意義,是由社會的共同意識所認可。譬如一株樹,我們用「樹」字來表示它,這個「樹」字是經過社會同意而發展為特定的意義。如果我們起始就用「木」字來表示「樹」字的意義,相沿下來,我們也就認為「木」就是「樹」。正如英語民族中認為tree就是我們所指的「樹」一樣,但它除了我們習慣上公認的「樹」的意義以外,同時也有人把玫瑰叫作tree或bush,而不叫作rose。
從這裡我們同時也發現到文字本身的特定意義,是隨著社會共同意識的認知而有所改變的。因為它的本質就是一種符號,符號是心意活動的一種現示,而語言則是心意現示的一種工具,因此我們可以說語言的表現和心意的表現,同樣都是由符號所現示的一種記載。然而,除了這兩種有形的現示以外,在我們的心底似乎還存有一種未經現示為記號的觀念,這種未經現示的心靈活動,近代心理學家已給予一個名詞叫「無意識」心理。無意識心理狀態,對現代作家的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現代詩人和小說家,對於無意識心理世界的把握與呈現,已使現代文學創作展示了一個嶄新的世紀—一個較之前輩作家更為真實,對人類靈魂的透視。
無疑的,語言在表現方法上已揚棄了昔日的諸多陳規,而另創了他們自己的一套法則,這套法則正足以表現出人類心靈深處較大部分的活動—這是一種非具象的真實存在,既流動,又飄忽,故極難把握。而這種存在,從我們的經驗知識來說,似乎還用不著援用那些哲學上的形而上學,或其他更為虛玄的學問來證實。事實上,今天大多數的現代詩人和現代藝術家都已超越了習成記號的意念,而進到探索語言記號以上的境界。我們常常聽人慨嘆說「一言難盡」或者「這是語言無法形容的」等等,正是指既有的語言已無法表出那種未經浮現的意念。而這種意念,事實上已存在於人類的內在世界裡。現代詩人和現代小說家為了傳真這一內在世界的實況,不得不採用一種「快速的自動語言」來展示這一真實。於是,現代小說的語言確已異於前輩作家的語言,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
----------------------------------------
1見卡西勒所著《論人》(An Essay on Man)第八章第三節。如欲見其詳,則需見其另一著作《符號形式的哲學》(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2見朱光潛譯克羅齊著的《美學原理》第一四六頁。
3見何秀煌譯阿爾斯通著的《語言的哲學》第三十四頁。三民書局出版。
4見哈克(Hanold Hake)所著《語言與說話》(Language and Speaking)。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現代小說論(四版)的圖書 |
 |
現代小說論(四版) 作者:周伯乃 出版社: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5-2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26 |
中文書 |
$ 136 |
文學作品 |
$ 136 |
Literature & Fiction |
$ 144 |
小說/文學 |
$ 144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152 |
華文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現代小說論(四版)
現代小說與其理論研究是周伯乃先生多年心血所在,此書更是他在文學理論領域極具代表性的介紹和批評集。
在這一本《現代小說論》中,他詳盡地介紹了現代小說的語言、形態、結構,以及人物刻劃等等,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現代小說中的「意識」 與「無意識」的關係,和精神分析學與現代小說的關係等等。同時也指出了現代小說常賦予這一代苦悶的原因,可以說這是一本瞭解現代小說精神最完整的巨著。
作者簡介:
周伯乃,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生。籍貫廣東。
曾任《中央月刊》、《中央日報》副刊編輯、《世界論壇報》副社長兼副刊主編、行政院文建會秘書、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河南開封大學董事兼客座教授、中國詩歌藝術學會理事長等職。民國四十六年開始創作詩歌和散文,著有詩集《荒城》、《濁流溪畔》、散文集《又是秋涼時節》、《晴窗小語》、《周伯乃散文集》等;現代文學理論之著作另有《二十世紀的文藝思潮》、《中國新詩的回顧》等,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國軍新文藝金像獎、教育部詩教獎等獎項。
TOP
章節試閱
一、傳統‧現代‧這一代
在英文裡有兩個字都是意味著現代的:一個是modern,另一個是contemporary。這兩個字,前者譯成「現代」,後者卻譯成「這一代」或同代人,同時代的,當代的等等。在中文裡現代的和當代的都含有相似的意義,也就是說它們都是指最近發生的事件或於我們今天所生存的日子而言。而事實上,這兩個字在英文裡有著極大的差別,modern可以概括contemporary,但contemporary卻不能包括modern。
在時間上來說,modern不一定是指現在而言,也許是指十年、五十年前的年代,我們看西洋很多叢書,可能有遠自十九世紀末葉的作品,至...
在英文裡有兩個字都是意味著現代的:一個是modern,另一個是contemporary。這兩個字,前者譯成「現代」,後者卻譯成「這一代」或同代人,同時代的,當代的等等。在中文裡現代的和當代的都含有相似的意義,也就是說它們都是指最近發生的事件或於我們今天所生存的日子而言。而事實上,這兩個字在英文裡有著極大的差別,modern可以概括contemporary,但contemporary卻不能包括modern。
在時間上來說,modern不一定是指現在而言,也許是指十年、五十年前的年代,我們看西洋很多叢書,可能有遠自十九世紀末葉的作品,至...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再版序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文藝思潮像大海的狂瀾撲激而來,尤其英語系列的文藝作品,包括詩、散文、小說、戲劇,書坊陳列的都是英、美、法等大家的翻譯作品,原文書店中,除了科技、理工及工具書以外,大都是那些比較著名的小 說、散文、詩集。因為,國家正處於戒嚴時期,凡三十年代的作品都在禁售、禁買、禁談之中。而我得天獨厚。其一,是一九五五年四月,我從空軍通信學校(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前身)畢業,分派在新竹機場服務,機場裡有一間佔地兩百多坪的圖書館,除了一些科技方面的書,大部分是文藝方面的詩、散文、小說、劇本...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文藝思潮像大海的狂瀾撲激而來,尤其英語系列的文藝作品,包括詩、散文、小說、戲劇,書坊陳列的都是英、美、法等大家的翻譯作品,原文書店中,除了科技、理工及工具書以外,大都是那些比較著名的小 說、散文、詩集。因為,國家正處於戒嚴時期,凡三十年代的作品都在禁售、禁買、禁談之中。而我得天獨厚。其一,是一九五五年四月,我從空軍通信學校(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前身)畢業,分派在新竹機場服務,機場裡有一間佔地兩百多坪的圖書館,除了一些科技方面的書,大部分是文藝方面的詩、散文、小說、劇本...
»看全部
TOP
目錄
再版序
一、傳統‧現代‧這一代 1
二、論現代小說的語言 8
三、論現代小說的形態 25
四、論小說中的人物刻劃 37
五、淺談小說中的懸疑效果 58
六、論小說中的意識與無意識 66
七、精神分析學與現代小說 78
八、論感覺性的小說 103
九、論環境與個人才能 111
十、論小說結構 122
十一、論短篇小說的創作技巧 134
十二、現代小說給這一代的苦悶 154
十三、論文藝的鑑賞與批評 174
附錄、西方文藝思潮對我國六十年代文學的影響 183
一、傳統‧現代‧這一代 1
二、論現代小說的語言 8
三、論現代小說的形態 25
四、論小說中的人物刻劃 37
五、淺談小說中的懸疑效果 58
六、論小說中的意識與無意識 66
七、精神分析學與現代小說 78
八、論感覺性的小說 103
九、論環境與個人才能 111
十、論小說結構 122
十一、論短篇小說的創作技巧 134
十二、現代小說給這一代的苦悶 154
十三、論文藝的鑑賞與批評 174
附錄、西方文藝思潮對我國六十年代文學的影響 183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周伯乃
- 出版社: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5-23 ISBN/ISSN:978957146087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