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蕩寇志》是《水滸傳》續書的一種,作者俞萬春以保守者的思想「尊王滅寇」作支撐,杜撰梁山被剿滅的情節,以陳希真父女為中心,寫陳希真、雲天彪及張叔夜征討梁山,擒殺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的故事,用這樣的創作和藝術構思,另類完結《水滸傳》。
本書以清咸豐三年初刻本為底本,校以重刻、石印本,補齊了原刻本中的缺誤,其他文字一律未改,以存原貌。《蕩寇志》作為文人作家的作品,其結構精撰,描寫細膩,文字精鍊,多用典故。此外,內文大量的夾批夾注和回評,或說明作者創作意圖,或闡釋小說情節,剖析寫作手法,評論人物得失。整體的評點,頗有見地,值得讀者留意欣賞。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蕩寇志(上/下)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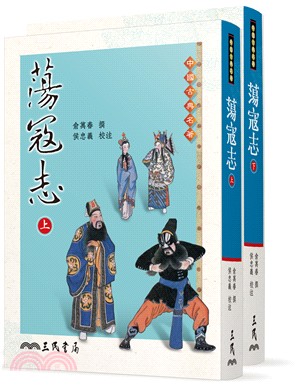 |
蕩寇志(上/下) 出版社:三民 出版日期:2017-07-0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240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63 |
文學 |
$ 363 |
Literature & Fiction |
$ 414 |
小說/文學 |
$ 427 |
中文書 |
$ 428 |
中國古典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蕩寇志(上/下)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侯忠義
1936年生,遼寧大連人。1959年吉林大學畢業,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師承魏建功、王重民先生,講授中國文學史、中國目錄學史、文言小説研究等課程。1989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教授。主要著作:《中國文言小說書目》、《中國文言小說參考資料》、《中國文言小說史稿》、《漢魏六朝小說史》、《隋唐五代小說史》、《水滸傳會評本》等。主編《中國小說史叢書》、《明代小說輯刊》、《古代小說評介叢書》、《中國珍稀本小說叢書》等。
侯忠義
1936年生,遼寧大連人。1959年吉林大學畢業,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師承魏建功、王重民先生,講授中國文學史、中國目錄學史、文言小説研究等課程。1989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整理研究室主任、教授。主要著作:《中國文言小說書目》、《中國文言小說參考資料》、《中國文言小說史稿》、《漢魏六朝小說史》、《隋唐五代小說史》、《水滸傳會評本》等。主編《中國小說史叢書》、《明代小說輯刊》、《古代小說評介叢書》、《中國珍稀本小說叢書》等。
目錄
引 言 一—十六
插 圖 一—四
回 目 一—五
正 文 一—一一三七
附 錄 一—六
序 古月老人
俞仲華先生蕩寇志序 陳奐
序 徐佩珂
蕩寇志緣起 忽來道人
識 語 俞龍光
回 目
上 冊
結水滸全傳 一
第七十一回 猛都監興師勦寇 宋天子訓武觀兵 二
第七十二回 女飛衞發怒鋤奸 花太歲癡情中計 二五
第七十三回 北固橋郭英賣馬 辟邪巷希真論劍 三九
第七十四回 希真智孫推官 麗卿痛打高衙內 五五
第七十五回 東京城英雄脫難 飛龍嶺強盜除蹤 七三
第七十六回 九松浦父女揚威 風雲莊祖孫納客 九四
第七十七回 皂莢林雙英戰飛衛 梁山泊羣盗拒蔡京 一一九
第七十八回 蔡京私和宋公明 天彪大破呼延灼 一四二
第七十九回 蔡太師班師媚賊 楊義士旅店除奸 一五八
第八十回 高平山騰蛟避仇 鄆城縣天錫折獄 一七二
第八十一回 張觷智穩蔡太師 宋江議取沂州府 一八六
第八十二回 宋江焚掠安樂村 劉廣敗走龍門厰 二○○
第八十三回 雲天彪大破青雲兵 陳希真夜奔猿臂寨 二一八
第八十四回 苟桓三讓猿臂寨 劉廣夜襲沂州城 二三六
第八十五回 雲總管大義討劉廣 高知府妖法敗麗卿 二五八
第八十六回 女諸葛定計捉高封 玉山郎請兵伐猿臂 二七六
第八十七回 陳道子夜入景陽營 玉山郎贅姻猿臂寨 二九六
第八十八回 演武㕔夫妻宵宴 猿臂寨兄弟歸心 三一二
第八十九回 陳麗卿力斬鐵背狼 祝永清智敗艾葉豹 三三一
第九十回 陳道子草創猿臂寨 雲天彪征討清真山 三四九
第九十一回 傅都監飛鎚打冠勝 雲公子萬弩射索超 三六八
第九十二回 梁山泊書諷道子 雲陽驛盜殺侯蒙 三八六
第九十三回 張鳴珂薦賢決疑獄 畢應元用計誘羣奸 四○五
第九十四回 司天臺蔡太師失寵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四二○
第九十五回 陳道子鍊鐘擒巨盜 金成英避難去危邦 四三七
第九十六回 鳳鳴樓紀明設局 鶯歌巷孫婆誘姦 四五七
第九十七回 陰秀蘭偷情釀禍 高世德縱僕貪贓 四七三
第九十八回 豹子頭𢡖烹高衙內 筍冠仙戲阻宋公明 四八九
第九十九回 禮拜寺放賑安民 正一村合兵禦寇 五○七
第一百回 童郡王飾詞諫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 五二一
第一百一回 猿臂寨報國興師 蒙陰縣合兵大戰 五三六
第一百二回 金成英議復曹府 韋揚隱力破董平 五五一
第一百三回 高平山叔夜訪賢 天王殿騰蛟誅逆 五六六
第一百四回 宋公明一月䧟三城 陳麗卿單鎗刺雙虎 五八二
第一百五回 雲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閒游承恩嶺 五九八
下 冊
第一百六回 魏輔樑雙論飛虎寨 陳希真一打兖州城 六一三
第一百七回 東方橫請元黃吊掛 公孫勝破九陽神鐘 六三○
第一百八回 真大義獨赴甑山道 陳希真兩打兖州城 六四六
第一百九回 加亮器攻新柳寨 劉慧娘計窘智多星 六六二
第一百十回 祝永清單入賣李谷 陳希真三打兗州城 六七七
第一百十一回 陳義士獻馘歸誠 宋天子誅奸斥佞 六九二
第一百十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報國除楊志 七一○
第一百十三回 白軍師巧造奔雷車 雲統制兵敗野雲渡 七二六
第一百十四回 宋江攻打二龍山 孔厚議取長生藥 七四一
第一百十五回 高平山唐猛捦神獸 秦王洞成龍捉參仙 七五五
第一百十六回 陳念義重取參仙血 劉慧娘大破奔雷車 七七一
第一百十七回 雲天彪進攻蓼兒洼 宋公明襲取泰安府 七八九
第一百十八回 陳總管兵敗汶河渡 吳軍師病困新泰城 八○七
第一百十九回 徐虎林臨訓玉麒麟 顏務滋力斬霹火 八二五
第一百二十回 徐青娘隨叔探親 汪恭人獻圖定策 八四一
第一百二十一回 六六隊大攻水泊 三三陣迅掃頭關 八五九
第一百二十二回 吳用智禦鄆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八七九
第一百二十三回 東京城賀太平誅佞 青州府畢應元薦賢 八九八
第一百二十四回 汶河渡三戰黑旋風 望蒙山連破及時雨 九一四
第一百二十五回 陳麗卿鬬箭射花榮 劉慧娘縱火燒新泰 九三一
第一百二十六回 凌振捨身轟鄆縣 徐槐就計退頭關 九四七
第一百二十七回 哈蘭生力戰九紋龍 龎致果計擒赤髮鬼 九六四
第一百二十八回 水攻計朱軍師就擒 車輪戰武行者力盡 九七九
第一百二十九回 吳用計間顏務滋 徐槐智識賈虎政 九九六
第一百三十回 麗卿夜戰扈三娘 希真晝逐林豹子 一○一○
第一百三十一回 雲天彪旂分五色 呼延灼力殺四門 一○二七
第一百三十二回 徐虎林捐軀報國 張叔夜奉詔興師 一○四三
第一百三十三回 衝頭陣王進罵林冲 守二關雙鞭敵四將 一○六○
第一百三十四回 沉螺舟水底渡官軍 臥瓜鎚關前激石子 一○七五
第一百三十五回 魯智深大閙忠義堂 公孫勝攝歸乾元鏡 一○八九
第一百三十六回 宛子城副賊就擒 忠義堂經畧勘盜 一一○四
第一百三十七回 夜明渡漁人擒渠魁 東京城諸將奏凱㨗 一一一九
第一百三十八回 獻俘馘君臣宴太平 溯降生雷霆彰神化 一一三四
第一百三十九回 雲天彪進春秋大論 陳希真修慧命真傳 一一五一
第一百四十回 辟邪巷麗卿悟道 資政殿嵇仲安邦 一一六六
結 子 牛渚山羣魔歸石碣 飛雲峯天女顯靈蹤 一一八一
附 錄 一一九五
插 圖 一—四
回 目 一—五
正 文 一—一一三七
附 錄 一—六
序 古月老人
俞仲華先生蕩寇志序 陳奐
序 徐佩珂
蕩寇志緣起 忽來道人
識 語 俞龍光
回 目
上 冊
結水滸全傳 一
第七十一回 猛都監興師勦寇 宋天子訓武觀兵 二
第七十二回 女飛衞發怒鋤奸 花太歲癡情中計 二五
第七十三回 北固橋郭英賣馬 辟邪巷希真論劍 三九
第七十四回 希真智孫推官 麗卿痛打高衙內 五五
第七十五回 東京城英雄脫難 飛龍嶺強盜除蹤 七三
第七十六回 九松浦父女揚威 風雲莊祖孫納客 九四
第七十七回 皂莢林雙英戰飛衛 梁山泊羣盗拒蔡京 一一九
第七十八回 蔡京私和宋公明 天彪大破呼延灼 一四二
第七十九回 蔡太師班師媚賊 楊義士旅店除奸 一五八
第八十回 高平山騰蛟避仇 鄆城縣天錫折獄 一七二
第八十一回 張觷智穩蔡太師 宋江議取沂州府 一八六
第八十二回 宋江焚掠安樂村 劉廣敗走龍門厰 二○○
第八十三回 雲天彪大破青雲兵 陳希真夜奔猿臂寨 二一八
第八十四回 苟桓三讓猿臂寨 劉廣夜襲沂州城 二三六
第八十五回 雲總管大義討劉廣 高知府妖法敗麗卿 二五八
第八十六回 女諸葛定計捉高封 玉山郎請兵伐猿臂 二七六
第八十七回 陳道子夜入景陽營 玉山郎贅姻猿臂寨 二九六
第八十八回 演武㕔夫妻宵宴 猿臂寨兄弟歸心 三一二
第八十九回 陳麗卿力斬鐵背狼 祝永清智敗艾葉豹 三三一
第九十回 陳道子草創猿臂寨 雲天彪征討清真山 三四九
第九十一回 傅都監飛鎚打冠勝 雲公子萬弩射索超 三六八
第九十二回 梁山泊書諷道子 雲陽驛盜殺侯蒙 三八六
第九十三回 張鳴珂薦賢決疑獄 畢應元用計誘羣奸 四○五
第九十四回 司天臺蔡太師失寵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四二○
第九十五回 陳道子鍊鐘擒巨盜 金成英避難去危邦 四三七
第九十六回 鳳鳴樓紀明設局 鶯歌巷孫婆誘姦 四五七
第九十七回 陰秀蘭偷情釀禍 高世德縱僕貪贓 四七三
第九十八回 豹子頭𢡖烹高衙內 筍冠仙戲阻宋公明 四八九
第九十九回 禮拜寺放賑安民 正一村合兵禦寇 五○七
第一百回 童郡王飾詞諫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 五二一
第一百一回 猿臂寨報國興師 蒙陰縣合兵大戰 五三六
第一百二回 金成英議復曹府 韋揚隱力破董平 五五一
第一百三回 高平山叔夜訪賢 天王殿騰蛟誅逆 五六六
第一百四回 宋公明一月䧟三城 陳麗卿單鎗刺雙虎 五八二
第一百五回 雲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閒游承恩嶺 五九八
下 冊
第一百六回 魏輔樑雙論飛虎寨 陳希真一打兖州城 六一三
第一百七回 東方橫請元黃吊掛 公孫勝破九陽神鐘 六三○
第一百八回 真大義獨赴甑山道 陳希真兩打兖州城 六四六
第一百九回 加亮器攻新柳寨 劉慧娘計窘智多星 六六二
第一百十回 祝永清單入賣李谷 陳希真三打兗州城 六七七
第一百十一回 陳義士獻馘歸誠 宋天子誅奸斥佞 六九二
第一百十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報國除楊志 七一○
第一百十三回 白軍師巧造奔雷車 雲統制兵敗野雲渡 七二六
第一百十四回 宋江攻打二龍山 孔厚議取長生藥 七四一
第一百十五回 高平山唐猛捦神獸 秦王洞成龍捉參仙 七五五
第一百十六回 陳念義重取參仙血 劉慧娘大破奔雷車 七七一
第一百十七回 雲天彪進攻蓼兒洼 宋公明襲取泰安府 七八九
第一百十八回 陳總管兵敗汶河渡 吳軍師病困新泰城 八○七
第一百十九回 徐虎林臨訓玉麒麟 顏務滋力斬霹火 八二五
第一百二十回 徐青娘隨叔探親 汪恭人獻圖定策 八四一
第一百二十一回 六六隊大攻水泊 三三陣迅掃頭關 八五九
第一百二十二回 吳用智禦鄆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八七九
第一百二十三回 東京城賀太平誅佞 青州府畢應元薦賢 八九八
第一百二十四回 汶河渡三戰黑旋風 望蒙山連破及時雨 九一四
第一百二十五回 陳麗卿鬬箭射花榮 劉慧娘縱火燒新泰 九三一
第一百二十六回 凌振捨身轟鄆縣 徐槐就計退頭關 九四七
第一百二十七回 哈蘭生力戰九紋龍 龎致果計擒赤髮鬼 九六四
第一百二十八回 水攻計朱軍師就擒 車輪戰武行者力盡 九七九
第一百二十九回 吳用計間顏務滋 徐槐智識賈虎政 九九六
第一百三十回 麗卿夜戰扈三娘 希真晝逐林豹子 一○一○
第一百三十一回 雲天彪旂分五色 呼延灼力殺四門 一○二七
第一百三十二回 徐虎林捐軀報國 張叔夜奉詔興師 一○四三
第一百三十三回 衝頭陣王進罵林冲 守二關雙鞭敵四將 一○六○
第一百三十四回 沉螺舟水底渡官軍 臥瓜鎚關前激石子 一○七五
第一百三十五回 魯智深大閙忠義堂 公孫勝攝歸乾元鏡 一○八九
第一百三十六回 宛子城副賊就擒 忠義堂經畧勘盜 一一○四
第一百三十七回 夜明渡漁人擒渠魁 東京城諸將奏凱㨗 一一一九
第一百三十八回 獻俘馘君臣宴太平 溯降生雷霆彰神化 一一三四
第一百三十九回 雲天彪進春秋大論 陳希真修慧命真傳 一一五一
第一百四十回 辟邪巷麗卿悟道 資政殿嵇仲安邦 一一六六
結 子 牛渚山羣魔歸石碣 飛雲峯天女顯靈蹤 一一八一
附 錄 一一九五
序
引言
蕩寇志一名結水滸傳,七十回,結子一回,清俞萬春撰。屬近代俠義小說流派,是水滸傳續書的一種。它篡改了水滸傳後五十回的內容和結局,重新敷演了七十回,讓梁山好漢一個一個悲慘死去,成為水滸傳續書中的別類作品。
蕩寇志是中國近代時期產生的一部長篇章回小說,然而它並無近代轉變期小說的新時代特點,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俠義小說流派。它以立意和命題,對經典小說水滸傳的拮抗與對立,被視為傳統小說中的另類,並以它的認識價值和欣賞價值,確定了它在中國小說史中的地位。
蕩寇志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說?不少人視其為「反動文學的代表作之一」,斥之為「反動小說」,評價頗為偏頗,不夠實事求是;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則認為,「在糾纏舊作(按指水滸傳)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並說「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寫也不壞,但思想未免煞風景」。可見蕩寇志應屬上乘之作,而其立意和思想,魯迅謂「然此尚為僚佐之見」,也就是說,這是當時部分官僚士大夫階級對現實政治的態度,或開出的救世良方。作為小說作家,也反映了作者的創作心態和心路歷程。
作者俞萬春,字仲華,號忽來道人,浙江山陰(今紹興)人。他生於乾隆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九四年),死於道光二十九年(西元一八四九年),享年七十五歲。他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吏家庭,卻也生活在一個清嘉慶、道光間的衰世。他自少「於古今治亂之本,與夫歷代興廢之由,罔不窮其源委。下至稗官小說,風俗所繫,人心攸關,尤致意焉」(俞灥蕩寇志續序),可見他對政治敏感,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和對生活的洞察力。其子俞龍光敘其父經歷時說:「道光辛卯、壬辰間,粵東猺民之變,先君隨先大父任,負羽從戎。緣先君子素嫻弓馬,有命中技,遂以功獲議敘。」(識語)作者在青壯年時期,曾隨父鎮壓廣東猺民起義,受過官府嘉獎,但卻未功成名就,最終也不過是個秀才。他的家庭、經歷以及社會環境對他的思想形成和小說創作無疑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不言而喻的。
「不懂得嘉慶、道光間的遍地匪亂,便不懂得俞仲華的蕩寇志」(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眼光去剖析俞萬春和蕩寇志。亂世使他思定,理想就是「天下太平,朝野無事」(第一百四十回),而安定之法就是平定、鎮壓作亂者,這是他從生活經歷中得來的士大夫階級的體驗。他認為「邪說」盛行,特別是水滸傳中梁山造反者的行為,影響了現實中的叛亂者,其實那不過是他文人的一孔之見,社會矛盾才是基因和根本。他解決不了社會的根本矛盾,於是企圖用寫作蕩寇志來製造影響,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
關於時代影響了他的創作這一點,同治辛未(西元一八七一年)俞灥序說得很明白:「海內升平日久,人心思亂,患氣方深,仲華獨隱然憂之,杜邪說于既作,挽狂瀾于已倒,其憂世之心,可謂深也已矣;其立說之旨,可謂正也已矣。然而附仙女之真靈,托長安之一夢,抑又何其誕也!」序中指出作者所謂仙女託夢而著書之說是荒誕無稽的,為何不公開直接宣示自己是為憂世而著書,是為杜絕造反邪說的影響,為挽救世道人心開出的一個救世良方呢?實質上他不過是要將自己的理想,塗抹上天命的色彩而已。
嘉慶、道光以來,清王朝的統治由盛轉衰,各地民眾的反抗此起彼伏。影響較大的就有天地會、哥老會、白蓮教等,而規模最大的太平軍,也正在孕育之中。對嘉、道以來的衰微國勢,對腐敗昏憒的朝廷,有識之士主張變革。如與作者同時代的詩人龔自珍,就提倡「更法」、「改圖」,以拯救時弊。他「往往引公羊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二)。他在己亥雜詩中說:「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表達了他對清王朝腐朽統治的不滿和批評,要求擺脫專制淫威,改革政治的理想。然而俞萬春卻不是這樣。對沒落的清王朝,作者仍然情有獨鍾,充滿希望。他主張安定和諧,反對造反起事。末回張叔夜剿滅了梁山後歌頌說:「不數月,內外頒詔,聲震海隅,共見聖君、賢相郅治無為,從此百姓安居,萬民樂業,恭承天命,永享太平。」表達了作者的心聲,也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部分士大夫文人的心態。然而,這不過是他的一廂情願的幻想而已。末回評語指出:「安邦一段,按切時勢立言,不同浮響。」一針見血指出了蕩寇志的主旨是針對現實而發的。聯想他在第九十八回借筍冠仙之口訓斥宋江道:「貪官污吏干你甚事?刑賞黜陟,天子之職也;彈劾奏聞,臺臣之職也;廉訪糾察,司道之職也。義士現居何職,乃思越俎而謀?」就體現出作者的政治觀點和創作思想,那就是安於職守,做個良民,維持朝廷的穩定。作者煞費苦心地拖出一個水滸傳中最早受迫害的王進,讓他現身說法,指責林沖說:「高俅要生事害你,高俅何嘗不生事害我?我不過見識比你高些。不解你好好一個男子,見識些許毫無,踏著了機關,不會閃避;……難道你捨了這路,竟沒有別條路好尋麼?」(第一百三十三回)公然反對林沖反抗官府的行為。作者承認社會有太多的不公平,但為維護、創造太平、安定的局面,面對官府的橫行,你或逃避現實,歸隱山野;或只能俯首貼耳,聽任宰割,當好奴才。這就是俞萬春對時局的態度,對受迫害、被剝削者開出的一劑藥方,也是小說所表達的理念。
於是,他的同道者,就由衷地讚揚此書的出版和產生的影響。半月老人在同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一年)重刻本續序中說:「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托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仲華先生之蕩寇志,救害匪淺,俱已見之於實事矣。」這是從一個後來者的眼光,看出此書的創作目的和效果。然而蕩寇志挽救不了清朝,反抗者的血也不會白流。他站在時代潮流的對立面,妄圖阻止歷史前進的步伐,這無疑是作者的悲劇。作者去世之次年,即爆發了太平軍起事;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軍攻占南京,並定為太平天國國都,與清王朝對峙十一年,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反抗者對蕩寇志的批判。
據其子俞龍光所稱,蕩寇志草創於道光六年(西元一八二六年),寫成於道光二十七年(西元一八四七年),歷時近二十二年,經俞龍光修飾後,咸豐三年刻印於南京,並以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古月老人之序,題曰結水滸傳。
小說故事承接金聖歎偽作水滸傳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驚惡夢續起,並有結子一回。小說以陳希真父女為中心,寫了陳希真、雲天彪及張叔夜征討梁山,擒殺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的故事。作者認為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中,七十回以後的內容,包括梁山受招安、征方臘事,係羅貫中偽造。他在第七十一回卷頭語中明白地說:「乃有羅貫中者,忽撰出一部後水滸(案:指水滸後五十回)來,竟說得宋江是真忠真義,從此天下後世做強盜的,無不看了宋江的樣,心裏強盜,口裏忠義,殺人放火也叫忠義,打家劫舍也叫忠義,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義。看官你想,這喚做什麼說話?真是邪說淫辭,壞人心術,貽害無窮。……因想當年宋江並沒有受招安、平方臘的話,只有被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話。如今他既妄造偽言,抹煞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他指責羅貫中所作的七十回以後的水滸傳,完全是「邪說淫辭,壞人心術」,於是做起了翻案文章。他把水滸傳中忠義的代表宋江,變成了強盜的代表,又另外塑造了一個他理想中的「草野忠臣」陳希真,一個不與朝廷對抗、一心只為朝廷平叛的真忠義、假強盜。於是俞萬春就編造出了這樣一部真正偽言的結水滸傳,即蕩寇志來。其友徐佩珂吹捧說:「余友仲華俞君,深嫉邪說之足以惑人,忠義、盜賊之不容不辨,故繼耐庵之傳,結成七十卷光明正大之書,名之曰蕩寇志。蓋以尊王滅寇為主,而使天下後世曉然於盜賊之終無不敗,忠義之不容假借混朦,庶幾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矣。」(咸豐二年序)其實,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在「忠君」這一點上,與俞萬春並無不同。明代李贄忠義水滸傳序中說:「宋江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李贄的話是符合書中實際的。然而在俞萬春生活的時代裏,這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心態,是需要陳希真這樣的假強盜、真忠義,不與朝廷對抗,不與官軍對敵的「草野忠臣」,而把宋江等梁山好漢,寫成水滸傳中類同方臘那樣真造反的「強盜」,讓他們非死即誅,徹底覆滅。很明白,作者創造此書的主題思想就是「尊王滅寇」,在動蕩的年代裏,反對起事,也反對招安,必滅之而後快。這反映了反對變革,維持現存秩序的「僚佐」們,與統治者一樣,害怕群眾的恐懼心理,同時以「尊王」為號召,維護搖搖欲墮的封建王朝,美化行將滅亡的封建統治。總之,作為續書,他以正統的保守者思想作支撐,重新改寫了水滸後五十回的內容,杜撰了梁山被剿滅的情節,歪曲了梁山好漢的性格,增加了三十餘位反梁山的主將,用這樣的創作思想和藝術構思,以完結水滸傳。於是就產生了這部蕩寇志。
蕩寇志一反水滸的寫法,將魯達「聽潮而圓,見信而寂」的心已成灰的死法,處理為發狂而死。魯達對梁山感情最深,作戰最勇。而對梁山即將被張叔夜大軍摧毀的危難關頭,魯達更是奮勇殺敵,不肯收兵。宋江詫異道:「魯兄弟住居山寨有年,頗知紀律,今日為何幾番鳴金收他不回?」對梁山命運的深切關注,加上力疲神亂,使魯達著了瘋魔。他對宋江道:「兄長要殺上東京,灑家明日先殺張家兩個娃子,後殺張家老兒,一路打進東京,拆毀了金鑾殿,回來同你吃酒。」(第一百三十五回)他狂奔酣呼,大罵高俅,道:「今日灑家打殺了你,為民除害。你們這班狗才,教你們死個爽快!」又誤將忠義堂當作金鑾殿打得粉碎,大叫「灑家今番大事了也」而死。魯達的瘋狂,是他至死不改對奸臣昏君的痛恨、堅決造反到底的美好心靈的反映。
人間只要有不平,群眾的反抗就不會停止。梁山好漢爭取自由和做人權利的鬥爭精神,永遠值得歌頌,也是任何力量所鎮壓不了的。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評論蕩寇志說:「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采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事實確實如此。第八十四回評語中也說:「仲華深得耐庵之法矣。」並在評點中屢屢與水滸相比較。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描寫、結構安排等方面,明顯受到水滸的深刻影響,並刻意加以模仿,有的還是成功的。如第一百十五回唐猛擒豹,竟是武松打虎場景的再現,特別生動驚險,動人心魄;又第一百十回寫陳希真三打?州城,用真大義詐降,魏輔樑作內應,就學自「三打祝家莊」。某些情節描寫精細,獨俱匠心,頗有欣賞價值。如第九十六回鶯歌巷孫婆誘姦、第九十七回陰秀蘭偷情釀禍,情節寫得委婉曲折,人物形象鮮明。如陰婆子的刁鑽奸詐,孫婆子的貪財好利,紀二的陰險狡猾,戴春的好色愚蠢,姚蓮峰的品行不端,都刻畫得生動逼真,躍然紙上。其中的人情世態,風俗習慣,描寫得別出心裁,自然有致,不落俗套,可謂發之於「情」,宣之於「筆」,說明作者對市井生活的稔熟和觀察。又如小說開始寫陳希真父女出逃經過,從準備的路線、包袱、武器、馬匹、雇工等,描寫都很細膩,甚至可以說「巨細不遺」,但卻顯得異常真實。雇挑夫一段,先寫陳希真要挑夫簽個承攬合同,又叫鄰人作保,作法可謂「周密」;挑夫要調整包袱重量,兩頭均稱,以便省力,可謂「合理」;挑夫以為包袱過重,望多加些酒肉錢,亦屬「正常」等等,也反映了作者觀察生活的能力及筆力的成熟和老練。
語言上,蕩寇志突顯了文人創作的特點。作為文人作家的個人作品,結構精撰,描寫細膩;文字精煉,語言講究;多用典故,喜歡賣弄。他的文章是漂亮的。就文字和描寫而言,小說確實不乏精彩的對話和有個性的語言描寫,如陳希真與郭英娘子關於購馬的一段對話:
……希真又去看了看牙齒道:「你要賣多少銀子?」娘子道:「不瞞丈丈說,說價也由我討,只奴是本分人,老實說與你。先夫病重時,並不說落價錢,只對奴說:有識得的,便賤些也賣了;倘不遇?識貨的,情願沒艸料餓死了他,也不賣。前日有一個人勸我賣與湯鍋上,說倒有五七兩銀子,喫我發揮他一頓。今丈丈真個要買,隨你自說罷。」希真道:「我說不要怪。」娘子道:「何怪之有!」希真委實看得那馬合意得緊,便脫口說道:「與你一百兩足色紋銀,何如?」娘子暗驚道:「卻不道還值這許多,落得再要些。」便道:「一百兩少些,求加加。」希真道:「竟是一百二十兩。」娘子忖道:「再不賣時,恐決裂了。」……那娘子收了銀子,見牽了馬去,想起丈夫在日,止不住那腮邊的淚,雨點般的落下來。希真老大不過意。娘子道:「丈丈,還有副鞍韉,是這馬上的,你一發買了去罷,省得在奴的眼角頭。」希真去看了看,已是破的了。希真道:「鞍韉我便不要,你如果嫌馬價少,我再添你些罷。」說罷,去銀包裏又取出十兩來重的一錠銀與娘子。娘子那里肯收,說道:「奴自己?物傷心,並非嫌銀少。」(第七十三回)
這段對話,把一個想買馬,一個真賣馬,討價還價,雙方都關心馬的命運的那種心態、品格展露無遺。
就蕩寇志整體而言,它捨棄了水滸中那種詩詞相間的形式和通俗活潑的口語化、平民化語言,倒插入了大量公文書信,正發揮了作者的一技之長。但也使小說讀來沉悶。
小說有范辛來(金門)、邵祖恩(循伯)二人的大量夾批、夾注和回評。評點者應是作者的好友和知音,既熟悉作者的小說創作又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因此評點有的放矢,頗有見地。評語內容包括:說明作者的創作意圖,闡釋小說的內容和情節,剖析寫作手法、遣詞造句,評論人物得失等。回末評並對本回的章法結構、寫作技巧、人物關係等,做出了系統評論,並與水滸前傳比較,多所頌揚、阿諛之辭。評語與小說內容結合較緊密,特別是在評論中引用了大量歷史典故、古典詩詞,亦使評語內容較為充實。其中雖不少愚腐、平庸之筆,也不乏精彩見解,對讀者閱讀本書不無裨益。故我們保留了所有評語,未加任何刪節,以供讀者欣賞和研究。書中尚有作者自注五則(第七十六回、第一百二回、第一百二十回、第一百二十二回);其子龍光注九則(第八十二回、第一百十四回、第一百十八回、第一百二十二回、第一百二十五回、第一百二十七回),彌足珍貴。所有這些注解和評語,都為中國小說批評史提供了一份難得的資料。
本次整理此書,是以清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初刻本為底本,校以咸豐七年重刻本、光緒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煥文書局石印本,補齊了原刻本中的缺失和置誤文字。書中其他文字,一律未改,以存原貌。書中避諱之處多有,如康熙名玄燁,凡「玄武」、「玄黃」、「玄妙」,玄皆作「元」;道光名旻寧,「寧可」改成「凝可」,「徐寧」改成「徐凝」。又大刀關勝,因與關羽同姓,竟認為他是「強盜」,不配姓「關」,故改成「冠勝」等。我們一仍其舊,不加改動。
本書整理過程中的疏漏之處,祈請讀者批評指正。(節錄)
蕩寇志一名結水滸傳,七十回,結子一回,清俞萬春撰。屬近代俠義小說流派,是水滸傳續書的一種。它篡改了水滸傳後五十回的內容和結局,重新敷演了七十回,讓梁山好漢一個一個悲慘死去,成為水滸傳續書中的別類作品。
蕩寇志是中國近代時期產生的一部長篇章回小說,然而它並無近代轉變期小說的新時代特點,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俠義小說流派。它以立意和命題,對經典小說水滸傳的拮抗與對立,被視為傳統小說中的另類,並以它的認識價值和欣賞價值,確定了它在中國小說史中的地位。
蕩寇志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說?不少人視其為「反動文學的代表作之一」,斥之為「反動小說」,評價頗為偏頗,不夠實事求是;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則認為,「在糾纏舊作(按指水滸傳)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並說「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寫也不壞,但思想未免煞風景」。可見蕩寇志應屬上乘之作,而其立意和思想,魯迅謂「然此尚為僚佐之見」,也就是說,這是當時部分官僚士大夫階級對現實政治的態度,或開出的救世良方。作為小說作家,也反映了作者的創作心態和心路歷程。
作者俞萬春,字仲華,號忽來道人,浙江山陰(今紹興)人。他生於乾隆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九四年),死於道光二十九年(西元一八四九年),享年七十五歲。他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吏家庭,卻也生活在一個清嘉慶、道光間的衰世。他自少「於古今治亂之本,與夫歷代興廢之由,罔不窮其源委。下至稗官小說,風俗所繫,人心攸關,尤致意焉」(俞灥蕩寇志續序),可見他對政治敏感,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和對生活的洞察力。其子俞龍光敘其父經歷時說:「道光辛卯、壬辰間,粵東猺民之變,先君隨先大父任,負羽從戎。緣先君子素嫻弓馬,有命中技,遂以功獲議敘。」(識語)作者在青壯年時期,曾隨父鎮壓廣東猺民起義,受過官府嘉獎,但卻未功成名就,最終也不過是個秀才。他的家庭、經歷以及社會環境對他的思想形成和小說創作無疑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不言而喻的。
「不懂得嘉慶、道光間的遍地匪亂,便不懂得俞仲華的蕩寇志」(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眼光去剖析俞萬春和蕩寇志。亂世使他思定,理想就是「天下太平,朝野無事」(第一百四十回),而安定之法就是平定、鎮壓作亂者,這是他從生活經歷中得來的士大夫階級的體驗。他認為「邪說」盛行,特別是水滸傳中梁山造反者的行為,影響了現實中的叛亂者,其實那不過是他文人的一孔之見,社會矛盾才是基因和根本。他解決不了社會的根本矛盾,於是企圖用寫作蕩寇志來製造影響,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
關於時代影響了他的創作這一點,同治辛未(西元一八七一年)俞灥序說得很明白:「海內升平日久,人心思亂,患氣方深,仲華獨隱然憂之,杜邪說于既作,挽狂瀾于已倒,其憂世之心,可謂深也已矣;其立說之旨,可謂正也已矣。然而附仙女之真靈,托長安之一夢,抑又何其誕也!」序中指出作者所謂仙女託夢而著書之說是荒誕無稽的,為何不公開直接宣示自己是為憂世而著書,是為杜絕造反邪說的影響,為挽救世道人心開出的一個救世良方呢?實質上他不過是要將自己的理想,塗抹上天命的色彩而已。
嘉慶、道光以來,清王朝的統治由盛轉衰,各地民眾的反抗此起彼伏。影響較大的就有天地會、哥老會、白蓮教等,而規模最大的太平軍,也正在孕育之中。對嘉、道以來的衰微國勢,對腐敗昏憒的朝廷,有識之士主張變革。如與作者同時代的詩人龔自珍,就提倡「更法」、「改圖」,以拯救時弊。他「往往引公羊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二)。他在己亥雜詩中說:「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表達了他對清王朝腐朽統治的不滿和批評,要求擺脫專制淫威,改革政治的理想。然而俞萬春卻不是這樣。對沒落的清王朝,作者仍然情有獨鍾,充滿希望。他主張安定和諧,反對造反起事。末回張叔夜剿滅了梁山後歌頌說:「不數月,內外頒詔,聲震海隅,共見聖君、賢相郅治無為,從此百姓安居,萬民樂業,恭承天命,永享太平。」表達了作者的心聲,也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部分士大夫文人的心態。然而,這不過是他的一廂情願的幻想而已。末回評語指出:「安邦一段,按切時勢立言,不同浮響。」一針見血指出了蕩寇志的主旨是針對現實而發的。聯想他在第九十八回借筍冠仙之口訓斥宋江道:「貪官污吏干你甚事?刑賞黜陟,天子之職也;彈劾奏聞,臺臣之職也;廉訪糾察,司道之職也。義士現居何職,乃思越俎而謀?」就體現出作者的政治觀點和創作思想,那就是安於職守,做個良民,維持朝廷的穩定。作者煞費苦心地拖出一個水滸傳中最早受迫害的王進,讓他現身說法,指責林沖說:「高俅要生事害你,高俅何嘗不生事害我?我不過見識比你高些。不解你好好一個男子,見識些許毫無,踏著了機關,不會閃避;……難道你捨了這路,竟沒有別條路好尋麼?」(第一百三十三回)公然反對林沖反抗官府的行為。作者承認社會有太多的不公平,但為維護、創造太平、安定的局面,面對官府的橫行,你或逃避現實,歸隱山野;或只能俯首貼耳,聽任宰割,當好奴才。這就是俞萬春對時局的態度,對受迫害、被剝削者開出的一劑藥方,也是小說所表達的理念。
於是,他的同道者,就由衷地讚揚此書的出版和產生的影響。半月老人在同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一年)重刻本續序中說:「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托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仲華先生之蕩寇志,救害匪淺,俱已見之於實事矣。」這是從一個後來者的眼光,看出此書的創作目的和效果。然而蕩寇志挽救不了清朝,反抗者的血也不會白流。他站在時代潮流的對立面,妄圖阻止歷史前進的步伐,這無疑是作者的悲劇。作者去世之次年,即爆發了太平軍起事;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軍攻占南京,並定為太平天國國都,與清王朝對峙十一年,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反抗者對蕩寇志的批判。
據其子俞龍光所稱,蕩寇志草創於道光六年(西元一八二六年),寫成於道光二十七年(西元一八四七年),歷時近二十二年,經俞龍光修飾後,咸豐三年刻印於南京,並以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古月老人之序,題曰結水滸傳。
小說故事承接金聖歎偽作水滸傳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驚惡夢續起,並有結子一回。小說以陳希真父女為中心,寫了陳希真、雲天彪及張叔夜征討梁山,擒殺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的故事。作者認為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中,七十回以後的內容,包括梁山受招安、征方臘事,係羅貫中偽造。他在第七十一回卷頭語中明白地說:「乃有羅貫中者,忽撰出一部後水滸(案:指水滸後五十回)來,竟說得宋江是真忠真義,從此天下後世做強盜的,無不看了宋江的樣,心裏強盜,口裏忠義,殺人放火也叫忠義,打家劫舍也叫忠義,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義。看官你想,這喚做什麼說話?真是邪說淫辭,壞人心術,貽害無窮。……因想當年宋江並沒有受招安、平方臘的話,只有被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話。如今他既妄造偽言,抹煞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他指責羅貫中所作的七十回以後的水滸傳,完全是「邪說淫辭,壞人心術」,於是做起了翻案文章。他把水滸傳中忠義的代表宋江,變成了強盜的代表,又另外塑造了一個他理想中的「草野忠臣」陳希真,一個不與朝廷對抗、一心只為朝廷平叛的真忠義、假強盜。於是俞萬春就編造出了這樣一部真正偽言的結水滸傳,即蕩寇志來。其友徐佩珂吹捧說:「余友仲華俞君,深嫉邪說之足以惑人,忠義、盜賊之不容不辨,故繼耐庵之傳,結成七十卷光明正大之書,名之曰蕩寇志。蓋以尊王滅寇為主,而使天下後世曉然於盜賊之終無不敗,忠義之不容假借混朦,庶幾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矣。」(咸豐二年序)其實,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在「忠君」這一點上,與俞萬春並無不同。明代李贄忠義水滸傳序中說:「宋江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李贄的話是符合書中實際的。然而在俞萬春生活的時代裏,這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心態,是需要陳希真這樣的假強盜、真忠義,不與朝廷對抗,不與官軍對敵的「草野忠臣」,而把宋江等梁山好漢,寫成水滸傳中類同方臘那樣真造反的「強盜」,讓他們非死即誅,徹底覆滅。很明白,作者創造此書的主題思想就是「尊王滅寇」,在動蕩的年代裏,反對起事,也反對招安,必滅之而後快。這反映了反對變革,維持現存秩序的「僚佐」們,與統治者一樣,害怕群眾的恐懼心理,同時以「尊王」為號召,維護搖搖欲墮的封建王朝,美化行將滅亡的封建統治。總之,作為續書,他以正統的保守者思想作支撐,重新改寫了水滸後五十回的內容,杜撰了梁山被剿滅的情節,歪曲了梁山好漢的性格,增加了三十餘位反梁山的主將,用這樣的創作思想和藝術構思,以完結水滸傳。於是就產生了這部蕩寇志。
蕩寇志一反水滸的寫法,將魯達「聽潮而圓,見信而寂」的心已成灰的死法,處理為發狂而死。魯達對梁山感情最深,作戰最勇。而對梁山即將被張叔夜大軍摧毀的危難關頭,魯達更是奮勇殺敵,不肯收兵。宋江詫異道:「魯兄弟住居山寨有年,頗知紀律,今日為何幾番鳴金收他不回?」對梁山命運的深切關注,加上力疲神亂,使魯達著了瘋魔。他對宋江道:「兄長要殺上東京,灑家明日先殺張家兩個娃子,後殺張家老兒,一路打進東京,拆毀了金鑾殿,回來同你吃酒。」(第一百三十五回)他狂奔酣呼,大罵高俅,道:「今日灑家打殺了你,為民除害。你們這班狗才,教你們死個爽快!」又誤將忠義堂當作金鑾殿打得粉碎,大叫「灑家今番大事了也」而死。魯達的瘋狂,是他至死不改對奸臣昏君的痛恨、堅決造反到底的美好心靈的反映。
人間只要有不平,群眾的反抗就不會停止。梁山好漢爭取自由和做人權利的鬥爭精神,永遠值得歌頌,也是任何力量所鎮壓不了的。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評論蕩寇志說:「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采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事實確實如此。第八十四回評語中也說:「仲華深得耐庵之法矣。」並在評點中屢屢與水滸相比較。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描寫、結構安排等方面,明顯受到水滸的深刻影響,並刻意加以模仿,有的還是成功的。如第一百十五回唐猛擒豹,竟是武松打虎場景的再現,特別生動驚險,動人心魄;又第一百十回寫陳希真三打?州城,用真大義詐降,魏輔樑作內應,就學自「三打祝家莊」。某些情節描寫精細,獨俱匠心,頗有欣賞價值。如第九十六回鶯歌巷孫婆誘姦、第九十七回陰秀蘭偷情釀禍,情節寫得委婉曲折,人物形象鮮明。如陰婆子的刁鑽奸詐,孫婆子的貪財好利,紀二的陰險狡猾,戴春的好色愚蠢,姚蓮峰的品行不端,都刻畫得生動逼真,躍然紙上。其中的人情世態,風俗習慣,描寫得別出心裁,自然有致,不落俗套,可謂發之於「情」,宣之於「筆」,說明作者對市井生活的稔熟和觀察。又如小說開始寫陳希真父女出逃經過,從準備的路線、包袱、武器、馬匹、雇工等,描寫都很細膩,甚至可以說「巨細不遺」,但卻顯得異常真實。雇挑夫一段,先寫陳希真要挑夫簽個承攬合同,又叫鄰人作保,作法可謂「周密」;挑夫要調整包袱重量,兩頭均稱,以便省力,可謂「合理」;挑夫以為包袱過重,望多加些酒肉錢,亦屬「正常」等等,也反映了作者觀察生活的能力及筆力的成熟和老練。
語言上,蕩寇志突顯了文人創作的特點。作為文人作家的個人作品,結構精撰,描寫細膩;文字精煉,語言講究;多用典故,喜歡賣弄。他的文章是漂亮的。就文字和描寫而言,小說確實不乏精彩的對話和有個性的語言描寫,如陳希真與郭英娘子關於購馬的一段對話:
……希真又去看了看牙齒道:「你要賣多少銀子?」娘子道:「不瞞丈丈說,說價也由我討,只奴是本分人,老實說與你。先夫病重時,並不說落價錢,只對奴說:有識得的,便賤些也賣了;倘不遇?識貨的,情願沒艸料餓死了他,也不賣。前日有一個人勸我賣與湯鍋上,說倒有五七兩銀子,喫我發揮他一頓。今丈丈真個要買,隨你自說罷。」希真道:「我說不要怪。」娘子道:「何怪之有!」希真委實看得那馬合意得緊,便脫口說道:「與你一百兩足色紋銀,何如?」娘子暗驚道:「卻不道還值這許多,落得再要些。」便道:「一百兩少些,求加加。」希真道:「竟是一百二十兩。」娘子忖道:「再不賣時,恐決裂了。」……那娘子收了銀子,見牽了馬去,想起丈夫在日,止不住那腮邊的淚,雨點般的落下來。希真老大不過意。娘子道:「丈丈,還有副鞍韉,是這馬上的,你一發買了去罷,省得在奴的眼角頭。」希真去看了看,已是破的了。希真道:「鞍韉我便不要,你如果嫌馬價少,我再添你些罷。」說罷,去銀包裏又取出十兩來重的一錠銀與娘子。娘子那里肯收,說道:「奴自己?物傷心,並非嫌銀少。」(第七十三回)
這段對話,把一個想買馬,一個真賣馬,討價還價,雙方都關心馬的命運的那種心態、品格展露無遺。
就蕩寇志整體而言,它捨棄了水滸中那種詩詞相間的形式和通俗活潑的口語化、平民化語言,倒插入了大量公文書信,正發揮了作者的一技之長。但也使小說讀來沉悶。
小說有范辛來(金門)、邵祖恩(循伯)二人的大量夾批、夾注和回評。評點者應是作者的好友和知音,既熟悉作者的小說創作又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因此評點有的放矢,頗有見地。評語內容包括:說明作者的創作意圖,闡釋小說的內容和情節,剖析寫作手法、遣詞造句,評論人物得失等。回末評並對本回的章法結構、寫作技巧、人物關係等,做出了系統評論,並與水滸前傳比較,多所頌揚、阿諛之辭。評語與小說內容結合較緊密,特別是在評論中引用了大量歷史典故、古典詩詞,亦使評語內容較為充實。其中雖不少愚腐、平庸之筆,也不乏精彩見解,對讀者閱讀本書不無裨益。故我們保留了所有評語,未加任何刪節,以供讀者欣賞和研究。書中尚有作者自注五則(第七十六回、第一百二回、第一百二十回、第一百二十二回);其子龍光注九則(第八十二回、第一百十四回、第一百十八回、第一百二十二回、第一百二十五回、第一百二十七回),彌足珍貴。所有這些注解和評語,都為中國小說批評史提供了一份難得的資料。
本次整理此書,是以清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初刻本為底本,校以咸豐七年重刻本、光緒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煥文書局石印本,補齊了原刻本中的缺失和置誤文字。書中其他文字,一律未改,以存原貌。書中避諱之處多有,如康熙名玄燁,凡「玄武」、「玄黃」、「玄妙」,玄皆作「元」;道光名旻寧,「寧可」改成「凝可」,「徐寧」改成「徐凝」。又大刀關勝,因與關羽同姓,竟認為他是「強盜」,不配姓「關」,故改成「冠勝」等。我們一仍其舊,不加改動。
本書整理過程中的疏漏之處,祈請讀者批評指正。(節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