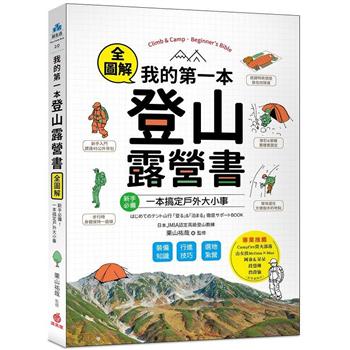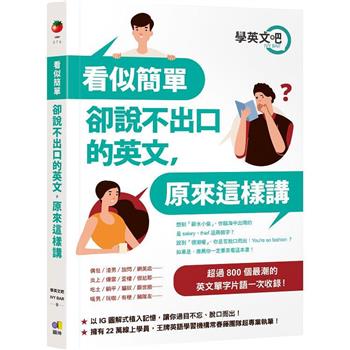嶺深道遠──懷念母親
去年十一月初旬自大陸回來,收到住在紐約的三弟莊喆的信,說:「《嶺深道遠》之展(在臺北市亞洲畫廊)適在媽媽仙逝後二日,是繼去年在歷史博物館的羅漢像主題展後以山水為主題之展。感念父母養育教化之恩,如今已近垂暮之年,這點成績就獻給他們二位吧。我這次回臺之行是別具意義,尤需向你詳說媽的人生最後一程:上月二十五日晨抵桃園機場,至臺北途中塞車,遂以手機撥給靈弟,當即知媽的心跳已降至最低,要我逕赴陽明醫院病房。到後與老母耳語,未幾心跳恢復幾至正常。難道不是知道我嗎?下午我去辦理諸事,囑咐小弟隨時通知我。次日六時即起身,因昨晚睡得不好。去大安公園晨走一小時,回程在和平東路上『丹堤咖啡』吃早餐,返師大學人招待所,得靈弟電話留言,稱媽媽已在清晨三時二十分仙逝了。」
媽媽可說是客死他鄉了。
而得知她老人家客死他鄉的我,卻是在她生我於斯的故鄉北京。我是在那裡旅遊作客投宿海淀區花園路北大醫學部第三院留學生公寓得知她老人家仙逝的消息。提供消息的是人在他鄉之鄉(臺灣臺北士林外雙溪洞天山堂)的四弟莊靈。
從他鄉的美國,暫回原本故鄉而今已是他鄉的我,得悉母親的去世當然是慘然的。而母親在他鄉(母親的故鄉是東北吉林)之他鄉的臺北駕鶴而去,似乎更其慘然了。尤其是駕鶴西歸的正確時刻是清晨三時二十分,人都在夢境中特別清寂的瞬間。
媽媽生我於北京的協和醫院。而我此次知悉她老人家的過世雖非人在該院,卻也是在與醫有關的北大(醫學部)三院,似亦可謂巧合了。媽媽大概至死還不知道,其實她生我於斯的協和醫院仍在,經過了驚天動地的災變後連名稱都未更改。但是,她老人家老年的病情已不容我知道她是否仍知。媽媽給予我生命,可是我此生第二度回到了已經易名的故鄉北京,而竟是在那兒得知她離鄉戰亂中南北奔走最終結束了坎坷一生的地方卻是海外孤島的臺灣。最令我感到遺憾與悲痛的是,她與我的永別,竟是當我人在他鄉既溫且生的故鄉茫茫然的睡夢裡。
喆弟真的比我幸運,因為他畢竟在媽媽謝世前趕到病榻與之耳語,讓媽媽「已減至最低的心跳幾至恢復正常。」而我沒有。誰會知道如果我有機會在她告別人世前跟她耳語,她是否會明張雙目,望著我,甚至會跟我說些什麼?
媽媽的遺體是在臺北「龍巖人本」公司二樓靈堂家祭過了,移送殯儀館「安順」廳(「安順」這名字也正好與抗戰期間我們家住貴州省的「安順」縣同名)後火化的。家祭的祭文,靈弟囑我執筆。我這樣寫:
母親大人申若俠女士,民國前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生於吉林,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凌晨三時二十分仙逝於臺北市立陽明醫院。享壽一百零一歲。
我們對於母親的體認,是從小在中日戰爭輾轉流亡各地的長期苦難歲月中感知的。她生育、教養了我們,這一份濃烈深厚的感情,彷彿風雨霜雪後的陽光,帶給了我們無限溫馨的盎然生意,也同時賦予了我們極大的庇佑。她一生勤儉自斂、忍勞、任怨,守法盡職,以身作則;這種身教,讓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得到恆定的支持與自信的滿足。
母親,您在臺灣辭世,遠離了故土,客死他鄉定是您老人家的一大憾事。您仙逝之日,除了三子、四子四媳,兩個孫女、孫女婿及他們的孩子隨侍在側外,長子(申)已故去多年,而二子因則以長期棲遲域外,未能親侍左右,這可說是您的第二大憾了。也惟其如此,我們的心情是無比悲慟哀傷的。
母親,我們將會將您的靈骨安葬在臺中大度山下,與父親同穴。這樣,或許您就不會感到太過孤單與寂寞了。
母親,請您安息吧!
去年十二月四日,我自北京返美再返臺參加靜宜大學邀約的「中國書畫藝文國際研討會」會後,曾至臺中大度山東海墓園祭掃先父母靈墓。那天天氣很好,陽光普照。墓碑的碑文已經新敷上金箔,顯得清晰美觀。我們供上了鮮花,行了禮。美麗、靈弟、夏生與我在燦爛陽光中離去。汽車自大度山馳往臺中市區的時候,我突然憶起了齊大姐邦媛教授在她的〈故鄉──父親齊世英逝世十年祭〉一文中,描寫她回到了東北齊老先生(我應稱世英老伯的)的故鄉時的思潮澎湃:「爬到丘頂,我沒有悲情,反似冷眼看著驚心動魄的土地大挪移。滄海、桑田,就在我眼前接壤。……沒有風,也沒有一片雲,天地默默。溫伯大夢(Rip Van Winkle)在山裡一睡二十年,回到村莊,鬢髮皆白,發現故鄉已經不是他的世界了。爸爸,我這樣回到了你曾魂牽夢縈而終老不能回歸的故鄉,也走了這麼遙遠的路。在臺灣淡水的山坡上,你已經知道了吧。」而我已經十多年未能與媽媽作口語溝通了。雖則我尚未去過母親的故鄉吉林,但我知道那也是跟邦媛大姐的父親的故鄉遼寧一樣,同在東北。而且是在更遠更北的東北。當然,那裡也肯定經過了驚心動魄的土地大挪移的。媽媽,您一定也已經知道了吧!
母親在臺度其四十五歲生日時,父親曾填寫了一首小詞〈西江月〉為賀。其中有這樣的幾句:「三十年來伴侶,八千里路同還。庭前玉樹自欣然,無忘松花江畔。」松花江畔即是伊的故鄉。我記得抗戰時期的〈流亡三部曲〉中有這樣兩句歌詞:「離別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媽媽不但是這樣,她更跨海到了臺灣。我在一九六四年離臺赴澳時,父親也曾寫了一詩給我:「水擊三千里,飛行一日航;叮嚀無別語,祇道早還鄉。」半世紀以來,「鄉」已數易,故鄉與他鄉,我已在其間來去行走過無數遍了。一九八五年楚戈曾為韓國的中國詩人學者許世旭教授的詩集《雪花賦》的出版,畫了該詩集的封面,是一個背負著「故鄉」流浪在渡頭的人。畫面上還題寫了世旭的詩句:「渡口的歲月,渡船的班次,還沒有認清。裝滿了的背包裡,都是發黃的信件。」母親的後半生,即使到她仙逝之時,我想她也都一直背負著那樣的一個包袱。但包袱中裝滿的或恐不是發黃的信件,而是移動的故鄉吧。
「移動的故鄉」,這有蒼涼之感的五個字使我想起了陶淵明的〈歸去來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陶氏「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他的歸去來是因為自認「誤落塵網中」,且有家鄉可歸。而母親呢?她自抗戰爆發,負家逃離生我於斯的故鄉北京,八千里路雲和月,就再也沒有回過她的故鄉了。對她來說,怕是千真萬確的「失鄉」了。「失」,不一定是「忘」。即使生前歸去,看見「忘不了」的鄉的「失去」,也是枉然。那份淒情,也定然令人鼻酸。
這樣吧,下回我返臺,媽媽,我一定會再至您的墓前,把齊豫女士的歌曲〈橄欖樹〉放給您聽:「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流浪……」
媽媽,您的故鄉是在海那邊白雲深處的遠方!
媽媽,您還記得嗎?大約三十年前,我在海外懷念感念和思念您時,曾經寫過一篇〈母親的手〉小文。在那篇文章裡,我說您有一雙至大完美的手,指甲上從未塗抹過蔻丹,也從未加過任何化妝品的潤飾。是那雙手,牽引我步入這繁雜險艱的人世。然後,它們撫我、護我、衛我、教我、育我、愛我、督我、導我、懲我、責我。您原本纖秀似玉的一雙手,在七七抗戰的砲火下經過風霜洗禮,竟脫胎換骨,變得厚實、堅強,足以應付任何苦難艱辛的巨掌了。我知道您不會游水,在冥域,隔了海峽,您會愁憂。但您不要怕,媽媽,請把您那雙至大完美的手給我,我會緊握了,無論是乘風或是浮海,帶您回到白山黑水的松花江畔──您終老不能回歸的故鄉去。
媽媽,一言為定啊!
(寄自加州)
二○○七年五月十三日美國《世界日報》
敬悼大愛摘星詩人紀弦
紀老走了。
從在報上見到消息之後,這幾日,他那直挺、有神、率真、活潑一似梧桐頂天立地大樹的身影,一直在我心中晃動著。壽高一百零一,這個數字令我想到許多有關的情事:縱貫加州南北的一○一號公路;聳立臺北市區內拔地而起的一○一大樓;和母親的壽數。一百,肯定是一個很有吸引力度、也同時是個很具權威感的數字。「百」上再加一,就更予人出類拔萃的領受了,那是一種不凡。
紀老生於一九一三年,我生於一九三三年,他是足足長我二十整歲的長者,尤其是他的身高更形成了對我這個後輩延頸仰望的「長者」形象。
我初聞紀弦其名,初知紀弦其人,還是我在臺北讀大學的青年時代。就在那年(一九五三),為當時寫新詩的現代派詩人揭纂大旗的人紀弦所創辦的《現代詩》季刊出版了。紀弦所倡導的現代詩,簡單地說是要以中國民族文化的認知為基礎,而捨棄傳統詩(即舊詩)的形式拘束及文字的襲用,譜寫全新的詩。傳統詩以「詩情」為本質,而現代詩以「詩想」為本質,前者重感性,後者則重知性,這樣的理論在當時引起詩壇傳統與創新的兩派大辯論。
對於以紀弦為代表的現代派新詩理論,說得最要約而又清楚的人,我認為是中國大陸編著《紀弦詩選》的藍棣之先生。他說:「紀弦認為舊詩與新詩是兩個傳統,兩座金字塔,舊詩早就達到它的頂點,再沒發展的餘地。今日寫新詩意味著一座全新的金字塔的建造……。從地面上看,確是兩個東西,而從地底深處看,它們自然是相通的。二者皆詩,都是文學,都是炎黃子孫所寫,為何不能相通呢?」依我個人的看法,新詩之所創,正如「詞」之出於「詩」,問題是不像「詞」之不同於「詩」,不但在體制格式上有其變化,更有了新名不叫「詩」,俗稱其為「長短句」。然則在文類上,詩、詞是屬於同一類的。藍棣之先生還說:「紀弦作為開創者的急進色彩和反傳統姿態,他的很多論點都在臺灣詩壇引起舉世矚目和曠日持久的論戰。」
我跟紀老相識相交,是在我們同客北加金山灣區棲遲天涯的時候。紀老是一個對整個宇宙有大愛的詩人,他曾說:「我的全靈全肉全生命,每一個細胞,每一根鬍子都充滿了無限的愛。」這簡直就跟「觀自在」一樣,他有摘星的癡狂,對於任何結緣的人與地,都深深愛著,純純愛著。
這種大愛,當然包括了對故鄉的愛。在〈懷鄉病〉一詩中,他寫道:「又是蒙古寒流南下的季節了,怎不令人想起小時候後花園中那些高大的梧桐樹而黯然神傷呢?」在〈茫茫之歌〉中又寫道:「呵!就在你茫茫的那邊,那邊,我的故國也茫茫,我的家鄉也茫茫。」這種愛的無奈,似發自內心的箭,又反射回他的大愛心房,且看他的〈觀音山組曲〉:
總有一天 我要去
攀登黑龍江省佛山縣的觀音山
總有一天 我要去
看看位於廣州市北的觀音山
總有一天 我要到
南京市觀音門外的觀音山上去
紀老不經心地已道出了他「觀自在」的菩薩心懷。「自在」就是他的詩心呀!與紀老談說,其語言明朗宏闊,氣透丹田,有少年發言的激越和逼人的衝動,跟詩句一樣令人容煥、神搖、臆熱。
紀老走了。
想起李白詩句「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當我仰望夜空,但見繁星點點閃爍時,我知道星群中的某一顆,就是「紀弦星」,我依然會舉杯說:「紀老,祝你永遠快樂。」
(原刊於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站「詩人紀弦紀念專輯」)
懷念高克毅先生睿智諧趣的風格──記花旗二高之一
整理書房,先將一壁書架上的書冊加以齊劃調整;次之抽汰掉部分稍嫌欠端的文字善本;再把受到冷落怠慢的後期蒐藏(因書架空間有限,致無由體面舒身廁立他賢之旁,而竟長期散臥在他書頭上的大著加以扶正)分類歸檔羅列書林,足足花了兩個小時。當然,輕撫珍拭,吹去封面微塵等小事自也稍費時間。然縱使如此,較之吸塵、洗拭衣物、堆抱垃圾等日常瑣事雜務,究竟尚屬文化性的活動,也就樂此不疲了。
畢生鑽研中英語文的文化推手
整理書架案頭時,常會有大發現及突如其來的感懷:諸如對某書到手之經歷原已相忘,彷彿愧對老友故人,竟因疏待曠日,而遲遲握暄;某書失而復得(友人借去,再轉借第三者,未期我本人在原冊上的簽名及隨手識記竟遭塗抹一去,而不幸又偏偏自第四者手中還歸書主。歷經滄桑,大難餘生,重返酒蟹居書架之上歇息);某書承著者高誼雅贈,再次翻閱時,書在人亡,不勝欷歔……。而這次檢書見及喬志高(George Kao,中文姓名高克毅)先生贈書《灣區華夏》(Cathay by the Bay),便是屬於書在人亡的。
是書有子題曰《一九五○年代的金山華埠》(San Francisco Chinatown in 1950),一九八八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印象中可能是克毅先生生前最後一本英文著述了。該年六月二十一日,著者在書的扉頁上簽寫了「送給美麗—為我們兩人書畫合作留念」的字樣自美國東岸寄贈。美麗,是我妻小名,書贈給她而未贈給我,讀者可能覺得霧水一頭。我願意再補充說明一下。其實,在前面克毅先生簽贈的題寫底下,還有他謙遜地閃身一旁的簽名及我應在其左並列空留簽名處下方寫好的「同贈」二字。事情是這樣:一九八八年春間,克毅先生偕夫人訪問臺、港,道經金山(三藩市),專程來訪酒蟹居。承其美意,邀約我為其待出之《灣區華夏》一書設製封面(畫作)並為書之內容插圖。前此一年,我曾為楊明顯女士大著《長白山下的童話》(臺北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一書,遵出版社主持人岳母林海音女士旨令作插圖,大概克毅先生見及(或緣岳母大人內舉,讓我的「第三支筆」拋頭露面),遂作寵邀。初生之犢竟然不敢違命。克毅先生在贈書的題寫中說「為我們兩人書畫合作留念」,顯然是把我「抬舉」了。克毅先生極重視文字,為人又風趣,在贈書這樣的一樁小事上,竟也充分見證了他一貫睿智和諧趣的風格。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嶺深道遠的圖書 |
 |
嶺深道遠 作者:莊因 出版社: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6-29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42 |
中文書 |
$ 142 |
文學作品 |
$ 153 |
Literature & Fiction |
$ 162 |
小說/文學 |
$ 162 |
中文現代文學 |
$ 171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嶺深道遠
本書是作者集寫作晚期的部分散文,小品文及雜文的合集。內容側重憶往,及對人、事、物的即時雜感。
本書共分四輯。首輯「思親懷友憶故人」收錄作者緬懷母親及友朋之作,憶及曩昔相處的點滴,情意綿綿、真摯溫馨;次輯「書藝淺說」為作者論述中國文字的書寫技巧及藝術之美,希冀傳承中華文化的豐厚底蘊;第三輯「雜文」為作者對生活中習見之物事及現代社會景況,闡述其真知灼見,深入淺出、富含理趣;末輯「小品」則是作者以輕鬆詼諧的筆調,直抒其情志。現在讓我們細細品讀。
作者簡介:
莊因
1933年生於北京,1949年隨家遷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及研究所畢業。曾任教於澳洲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及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現已退休,定居美國。散文風格行文曉暢、詼諧幽默且寓意深遠。除寫作外,莊因先生亦兼善書藝及繪畫,深具知識分子的雅懷流風及對文化傳統的關注。著有《莊因詩畫》、《莊因詩畫(二)》、《八千里路雲和月》、《詩情與風骨》等十餘本著作。
TOP
章節試閱
嶺深道遠──懷念母親
去年十一月初旬自大陸回來,收到住在紐約的三弟莊喆的信,說:「《嶺深道遠》之展(在臺北市亞洲畫廊)適在媽媽仙逝後二日,是繼去年在歷史博物館的羅漢像主題展後以山水為主題之展。感念父母養育教化之恩,如今已近垂暮之年,這點成績就獻給他們二位吧。我這次回臺之行是別具意義,尤需向你詳說媽的人生最後一程:上月二十五日晨抵桃園機場,至臺北途中塞車,遂以手機撥給靈弟,當即知媽的心跳已降至最低,要我逕赴陽明醫院病房。到後與老母耳語,未幾心跳恢復幾至正常。難道不是知道我嗎?下午我去辦理諸事,囑咐小...
去年十一月初旬自大陸回來,收到住在紐約的三弟莊喆的信,說:「《嶺深道遠》之展(在臺北市亞洲畫廊)適在媽媽仙逝後二日,是繼去年在歷史博物館的羅漢像主題展後以山水為主題之展。感念父母養育教化之恩,如今已近垂暮之年,這點成績就獻給他們二位吧。我這次回臺之行是別具意義,尤需向你詳說媽的人生最後一程:上月二十五日晨抵桃園機場,至臺北途中塞車,遂以手機撥給靈弟,當即知媽的心跳已降至最低,要我逕赴陽明醫院病房。到後與老母耳語,未幾心跳恢復幾至正常。難道不是知道我嗎?下午我去辦理諸事,囑咐小...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思親、懷友、憶故人,是本書重點。而對母親的懷念,則又是重點的重點。所以,排在全書之首,以篇名「嶺深道遠」提升為全書書名,就是這個道理。中外皆一,除了極鮮少的例外,總地來說,為子女的都冠以父姓。可是在人生的過程中,父親除了投精成孕,培育一個人的生命到入世的全部歷程,多半都是母親獨力完成的。母親的愛與恩,恰如明月在天,輝散出平和、慧亮、溫暖和慈愛的光芒,不似太陽照射得使人螫痛,氣極敗壞,火躁甚至感受到壓力。感恩,從人性的角度出發,首先應該感的人就是母親。
「嶺深道遠」,不但是懷舊,也是作者對生活的一...
「嶺深道遠」,不但是懷舊,也是作者對生活的一...
»看全部
TOP
目錄
前言
第一輯 思親懷友憶故人
嶺深道遠──懷念母親 3
敬悼大愛摘星詩人紀弦 10
懷念高克毅先生睿智諧趣的風格──記花旗二高之一 14
懷念摯友高恭億──記花旗二高之二 27
追記「華癡」許世旭教授 35
第二輯 書藝淺說
淺說書之藝 43
如何學寫中國字 50
第三輯 雜 文
中國國歌再譜新聲芻議 61
臺北行──老漢歸國十一日鈔 71
十六羅漢尊者造像 96
假作真時真亦假 104
天地一沙鷗 109
舊事新談 114
盛事之嬰 118
晚 晴 123
食藝與食德 128
無字天書 135
漂泊的兒童 139
...
第一輯 思親懷友憶故人
嶺深道遠──懷念母親 3
敬悼大愛摘星詩人紀弦 10
懷念高克毅先生睿智諧趣的風格──記花旗二高之一 14
懷念摯友高恭億──記花旗二高之二 27
追記「華癡」許世旭教授 35
第二輯 書藝淺說
淺說書之藝 43
如何學寫中國字 50
第三輯 雜 文
中國國歌再譜新聲芻議 61
臺北行──老漢歸國十一日鈔 71
十六羅漢尊者造像 96
假作真時真亦假 104
天地一沙鷗 109
舊事新談 114
盛事之嬰 118
晚 晴 123
食藝與食德 128
無字天書 135
漂泊的兒童 139
...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莊因
- 出版社: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6-29 ISBN/ISSN:978957146168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8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