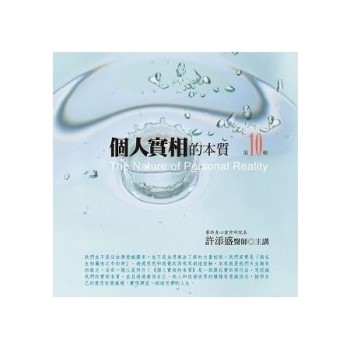本詩集是泰戈爾於191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原名是Gitanjali,意思是「頌歌的奉獻」,集內共收長短詩歌103篇,大多是對於最高自我(上帝)的企慕與讚美的頌歌,故書名譯作「頌歌集」。
集中充滿許多微妙而神祕的詩篇,其讚美上帝的各種手法和姿態,尤為高超奇特,讀之令人油然神往。譯者對印度文學鑽研深入,此版經多次潤飾、修改、校訂,終將難譯的泰戈爾頌神詩呈現讀者面前,值得一再品味。
本書特色
☆封面書名由一代名人羅家倫親筆題字
☆首創翻頁動態書眉,趣味十足
☆版面清新,搭配優美插圖,百看不厭
☆小開本設計,隨身一冊,輕鬆閱讀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頌歌集(五版)的圖書 |
 |
頌歌集(五版) 作者:泰戈爾-著;糜文開-譯 出版社: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7-0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94 |
中文書 |
二手書 |
$ 94 |
二手中文書 |
$ 95 |
Literature & Fiction |
$ 95 |
詩 |
$ 102 |
文學作品 |
$ 102 |
小說/文學 |
$ 114 |
世界詩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頌歌集(五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泰戈爾
自一九一三年以「頌歌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的詩風靡全球,不到十年,也引起了中國新文壇的狂熱,尤其在一九二四年他來華的前後,相關譯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泰翁的詩,雖然清新俊逸,但若不了解他奧妙哲學的全部,便不能有真切的理解。
譯者簡介
糜文開
江蘇無錫人。生於1907年,卒於1983年。印度國際大學哲學院研究。歷任香港新亞書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以及外交部專員, 駐印度、菲律賓、泰國大使館祕書,退休後任華岡印度研究所指導教授。作品多以論述、散文為主,由於駐留印度近十年,對於印度文學、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與深入的了解,致力於中印文化交流,著譯作品十餘種,為我國當代少數精研印度文化的學人。
泰戈爾
自一九一三年以「頌歌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的詩風靡全球,不到十年,也引起了中國新文壇的狂熱,尤其在一九二四年他來華的前後,相關譯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泰翁的詩,雖然清新俊逸,但若不了解他奧妙哲學的全部,便不能有真切的理解。
譯者簡介
糜文開
江蘇無錫人。生於1907年,卒於1983年。印度國際大學哲學院研究。歷任香港新亞書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以及外交部專員, 駐印度、菲律賓、泰國大使館祕書,退休後任華岡印度研究所指導教授。作品多以論述、散文為主,由於駐留印度近十年,對於印度文學、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與深入的了解,致力於中印文化交流,著譯作品十餘種,為我國當代少數精研印度文化的學人。
序
跋
泰戈爾這本詩集是一九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得獎作,原名Gitanjali,意思是「歌頌的奉獻」,集內共收長短詩歌一○三篇,大多是對於最高自我(上帝)的企慕與讚美的頌歌,所以譯作《頌歌集》。
一般說來,泰戈爾的作品,受《奧義書》的影響很大,其實他的詩是印度吠陀頌歌以來直到迦比爾(Kabir)、杜西陀(Tulsidas)以及十九世紀的托露達德(Taru Dutt)等人的集大成。《頌歌集》裡充滿著許多微妙的神祕的詩篇,他讚美上帝的各種手法和姿態,尤為高超而奇特,讀之令人油然神往。難怪歐美讀者,那麼狂熱地崇拜他的人,那麼醉心地喜愛他的詩。
古印度《奧義書》的學者們隱居山林,探索自我,他們在大自然的薰陶中體會宇宙的真理,達到了超脫的境界。同樣地,泰戈爾得力於《奧義書》的傳承,產生了他的森林哲學和清新詩篇。他在一本書的序文中,敘述《奧義書》的精神說:「雖則這最高自我是不可知、不可思議,但仍可通過自制和學問,用人的自我來實感它,因為兩者最後是一。這樣人從宇宙大力中解脫而成為神志的一部分了。」泰戈爾這本《頌歌集》,就是他「實感」的記錄。
可是泰戈爾對於《奧義書》的成就是不滿意的,他批評《奧義書》的學者們太偏於「理智」,太偏於「個人的完善」,說他們「通過愛與虔誠去接近真理的探索還不夠」。在這本《頌歌集》裡,我們可以看到泰戈爾是怎樣用他的愛與虔誠來通靈。上帝固崇高而威嚴,但最基本的是「愛」,所以他有時也把上帝視作朋友,甚或視作愛人。我國託物言志的詩人,寫給天子的詩往往以男女的愛情來比擬君臣的恩義,這裡更把這種比擬擴充到上帝身上去,因此他的頌神詩也更動人。
因為泰戈爾把握了「愛」,所以他體驗到的神志,使他非但要獲得「個人的完善」,同時也要謀求「社會的福利」,使他以隱士的身分,來做改造社會的工作。
於是在《頌歌集》裡他寫出這樣的詩句:
放棄這種禮讚的高唱和祈禱的低語吧!……睜開你的眼看看,上帝並不在你面前啊!
他是在犁耕著堅硬土地的農夫那裡,在敲打石子的築路工人那裡。無論晴朗或陰雨,他總和他們在一起,他的衣服上撒滿著塵埃。脫掉你的聖袍,甚至像他一樣走下塵土滿布的地上來吧!……
放下你供養的香和花,從靜坐沉思中出來吧!你的衣服變成襤褸或被染汙,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在勞動裡去會見他,和他站在一起,汗流在你額頭。
這是泰戈爾詩的終極意義。這是他對印度國家民族最大的貢獻。
我在印度國際大學時曾看到胡適之先生在泰翁六十四歲生日送給他的祝壽詩,題名「回向」,就是讚美他回向民間的。這詩為《胡適文存》及其他任何書中所無,現在一併抄錄在這裡,以供參考:
他從大風雨裡過來,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沒有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著山腳下,
想起了風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雲遮著的邨子裡,
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
他捨不得他們,
但他又怕山下的風和雨。
「也許還下雹哩?」
他在山上自言自語。
他終於下山來了,
向那密雲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泰戈爾的頌神詩是難譯的,這本集子的初譯稿,大部分完成於八年以前,後來譯全了曾經過兩次潤飾修改,長女榴麗也給我校訂了一遍,還是不能愜意。現在三民書局催著要印行,在百忙中整理出來,再仔細校閱修改了一遍。因為已印的泰翁詩集《漂鳥》、《新月》、《採果》三譯本,得到許多讀者的愛好,雖羞於露面,為答謝讀者的厚意,也只得暫時這樣出版了。
希望能給誦讀此書的人一些幫助,在書後寫上這幾句。
泰戈爾這本詩集是一九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得獎作,原名Gitanjali,意思是「歌頌的奉獻」,集內共收長短詩歌一○三篇,大多是對於最高自我(上帝)的企慕與讚美的頌歌,所以譯作《頌歌集》。
一般說來,泰戈爾的作品,受《奧義書》的影響很大,其實他的詩是印度吠陀頌歌以來直到迦比爾(Kabir)、杜西陀(Tulsidas)以及十九世紀的托露達德(Taru Dutt)等人的集大成。《頌歌集》裡充滿著許多微妙的神祕的詩篇,他讚美上帝的各種手法和姿態,尤為高超而奇特,讀之令人油然神往。難怪歐美讀者,那麼狂熱地崇拜他的人,那麼醉心地喜愛他的詩。
古印度《奧義書》的學者們隱居山林,探索自我,他們在大自然的薰陶中體會宇宙的真理,達到了超脫的境界。同樣地,泰戈爾得力於《奧義書》的傳承,產生了他的森林哲學和清新詩篇。他在一本書的序文中,敘述《奧義書》的精神說:「雖則這最高自我是不可知、不可思議,但仍可通過自制和學問,用人的自我來實感它,因為兩者最後是一。這樣人從宇宙大力中解脫而成為神志的一部分了。」泰戈爾這本《頌歌集》,就是他「實感」的記錄。
可是泰戈爾對於《奧義書》的成就是不滿意的,他批評《奧義書》的學者們太偏於「理智」,太偏於「個人的完善」,說他們「通過愛與虔誠去接近真理的探索還不夠」。在這本《頌歌集》裡,我們可以看到泰戈爾是怎樣用他的愛與虔誠來通靈。上帝固崇高而威嚴,但最基本的是「愛」,所以他有時也把上帝視作朋友,甚或視作愛人。我國託物言志的詩人,寫給天子的詩往往以男女的愛情來比擬君臣的恩義,這裡更把這種比擬擴充到上帝身上去,因此他的頌神詩也更動人。
因為泰戈爾把握了「愛」,所以他體驗到的神志,使他非但要獲得「個人的完善」,同時也要謀求「社會的福利」,使他以隱士的身分,來做改造社會的工作。
於是在《頌歌集》裡他寫出這樣的詩句:
放棄這種禮讚的高唱和祈禱的低語吧!……睜開你的眼看看,上帝並不在你面前啊!
他是在犁耕著堅硬土地的農夫那裡,在敲打石子的築路工人那裡。無論晴朗或陰雨,他總和他們在一起,他的衣服上撒滿著塵埃。脫掉你的聖袍,甚至像他一樣走下塵土滿布的地上來吧!……
放下你供養的香和花,從靜坐沉思中出來吧!你的衣服變成襤褸或被染汙,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在勞動裡去會見他,和他站在一起,汗流在你額頭。
這是泰戈爾詩的終極意義。這是他對印度國家民族最大的貢獻。
我在印度國際大學時曾看到胡適之先生在泰翁六十四歲生日送給他的祝壽詩,題名「回向」,就是讚美他回向民間的。這詩為《胡適文存》及其他任何書中所無,現在一併抄錄在這裡,以供參考:
他從大風雨裡過來,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沒有風和雨了。
他回頭望著山腳下,
想起了風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雲遮著的邨子裡,
忍受那風雨中的沉暗。
他捨不得他們,
但他又怕山下的風和雨。
「也許還下雹哩?」
他在山上自言自語。
他終於下山來了,
向那密雲遮處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們受得,我也能受!」
泰戈爾的頌神詩是難譯的,這本集子的初譯稿,大部分完成於八年以前,後來譯全了曾經過兩次潤飾修改,長女榴麗也給我校訂了一遍,還是不能愜意。現在三民書局催著要印行,在百忙中整理出來,再仔細校閱修改了一遍。因為已印的泰翁詩集《漂鳥》、《新月》、《採果》三譯本,得到許多讀者的愛好,雖羞於露面,為答謝讀者的厚意,也只得暫時這樣出版了。
希望能給誦讀此書的人一些幫助,在書後寫上這幾句。
民國四十六年六月七日文開跋於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