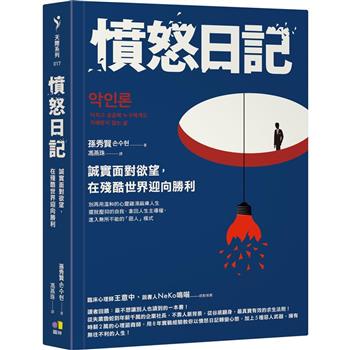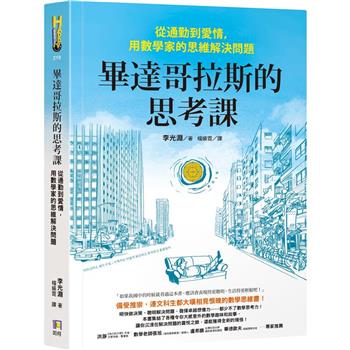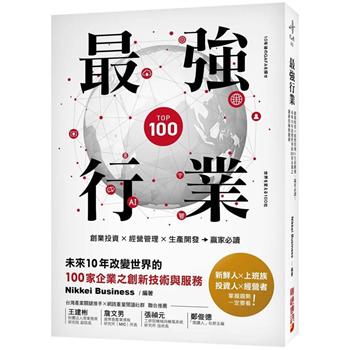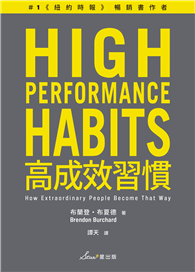《新月集》是泰戈爾以孩子之眼觀看這個世界的作品,在這本詩集中處處可見兒童般的想法及話語,滌淨我們久經世俗的心。兒時的童稚想法透過詩句再現,在韻律之中,發現「童心」的可貴。在〈玩具〉中,詩人說道:「孩子,我已忘記了專心致志於棒頭與泥餅的藝術。/我找出昂貴的玩具來,集合著一大批的金和銀。/你找到隨便什麼,你創造你的樂意的遊戲,我既浪費我的時間,又浪費我的精力,去找我永無獲得的東西。」不妨透過這些珍珠般的詩句,從孩子眼中,了解「慢活」的快樂吧!
本書特色
☆封面書名由一代名人羅家倫親筆題字
☆首創翻頁動態書眉,趣味十足
☆版面清新,搭配優美插圖,百看不厭
☆小開本設計,隨身一冊,輕鬆閱讀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新月集(七版)的圖書 |
 |
新月集(七版) 作者:泰戈爾-著;糜文開、糜榴麗-譯 出版社: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7-0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新月集(七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泰戈爾
自一九一三年以「頌歌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的詩風靡全球,不到十年,也引起了中國新文壇的狂熱,尤其在一九二四年他來華的前後,相關譯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泰翁的詩,雖然清新俊逸,但若不了解他奧妙哲學的全部,便不能有真切的理解。
譯者簡介
糜文開
江蘇無錫人。生於1907年,卒於1983年。印度國際大學哲學院研究。歷任香港新亞書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以及外交部專員, 駐印度、菲律賓、泰國大使館秘書,退休後任華岡印度研究所指導教授。作品多以論述、散文為主,由於駐留印度近十年,對於印度文學、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與深入的了解,致力於中印文化交流,著譯作品十餘種,為我國當代少數精研印度文化的學人。
泰戈爾
自一九一三年以「頌歌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的詩風靡全球,不到十年,也引起了中國新文壇的狂熱,尤其在一九二四年他來華的前後,相關譯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泰翁的詩,雖然清新俊逸,但若不了解他奧妙哲學的全部,便不能有真切的理解。
譯者簡介
糜文開
江蘇無錫人。生於1907年,卒於1983年。印度國際大學哲學院研究。歷任香港新亞書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以及外交部專員, 駐印度、菲律賓、泰國大使館秘書,退休後任華岡印度研究所指導教授。作品多以論述、散文為主,由於駐留印度近十年,對於印度文學、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與深入的了解,致力於中印文化交流,著譯作品十餘種,為我國當代少數精研印度文化的學人。
目錄
1 序
10 家
12 海邊
15 泉源
17 孩兒之歌
20 生命的小蕾
24 睡眠的偷竊者
28 來源
31 孩子的世界
33 領悟
35 誹謗
38 裁判
40 玩具
42 天文家
44 雪與浪
47 香伯花
49 仙境
53 放逐之地
58 雨天
61 紙船
63 水手
66 遙遠的彼岸
70 花校
72 商人
74 同情
76 職業
79 年長者
82 小大人
86 十二點鐘
88 寫作
91 可惡的郵差
94 英雄
100 終結
103 招魂
105 第一次的茉莉花
108 榕樹
110 祝福
112 禮物
114 我的歌
116 小天使
118 最後的交易
10 家
12 海邊
15 泉源
17 孩兒之歌
20 生命的小蕾
24 睡眠的偷竊者
28 來源
31 孩子的世界
33 領悟
35 誹謗
38 裁判
40 玩具
42 天文家
44 雪與浪
47 香伯花
49 仙境
53 放逐之地
58 雨天
61 紙船
63 水手
66 遙遠的彼岸
70 花校
72 商人
74 同情
76 職業
79 年長者
82 小大人
86 十二點鐘
88 寫作
91 可惡的郵差
94 英雄
100 終結
103 招魂
105 第一次的茉莉花
108 榕樹
110 祝福
112 禮物
114 我的歌
116 小天使
118 最後的交易
序
序
「瓶花妥帖爐煙定,覓我童心十六年。」龔定盦這兩句詩的意境,確是數千年中國詩史所罕有,我們這個民族是以敬老尚齒聞於世界的。我們是以「齒」、「爵」、「德」為三達德,以「年高德劭」、「黃項槁馘」為尊敬的對象;便是對於少年人,我們也希望他「老成」,對於兒童,則竟要鼓勵他「弱不好弄」。「童心」在人是嘲笑的批評,在文學上則從來搜不出這麼個辭彙。勉強說來,唯「稚氣」、「天真」有依稀近似處,但誰都知道前者是我們文學上不可容忍的缺點,後者與「童心」還有莫大距離。
據說動物的記憶力是極薄弱的,動物而愈下等,則記憶亦愈劣。蝴蝶雖是美麗生物,但牠也只算是下等生物。牠生長的過程又遠比人類來得繁複。人一出母胎,便一路生長上去,而蝴蝶則要經過毛蟲、蛹、成蟲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使蝴蝶生命截然分而為三,不相連續。我敢同你打賭:即使蝴蝶中間有記憶力最強的,當牠飛舞花叢,栩然自得之際,決記不起牠自己過去做毛蟲和蛹時的生活。不但全部記不起,模糊恍惚的影子都不會有。
所以,蝴蝶儘管文彩輝煌得可愛,牠始終只是個可憐的昆蟲!
但是,我又敢同你打賭:你是萬物之靈的人類,你自嬰孩發展而為成人,自成人成熟而為中年老年。成人以下的三個階段,你也許記憶得相當清楚,那嬰孩的階段,模糊恍惚的影子也許有—這確是我們萬物之靈勝於昆蟲之處—可是你能把那些記憶,淋漓盡致一絲不走地表達出來,形容出來嗎?你能縮回你的生命,扭轉你的想像,倒流你無憂的歲月,恢復你天真爛漫的心情,以孩童的眼睛來觀察這繽紛多彩的世界,以孩童的耳朵來聽這萬籟共鳴的聲音,以孩童的口吻來說出你的驚奇、喜悅、恐懼、興奮、愛好嗎?我知道你一定會對我連連搖手,我辦不到,辦不到。尼閣德睦對耶穌說:人不能重入母腹而為嬰兒,你要我做的事,雖不至於像重入母腹之難,卻也差不多了。誰又能記得那毫無意義孩童時代的一切呢?即使記得,有什麼適當的辭彙、語法來寫述出來呢?
對呀,這件事果然不很容易,是以西洋童話家雖彬彬輩出,也只有安徒生、格林兄弟等幾個人稱為翹楚。在我們中國則點起亮亮的燈籠,打起明晃晃的火把找不出一個半個。為了這緣故,我們的兒童時代從來沒聽見過什麼國王、公主、仙女、巨人;我們的文學,也從來沒有什麼駕著駟馬金車馳騁天空的阿波羅,執著雙蛇棒帶領亡靈沿著銀河走入地府的赫梅士。因之我們也缺乏沉博絕麗,恢奇俊偉,像荷馬、魏琪爾所作的詩篇。我們民族的腦筋,自幼便被強撳在修齊治平的模子裡,鑄成了一副死板的型式。我們的文學是蒼白的、萎黃的、枯槁的、矯揉造作的、千篇一律程式化的,缺乏真純的趣味和青春的活力,也缺乏偉大的想像,和天馬行空、不受羈勒的創造天才。
因此,即以定盦先生而論,他也許能在瓶花弄影,爐煙裊裊的境界裡,重新覓得他那十六年前早經消逝的童心,但我們卻只能在他的詩詞中,體認他少年綺怨的幽咽,壯歲意氣的飛揚,暮年逃空的寂寞,表現童心的文字卻一個字也看不見。我想定盦先生或者要答覆我們道:這和隱士的山中白雲一樣,「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當然,這只是他解嘲的話,寫不出才是真實的形況。
印度這個國家民族的歷史也許比我們還古老得多,但他們雖也尊敬老人,卻並不希望少年老成,鼓勵兒童弱不好弄;反之,他們從古以來,便有無數禽獸擬人的童話,寫入典重的文字,竄入莊嚴的經典。他們又有兩部著名的史詩,一部是《羅摩耶那》,一部是《摩訶婆羅多》。印度人自兒童時代便讀起,一直讀到頭童齒豁尚有餘味。印度全民族不分貧富貴賤,不問男女老幼,沒有不知這兩部史詩的事跡和詩中英雄之作為的。這在兒童文學的寫作上,印度人所憑藉者比我們當然要豐富千百倍了。詩哲泰戈爾的《新月集》則更是印度這類文學裡提煉出來的精華,也可說是世界絕無僅有的一部傑作。他寫這部詩集對於印度的文學遺產,當然有所借重,但他若沒有那五個婉孌可愛的小天使和他那溫柔嫻淑的夫人,朝夕周旋,我想他還是寫不出這類好詩來的。你看《新月集》這部詩,泰戈爾真的走回了他自己的孩童時代,以純粹兒童的官感、心靈來認識這世界,歌唱這世界,讚頌這世界。現在請你且讀以下的詩句:
母親,我真正相信花兒是到地下上學去的。
他們把門關著讀書,若是他們要未到時間就出來玩耍,他們的教師就要叫他們立壁角的。
當雨季到來,他們就放假了。
森林的枝條相擊,在野風中葉子發沙沙聲,雷雲們拍著他們巨大的手,花朵孩童們就衝出來了,穿著粉紅、鵝黃與雪白服裝。(〈花校〉)
巷裡黑暗而寂寞,街燈站在那裡像一個巨人,他的頭上有一隻紅眼睛。(〈職業〉)
這完全是孩童的癡話,然而卻是充滿著大人們永遠自愧不如的想像力的癡話。
我個人所喜愛的是〈孩兒之歌〉、〈睡眠的偷竊者〉、〈誹謗〉、〈雲與浪〉、〈香伯花〉、〈商人〉、〈英雄〉那幾首,不過說句老實話,《新月集》的四十首詩內容雖各殊,卻有同等的價值。泰戈爾在這閃著琥珀色奇光的兒童王國裡設了一席盛宴,歡迎任何人的參加。惟一條件是要你把那件滿沾「世途經歷」之灰塵的長袍,脫卸在這王國的大門之外,帶著一顆赤裸的「童心」進去!
蘇雪林
「瓶花妥帖爐煙定,覓我童心十六年。」龔定盦這兩句詩的意境,確是數千年中國詩史所罕有,我們這個民族是以敬老尚齒聞於世界的。我們是以「齒」、「爵」、「德」為三達德,以「年高德劭」、「黃項槁馘」為尊敬的對象;便是對於少年人,我們也希望他「老成」,對於兒童,則竟要鼓勵他「弱不好弄」。「童心」在人是嘲笑的批評,在文學上則從來搜不出這麼個辭彙。勉強說來,唯「稚氣」、「天真」有依稀近似處,但誰都知道前者是我們文學上不可容忍的缺點,後者與「童心」還有莫大距離。
據說動物的記憶力是極薄弱的,動物而愈下等,則記憶亦愈劣。蝴蝶雖是美麗生物,但牠也只算是下等生物。牠生長的過程又遠比人類來得繁複。人一出母胎,便一路生長上去,而蝴蝶則要經過毛蟲、蛹、成蟲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使蝴蝶生命截然分而為三,不相連續。我敢同你打賭:即使蝴蝶中間有記憶力最強的,當牠飛舞花叢,栩然自得之際,決記不起牠自己過去做毛蟲和蛹時的生活。不但全部記不起,模糊恍惚的影子都不會有。
所以,蝴蝶儘管文彩輝煌得可愛,牠始終只是個可憐的昆蟲!
但是,我又敢同你打賭:你是萬物之靈的人類,你自嬰孩發展而為成人,自成人成熟而為中年老年。成人以下的三個階段,你也許記憶得相當清楚,那嬰孩的階段,模糊恍惚的影子也許有—這確是我們萬物之靈勝於昆蟲之處—可是你能把那些記憶,淋漓盡致一絲不走地表達出來,形容出來嗎?你能縮回你的生命,扭轉你的想像,倒流你無憂的歲月,恢復你天真爛漫的心情,以孩童的眼睛來觀察這繽紛多彩的世界,以孩童的耳朵來聽這萬籟共鳴的聲音,以孩童的口吻來說出你的驚奇、喜悅、恐懼、興奮、愛好嗎?我知道你一定會對我連連搖手,我辦不到,辦不到。尼閣德睦對耶穌說:人不能重入母腹而為嬰兒,你要我做的事,雖不至於像重入母腹之難,卻也差不多了。誰又能記得那毫無意義孩童時代的一切呢?即使記得,有什麼適當的辭彙、語法來寫述出來呢?
對呀,這件事果然不很容易,是以西洋童話家雖彬彬輩出,也只有安徒生、格林兄弟等幾個人稱為翹楚。在我們中國則點起亮亮的燈籠,打起明晃晃的火把找不出一個半個。為了這緣故,我們的兒童時代從來沒聽見過什麼國王、公主、仙女、巨人;我們的文學,也從來沒有什麼駕著駟馬金車馳騁天空的阿波羅,執著雙蛇棒帶領亡靈沿著銀河走入地府的赫梅士。因之我們也缺乏沉博絕麗,恢奇俊偉,像荷馬、魏琪爾所作的詩篇。我們民族的腦筋,自幼便被強撳在修齊治平的模子裡,鑄成了一副死板的型式。我們的文學是蒼白的、萎黃的、枯槁的、矯揉造作的、千篇一律程式化的,缺乏真純的趣味和青春的活力,也缺乏偉大的想像,和天馬行空、不受羈勒的創造天才。
因此,即以定盦先生而論,他也許能在瓶花弄影,爐煙裊裊的境界裡,重新覓得他那十六年前早經消逝的童心,但我們卻只能在他的詩詞中,體認他少年綺怨的幽咽,壯歲意氣的飛揚,暮年逃空的寂寞,表現童心的文字卻一個字也看不見。我想定盦先生或者要答覆我們道:這和隱士的山中白雲一樣,「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當然,這只是他解嘲的話,寫不出才是真實的形況。
印度這個國家民族的歷史也許比我們還古老得多,但他們雖也尊敬老人,卻並不希望少年老成,鼓勵兒童弱不好弄;反之,他們從古以來,便有無數禽獸擬人的童話,寫入典重的文字,竄入莊嚴的經典。他們又有兩部著名的史詩,一部是《羅摩耶那》,一部是《摩訶婆羅多》。印度人自兒童時代便讀起,一直讀到頭童齒豁尚有餘味。印度全民族不分貧富貴賤,不問男女老幼,沒有不知這兩部史詩的事跡和詩中英雄之作為的。這在兒童文學的寫作上,印度人所憑藉者比我們當然要豐富千百倍了。詩哲泰戈爾的《新月集》則更是印度這類文學裡提煉出來的精華,也可說是世界絕無僅有的一部傑作。他寫這部詩集對於印度的文學遺產,當然有所借重,但他若沒有那五個婉孌可愛的小天使和他那溫柔嫻淑的夫人,朝夕周旋,我想他還是寫不出這類好詩來的。你看《新月集》這部詩,泰戈爾真的走回了他自己的孩童時代,以純粹兒童的官感、心靈來認識這世界,歌唱這世界,讚頌這世界。現在請你且讀以下的詩句:
母親,我真正相信花兒是到地下上學去的。
他們把門關著讀書,若是他們要未到時間就出來玩耍,他們的教師就要叫他們立壁角的。
當雨季到來,他們就放假了。
森林的枝條相擊,在野風中葉子發沙沙聲,雷雲們拍著他們巨大的手,花朵孩童們就衝出來了,穿著粉紅、鵝黃與雪白服裝。(〈花校〉)
巷裡黑暗而寂寞,街燈站在那裡像一個巨人,他的頭上有一隻紅眼睛。(〈職業〉)
這完全是孩童的癡話,然而卻是充滿著大人們永遠自愧不如的想像力的癡話。
我個人所喜愛的是〈孩兒之歌〉、〈睡眠的偷竊者〉、〈誹謗〉、〈雲與浪〉、〈香伯花〉、〈商人〉、〈英雄〉那幾首,不過說句老實話,《新月集》的四十首詩內容雖各殊,卻有同等的價值。泰戈爾在這閃著琥珀色奇光的兒童王國裡設了一席盛宴,歡迎任何人的參加。惟一條件是要你把那件滿沾「世途經歷」之灰塵的長袍,脫卸在這王國的大門之外,帶著一顆赤裸的「童心」進去!
蘇雪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