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王星琦
一
竇娥冤是元代偉大的戲曲作家關漢卿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古典悲劇中的典範之作。
關於關漢卿的生平事跡,相關的文獻記載零星有一些,然往往語焉不詳,甚至是互相齟齬。前輩與時賢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經考辨求索,反覆推論,可大體上勾勒出這位偉大戲劇家一生戲劇活動的基本情況。
元以後有關關漢卿生平事跡的記載,主要有以下七條:
一、元鍾嗣成錄鬼簿卷上:「關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已齋叟。」(曹楝亭刻本)
(案:天一閣刻本、說集本、孟稱舜刻本「尹」均作「戶」。)
二、熊自得析京志名宦傳:「關一齋,字漢卿,燕人。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為一時之冠。是時文翰晦盲,不能獨振,淹于辭章者久矣。」(永樂大典卷四六五三天字韻引)
三、邾經青樓集序:「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流連光景。」
(案:說集本無「而金之遺民」五字。)
四、楊維楨鐵崖古樂府宮詞:「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弦。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
五、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八十:「關漢卿,號已齋叟,大都人。金末為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好談妖鬼,所著有鬼董。」
六、清乾隆新修祁州志卷八紀事關漢卿故里:「漢卿,元時祁州之任仁村人也。高才博學,而艱于遇。因取會真記作西廂以寄憤,脫稿未完而死,棺中每作哭泣之聲。……此言雖云無稽,然任仁村旁有高臺一所,相傳為漢卿故宅。」
七、邵遠平元史類編卷三十六文翰傳:「關漢卿,解州人。工樂府,著北曲六十種。」
首先要辨明的是關氏的名字。漢卿既是其字,那他的名又是什麼呢?張月中先生根據實地考察,在今河北省安國縣一處橋頭碑上發現了「關燦捐銀五十兩」的碑文,遂著文稱:「『燦』即盛明之意,而天地間最負盛明的莫過於銀河了,銀河即天河,在文言中就是『漢』,也稱雲漢、銀漢和星漢。『卿』在人名中與『瑞』相連,即表吉祥之意,如與他字連用即表尊敬,並無實際意義。如此,『漢卿』的實際意義就是『漢』;名『燦』字『漢卿』完全符合我國傳統的名、字緊密相關的常規。關漢卿名燦,已無可置疑。」
案:曹孟德步出夏門行觀滄海中有「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句,可資補為注腳。至於漢卿之號,已齋、一齋、已齋叟,皆因祁州關漢卿故宅北院有座「一齋樓」而得。「一」通「乙」,乙、已又音同形似,通用自不在話下。如此,己、巳則只能是誤刻訛傳了。結論是關氏名燦,字漢卿,號一(已)齋。
張月中先生還通過實地考察與辨析,指出祁州志中漢卿為「祁州任仁村人」中的「任」字,係「伍」字之誤,這也是無可置疑的 。漢卿的故里為祁州(今河北省安國縣)伍仁村人,已是關漢卿研究領域的共識。解州(今山西省解縣)當為關漢卿的祖籍(或曾客居於解州),其重要戲劇活動在大都,晚年歸於伍仁村故里,並終老於此。「燕人」說顯然是一種泛指。
此外,還有一個究竟是「太醫院尹」還是「太醫院戶」的問題,各家意見尚未取得一致。筆者傾向於前者是,後者非。關漢卿家族宋金時既是祁州名醫門第,與太醫院的往來自是密切,世襲相承,在民間稱之謂「太醫院尹」,也只是一種泛稱,不必以當時官制中是否有此職官強為說解。錄鬼簿為非官方著作,取了民間習慣稱謂也是很自然的事。這樣一來,也可以解釋何以析京志中將其列入「名宦傳」中了,同時也可以解釋何以關漢卿劇作中經常出現懸壺施術以及岐黃藥理之事了。
因上述片斷記載中提及的「金之遺民」、「大金優諫」以及「金亡不仕」等說法,遂引出了關漢卿生卒年斷限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各家亦歧見疊出,眾說紛紜。羅忼烈先生曾按照各家所定的年代先後為序,概括為九種說法,現摘錄如下:
一、生於一二一○年(金大安二年)左右,卒於一二八○年(元至元十七年)左右趙萬里先生說,見一點補正。
二、約生於一二一○年(金大安二年)左右,約卒於一二九八至一三○○年(元大德二年至四年)之間鄭振鐸先生說,見關漢卿我國十三世紀偉大的戲曲家。
三、生年至遲當在一二一四年(金貞祐二年)之前,卒年至遲當在一三○○年(大德四年)之前亦鄭振鐸先生說,見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四十六章第五節。
四、生年約在一二三○年(金正大七年),卒年在一三○○年(大德四年)以後胡適先生說,見再談關漢卿的年代。
五、生於一二二四年(金正大元年)左右,卒於一三○○年(大德四年)左右吳曉鈴先生說,見再論關漢卿的年代。
六、生卒年代約在一二二五年(金正大二年)至一三○○年(大德四年)之間王季思先生說,見談關漢卿及其作品〈竇娥冤〉和〈救風塵〉。
七、生年約在一二二七年(金正大四年)以後,卒年在一二九七年(元貞三年、大德元年)以後亦王季思先生說,見關漢卿和他的雜劇。
八、生於一二四○年(蒙古太宗十二年)左右馮沅君女士說,見古劇說匯才人考:關漢卿的年代。文中不提卒年。
九、生於一二四一年至一二五○年(蒙古乃馬真后元年至海迷失后三年)之間,卒於一三二○年至一三二四年(延祐七年至泰定元年)之間孫楷第先生說,見關漢卿行年考。
如同羅忼烈先生所言:「由於文獻不足徵,各人的講法表面上雖然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其實仔細考察,也都各有疑竇,只有卒於大德初年以後這一點比較確實,一般被接受。」 之所以大家都不懷疑漢卿卒年在大德初年以後,乃因漢卿寫過十首〔雙調‧大德歌〕,其中末曲寫道:「吹一個,彈一個,唱新行大德歌。」這「新行」的〔大德歌〕顯然為漢卿晚年的作品,而且,「很可能是關氏創製的。今存元人小令,未發現其他曲家寫過〔大德歌〕」 。為了避免繁瑣考證,筆者這裏徑直取王季思先生說,即上列第六、七種說法,因為如此,「金之遺民」、「大金優諫」等記載方能解釋得通,亦即漢卿金亡時(一二三四)只是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所謂「遺民」、「優諫」以及「金亡不仕」等,也只能是一種模糊的說法。
至此,我們可以綜合各家之說,將關漢卿的生平事跡,作一個簡要的結論:關燦,字漢卿,號一齋,亦作已齋,晚署已齋叟,以字行。元祁州(今河北省安國縣)伍仁村人。約生於金哀宗正大二年(一二二五)前後,卒於元成宗大德四年(一三○○)左右。他是一位高壽的作家,享年在八十歲上下。其祖籍當為解州(今山西省解縣),抑或曾客居過解州。他的重要戲劇活動多在大都(今北京),晚年歸於伍仁村故里,並終老於此。關漢卿曾與在大都活動的一些雜劇作家白樸、趙子祥等組織過「玉京書會」,致力於雜劇的創作演出活動,是多才多藝的典型「書會才人」。他精通各種民間技藝和舞臺藝術,有時也「躬踐排場,面敷粉墨」,親自登臺串演。由於關氏家族宋金以來與太醫院聯繫緊密,祁州又是北方藥材重要集散地,漢卿當亦通醫術,這從他雜劇作品中的描寫不難領略到。漢卿一生所作雜劇多達六十餘種,為諸家之冠。今存十八種(其中個別作品是否屬關作,學術界尚有不同看法)。因漢卿入元之後不屑仕進,長期廣泛接觸社會底層,故其雜劇創作題材多樣,往往能深刻反映當時社會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對民生疾苦和社會的不公平多有揭露,對下層婦女的社會地位和命運遭遇,尤為關注,並寄予深切的同情。此外,歷史人物、民間傳說等,也是關劇常見的題材。他的優秀雜劇作品竇娥冤、救風塵、單刀會等,均被後人改編成各種地方戲曲,廣泛流傳。關漢卿雜劇的曲詞渾樸自然,生動凝煉,被視為元前期本色派的典範;在情節安排和人物塑造方面,關劇以曲折跌宕和鮮明生動見長,適於舞臺演出,表現出「當行」的特色。除雜劇創作之外,關漢卿兼擅散曲,今存小令四十餘首,套數十餘套,風格以潑辣豪放為主。元人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韻中將關漢卿與鄭德輝、白樸、馬致遠相提並論,列為四大家之首。
二
竇娥冤雜劇的題目正名為:「秉鑒持衡廉訪法,感天動地竇娥冤」一般都認為,它與單刀會均為漢卿晚年的作品,當作於杭州。「劇中為竇娥平反冤獄的清官,是竇娥的父親竇天章,官為肅政廉訪使。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二月,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知本劇作於此後」 。徐沁君先生則認為,竇娥冤創作年代還要向後推:「本劇第三折竇娥在刑場發出三大誓願,第三誓願是:『做甚麼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為東海曾經孝婦冤。如今輪到你山陽縣。』元代山陽縣為淮安路治所。淮安路(及揚州等地)確有三年之旱。見元史成宗紀大德元年、二年、三年(一二九七一二九九)記載,災情甚為嚴重,屢次賑糧免租。劇中所言,絕非向壁虛造。因此,劇中揭出此事,對統治者提出控訴,才能產生『驚天動地』的力量。許多評論竇娥冤的文章,都引用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一三○三)紀事:『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贓汙官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這就是竇娥冤悲劇產生的時代背景。」 徐先生顯然是認為,此劇當作於大德年間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關漢卿「秉鑒持衡」,憤筆控訴,寫下了這血淚冤獄故事。正如題目正名所標示的那樣,竇娥冤的確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大悲劇,也的確當得起王靜安先生所讚嘆的那樣「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雜劇從竇娥幼年即遭遇困苦與不幸寫起,深刻地揭露並控訴了當時社會的腐朽與黑暗,真實而生動地揭示出一個善良女子在殘酷的社會現實面前,除了引頸受戮,任人宰割,竟別無選擇。「衙門自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作品通過一系列生動細緻的描寫,憤怒鞭撻了無心正法、草菅人命的封建官僚令人髮指的罪惡,同時滿腔熱情地歌頌了被壓迫、被殘害的市井婦女強烈的鬥爭精神和不屈的反抗性格。
竇娥冤雜劇所概括的社會生活是相當豐富的。從表面上看,孤立無援的寡居婆媳受到市井惡棍的欺侮凌逼,乃是劇本一個偶然的契機,然而它卻是在極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的展示中,透露出異常深刻的思想內涵。竇娥的含冤負屈,無端受刑直至慘遭殺戮,絕非通常意義上的婦女問題所能概括,亦非簡單的冤假錯案所致。她的三樁無頭誓願,源於漢書于定國傳和搜神記中的東海孝婦故事。關漢卿並非一味因襲「本事」的傳奇性記載,而是化腐朽為神奇,創造性地結合元代社會的嚴酷現實,展現了帶有總體性的、意味深長的廣闊社會悲劇畫卷。竇娥冤超越了時代,實質上是對自漢代以來,千百年來世世代代被侮辱被損害的弱勢民眾深重冤憤的昇華和凝煉。如此說,自然是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審視這個千古名劇的。事實上關漢卿在創作中,始終是扣緊元代社會現實的。他在劇本中向人們展示出所謂「覆盆不照太陽暉」的當時社會之種種黑暗:流氓惡棍的肆無忌憚,任意橫行;大小官吏們的貪贓枉法,草菅人命;弱勢的市民(特別是婦女)群體生命財產安全得不到保障;下層知識分子的窮困潦倒,為求生計不得不賣兒鬻女(竇娥去作童養媳,是變相的典賣)等等。所有這些,都在劇作家筆下得到了廣泛而深刻的藝術再現。可見越是真實地反映時代的作品就越具有普遍性。因而,將竇娥冤視為中國古典悲劇中思想與藝術都十分成熟的、成就極高的經典作品,是學術界無可爭議的共識。
要將如此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和如此深刻的思想蘊含,概括在一個固定體例的、篇幅不長的雜劇作品中,就必須對生活素材進行認真選擇、恰當剪裁和精心結構。關漢卿在竇娥冤創作中,表現出高超的組織戲劇結構的才能。首先是詳略得當,鋪敘自如。劇作家將幼年竇娥被父親送到蔡婆家抵債寫得極為簡略,放在「楔子」中一帶而過。第一折開始時一下子跳過十三年,我們從蔡婆婆和竇娥的自報家門中得知,端雲自到蔡婆婆家將小字改為竇娥。她三歲喪母,七歲離父,十七歲與蔡婆婆兒子成親,不上二年,丈夫害弱症死了。如今二十歲也。蔡婆婆與竇娥老寡對新寡,相依為命。第一折中寫蔡婆婆討債,賽盧醫賴債並妄圖害死她,恰為張老兒父子偶然撞破,賽盧醫倉惶逃遁。接著劇情迅速發展,引出張老兒父子逼迫蔡婆婆與竇娥婆媳成婚,竇娥堅決不從。第二折,劇情突轉,張驢兒企圖害死蔡婆婆,以便強行霸占竇娥,不料經張驢兒下了毒藥的羊肚兒湯被其父誤食,陰差陽錯,張老兒一命嗚呼,遂使戲劇矛盾複雜化、尖銳化。張驢兒要挾威逼,竇娥仍然誓死不從,於是氣急敗壞的張驢兒惡人先告狀,誣陷竇娥藥死公公,竇娥百般無奈,只能與張驢兒對簿公堂。楚州太守桃杌昏庸不察,冤判竇娥死罪,戲劇衝突進一步激化。
第三折是偉大悲劇的高潮,也是劇作家重彩濃墨、著意發揮的精彩絕倫之筆。這裏突出一個「冤」字,竇娥在臨刑前呼天搶地,怨憤逼人,對黑暗的社會現實作了「天問」式的血淚控訴。其中〔滾繡球〕一曲唱道:
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此等唱詞不用典故,不飾藻繪,直抒胸臆,明白如話,更由於情真意切,激越飽滿,給人以聲情並茂,酣暢淋漓之美。第三折中還極盡浪漫主義的幻想,以超現實的神異手法,描寫了竇娥刑前迸發而出的三樁誓願,以突出其冤深似海,更以三樁誓願奇蹟般應驗,昭示了冤情之深重足以感天地、泣鬼神,表現出劇作家戲路之寬廣、筆墨之奇崛,同時,也飽含著劇作家對主人公深切的同情。而官府坐視冤情,儘管天地動容卻不改原判,這一筆著實有力,它既從本質上揭露了「官吏每無心正法」的罪惡,又為第四折竇天章親臨為女兒昭雪平冤作了必要的鋪墊。劇作家暗喻明示,也只有竇娥生身父親做上「提刑肅政廉訪使」這樣的大官,冤獄始能昭雪。即使是如此,也還要竇娥死後冤魂一年不散,衝決官府門神戶尉的重重阻攔,顯靈於其父面前。這說明,在當時社會嚴酷的現實面前,沉冤大白幾乎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劇作家理想主義的一種幻想罷了,幻想背後則是陰慘慘的產生悲劇的時代。
三
竇娥冤藝術上最突出的成就,在於作者成功地塑造了竇娥這一典型化的悲劇形象。這個形象是古代戲曲小說作品中少見的例外。一個普通市井平民女子,命運已足夠不幸,偏又飛來橫禍,偶然中有必然性。她逆來順受,沒有招惹任何人,也沒有與任何人結下宿怨積仇,恭恭謹謹、寂寂寥寥、本本分分過著自己的苦日子。然而那暗無天日的社會卻不容她,乃至招來「身首不完全」的噩運。劇作家如此通過人物形象的遭際來揭露社會的窳敗和吏制的腐朽,真的稱得上是鞭辟入裏,一剮「一道血,一層皮」了。竇娥是那樣善良,那樣孝順而又與人無爭,當時社會連這樣一個弱女子都不能見容,其殘酷與腐敗真是令人髮指。劇作家如此敢於揭穿社會的瘡痍與毒瘤,作品豈能不深刻之至!第三折無疑是竇娥性格發展中由隱忍轉入反抗的關鍵之筆。劇作家在這裏通過竇娥反抗性格的展現,集中折射出當時民眾對黑暗統治的強烈憤懣情緒和不可遏止的抗爭精神。竇娥的呼天搶地和三樁無頭誓願,正是她性格突轉的顯著標誌。一個孤苦無助的弱女子,也只能以死去抗爭,以犧牲自己的個體生命去昭示自己的清白,從而喚醒自己也喚醒千千萬萬的民眾。在第二折中我們看到,善良的竇娥誤認為自己的「遭刑憲」是由於「不提防」,她之所以敢於同張驢兒去見官,是因為她對官府還不了解,或者說她還存在某種幻想,以為自己未做虧心事,便不怕三推六問。「大人你明如鏡,清似水,照妾身肝膽虛實」(〔牧羊關〕)。血淋淋的現實喚醒了她,使她在絕望中猛省,終於迸發出最後的呼喊,這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作為一個普通下層婦女所能做出的最強烈的抗爭。關漢卿層次清楚地揭示出竇娥反抗性格的形成脈絡,令人信服地寫出了竇娥性格發展的真實過程,遂使竇娥形象具有動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
至於蔡婆婆形象,或以為她放「羊羔兒利」(高利貸),家道殷實,不應視為底層婦女。第一折中竇娥唱道:
想當初你夫主遺留,替你圖謀,置下田疇,早晚羹粥,寒暑衣裘。滿望你鰥寡孤獨,無捱無靠,母子每到白頭。公公也,則落得乾生受。(〔青哥兒〕)
第一折尾曲〔賺煞〕中又唱道:
俺公公撞府沖州, 的銅斗兒家緣百事有。想著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張驢兒情受?
看來蔡婆婆丈夫的確留下不少家產。她自己也毫不掩飾:「家中頗有些錢財」但孤兒寡母,僅靠積蓄度日,只出不進,坐吃山空,怕是自有許多難處。況且元代放「羊羔兒利」幾成一種風氣,大有大放,小有小放,並非什麼了不起的事。打個近乎蹩腳的比方,猶如今天人們買股票一樣,因而不必在這一點上去苛求。蔡婆婆形象顯然是劇作家著意設計的,用以襯托竇娥形象,從而使竇娥形象更加鮮明的匠心所在。是對比,也是反襯,更是一種相映成趣:一軟弱,一剛強;一優柔寡斷,一斬釘截鐵;一遇事六神無主,一臨危不卑不亢。總之,劇作家以巧妙且渾化無跡的筆觸,將兩個人物都寫活了。不消說蔡婆婆的確是有些糊塗的,當竇娥質問婆婆「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時,蔡婆婆道:
孩兒也,你說的豈不是!但是我的性命全虧他這爺兒兩個救的。我也曾說道:待我到家,多將些錢物酬謝你救命之恩。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裏有個媳婦兒,道我婆媳婦又沒老公,他爺兒兩個又沒老婆,正是天緣天對!若不隨順他,依舊要勒死我。那時節我就慌張了。莫說自己許了他,連你也許了他。兒也,這也是出於無奈。
情急之下,竇娥又氣又恨,自然是搶白了婆婆一翻。蔡婆婆反覆強調的只是蒙人救命之恩,百般無奈:「我的性命,都是他爺兒兩個救的。事到如今,也顧不得別人笑話了。」又說:「那個是要女婿的!爭奈他爺兒兩個自家捱過門來,教我如何是好?」正是在這一來一往的對話中,兩個人物的性格層次分明地凸顯出來。事實上蔡婆婆亦被置於黑暗勢力的刀俎之上,同樣是一個受害者。說起來她的命運已夠不幸,先是中年喪夫,又痛失親子,婆媳倆老寡新寡相依為命,雖說家有積蓄,吃穿不愁,精神上的孤苦與愁悶是不言而喻的。及待索債不成險些送命,偏偏又遭遇強梁要挾逼迫,可謂禍不單行。她未失善良的心地,不僅免除了竇天章本利四十兩銀子的欠債,又格外送他十兩銀子和「些少東西」作為上朝取應的盤纏。童養媳制度的罪與不罪這裏姑且不論,在這個個案中,竇天章是不得已而為之,蔡婆婆亦不失憐憫之心,自有兩方便處,至少年幼不幸的竇娥有了個歸宿。總之,蔡婆婆是一個真實的、活生生的市井中市民婦女形象,透過這個人物形象,庶幾可以窺見元代市井生活中的一個側面。
張驢兒形象我們留待後文再談。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也是竇娥冤藝術上明顯的特色。前兩折基本上採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後兩折則馳騁浪漫主義的奇思妙想,且二者結合得相當完美。如此駕馭自如、渾融無跡的創作經驗,可視為中國古典主義戲劇中的一個範例,對後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此外,竇娥冤的曲詞、賓白都寫得老辣從容,自然本色。王國維曾列舉第二折〔鬥蝦蟆〕曲稱其「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為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至中葉以後,已罕覯矣。」並且說:「關漢卿一空依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 特別是第三折,寫得激情如火,氣氛如潮,遣詞用語如迅雷疾電,音調節奏似驟雨狂風,且不失當行本色,直入化境。就連插科打諢也用得極巧,於妙趣橫生之餘,閃現出冷峻的思致,大有所謂「黑色幽默」的味道。如昏官楚州太守桃杌上場時的一段科諢穿插,他但見了告狀的就連忙跪下,口稱衣食父母。劇作家以誇張、怪誕的手法,活畫出貪贓枉法的昏官嘴臉,不僅平添了無限機趣,活躍了場子,更增強了作品的諷刺與批判力量。這一忙中閒筆,不可輕易放過,須是仔細玩味之處。足見關漢卿是一位熟悉戲曲舞臺,筆墨靈動活潑的斫輪巨匠。
四
以上我們對竇娥冤雜劇的思想與藝術作了一些簡要的分析論述,主要著眼於作品在客觀上所給予我們的顯而易見的感受,或者說,是從作品社會性衝突的視角去審視的,即研究者基本上能夠取得共識的層面上展開探討的。然而,關漢卿不僅是一位古典主義的戲劇大師,更是一位近代精神啟蒙的先驅者。關劇的思想文化意蘊往往呈現出異常複雜的、多元並存且渾化無跡的情況。猶如詩歌有寄託,小說有複調,關漢卿戲劇作品的意蘊大多也並非是單一的、一望而知的。對竇娥冤的深層意蘊,長期以來,多有探微抉幽、開掘闡發者,有些見解可謂推陳出新,振聾發聵,足以啟迪後學。如郭英德先生就認為關漢卿在竇娥冤中,「只不過是把經濟剝削、政治壓迫作為悲劇的一種背景,一種偶然的機緣,來加以描繪的;而不是如我們所一廂情願地認為,作為悲劇的根源,悲劇的決定性因素」。他還進一步認為竇娥冤的戲劇衝突有三個層面,即社會衝突、道德衝突和意志衝突。郭先生指出:「關漢卿建立在傳統文明基礎上的樂觀自信精神,即相信古老而悠久的道德文明,毋庸置疑地是不可抗拒、不會毀滅的。傳統的道德文明,即使因為外族的入侵和別種文化的輸入而暫時蒙塵被難,但最終還是會光復、會發揚光大的。」其結論是:「關劇中潛藏的這種對傳統道德的懷舊情調和復古企望,是中華民族心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仍流動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血管中。而關劇所呈現給我們的對道德與現實兩難抉擇這種深沉的文化困惑,至今不也常常縈繞有識之士的心靈,促使他們進行不懈的文化探索麼?能給人長期的精神滋養和思想啟迪的作家是不朽的,關漢卿正是這樣的作家。」 這無疑是一個有價值的思路。說的雖是對關劇的總體認識,但也不失為探討個案如竇娥冤深層意蘊的一條途徑,甚至對整個元雜劇思想文化意蘊的把握,似亦具有普遍意義。
我們知道,元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使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背景變得異常複雜。一方面元代漢族士人呼喚承嗣接續漢民族傳統文化,對漢民族的宗法觀念與人倫思想自覺維護,著意張揚,對所謂「禮崩樂壞」和「世風日下」痛心疾首。因而文人劇作家普遍關注「秩序」的混亂問題,表達懲惡揚善的理想,渴望傳統人倫精神的回歸,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民族意識。另一方面,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既有碰撞又有交融,且草原文化為中原文化吹來清新的空氣,此後也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我們這裏更多的著眼於「碰撞」,乃是因為元雜劇作品,特別是前期作家的作品,確有特別強調漢民族傳統宗法觀念和人倫思想的傾向。在人情世態劇中這種傾向就更為明顯。如鄭延玉的看錢奴、武漢臣的老生兒、張國賓的合汗衫以及無名氏的漁樵記、貨郎擔等劇作,均屬此等。
在竇娥冤中,竇娥的家族觀念表現得非常突出,她不僅維護著公公的財產不被外姓人侵掠與「情受」,而且「家門」觀念根深蒂固。在張老兒誤食羊肚兒湯死後,她勸婆婆說:
不如聽咱勸你,認個自家晦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腳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恓惶淚。(〔鬥蝦蟆〕)
張家父子是外來闖入者,竇娥竭力抵禦著這突兀而來的無端侵擾,捍衛著自家的安全和利益。施叔青女士曾引用其老師俞大綱先生的話,來說明合汗衫雜劇的意外之意:「如合汗衫,把一個陌生人引了進來,卻造成了一家人妻離子散的悲劇。……中國人極端保守,從建築的結構就可以看出是十分防禦性的,農業社會十分封閉,對於外來的闖入者在恐懼之餘,多半不受歡迎,認為外來的力量具有侵略性,甚至足以造成摧毀一個村子、一個宗族的導火線,元雜劇合汗衫正是反映了中國人疑懼外來者的心態。」 此劇中的陳虎是「外來闖入者」,老生兒中的張郎也是,竇娥冤中的張家父子更是。從角色的名字也可以看出,虎、狼(郎)、驢兒,猛獸、畜牲也。其實看錢奴中的賈仁、貨郎擔中的張玉娥、魏邦彥以及一些劇作中符號化了的柳隆卿、胡子傳等,都有同樣的意味,這似乎可以看作是元雜劇作家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符號化了的「外來闖入者」形象,暗寓著劇作家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一種特殊的文化心態,其背後正是對傳統宗族觀念與人倫思想的追懷,潛藏著濃厚的民族意識。
宗族意識和人倫觀念是一個歷史的存在,它的形成與發展有著漫長的歷史文化淵源。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長處,一在倫理情誼,一在以是非觀代替厲害觀。又強調指出:「倫理秩序初非一朝而誕生。它是一種禮俗,它是一種脫離宗教與封建,而自然形成於社會的禮俗。……即此禮俗,便是後二千年中國文化的骨幹,它規定了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大體上一直沒有變。」 縱觀兩千年來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事實上宗族觀念與人倫思想既是封建統治者專制壓迫的核心思想,又是中華民族得以凝聚和綿延的精神支柱;它既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又是一種世俗化了的禮俗。它在正負背反以及超越性與局限性的兩重性中,呈現出錯綜複雜的情況。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的內涵和表現形態有著很大的不同;或者說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對它的認識與理解也有所不同。然而它總體精神一直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如果說在其他歷史時期特別強調它可能會有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那末在元代這個特殊的背景下,強化它以寄寓作家的一種特別的情懷,就另當別論了。這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一種特定的心理趨勢。元前期雜劇作家在草原文化的猛烈衝擊之下,起而以維護漢民族的宗法觀念與倫理思想為己任,意欲接續中原傳統文化,對所謂「綱常鬆弛」、「世風日下」的局面進行救贖,顯然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關漢卿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挺身站在最前沿的作家。
我們知道,中國人家與國往往是交相而稱,互文而用的,又常常是以天下觀代替國家觀,再以家族(庭)觀去實踐國家觀,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個人命運與家庭、民族利益融為一體,從而使「故園」與「故國」具有相通甚至是難以區別的意義。關於這一點,即便是外國學者也看得很清楚。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中寫道:「雖然家庭總是基本的社會組織,但這種情況在中國幾乎到了獨一無二的程度。中國的家庭是一個緊密組織起來的單位,致力於防備任何外界的官方或非官方的力量,以維護它的成員的利益。它大概還是下層階級對抗無限制剝削的唯一有力的保護者。……中國家庭不只是一個經濟的和社會的單位,同時也是一個宗教的和政治的單位。……在中國的大部分時期,普通人的宗教生活主要是照料他的家庭墳塋和祖先神靈的祈禱和供奉。作為一個政治單位,家庭執行紀律,並把它的某個成員的劣行看作是集體的恥辱。」 明乎此,庶幾可以讀懂何以竇娥不遺餘力地責備蔡婆婆,埋怨她輕許再嫁,亦可以明瞭「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背後的潛臺詞,更能悟出竇娥竭力維護公公遺產的心理依據。倘若再深入開掘一層,亦不難領略關漢卿的良苦用心。有如趙氏孤兒以「趙」氏隱喻趙宋王朝,老生兒以「劉」氏暗指劉漢天下,新生兒恰恰是恢復漢家天下的一個希冀的聯想 。關漢卿通過竇娥形象所要傳達的故國情懷和民族意識也是不言而喻的。總之,宋金元之交,呼喚重振漢民族宗族意識和人倫思想,可以看作是一股潮流即是使漢民族禮俗與文化免於淪喪的一種心理上的掙扎與努力,也可以看作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它是解讀元雜劇不可忽略的一個思維途徑,值得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說到宗法觀念和人倫思想,不能不涉及「孝」的問題。在竇娥冤中,更是無法迴避這個問題。說中國文化是孝的文化,從某種意義看可謂是一語破的。這是因為在五種倫常關係中,最重要的環節是家族關係,占了五倫的三種,即父子、夫妻、兄弟。而君臣關係、朋友關係乃是父子、兄弟關係的擴大與衍生。倘若再深入一層思考,父子關係更是宗法觀念和人倫思想之核心,它是血親與嫡傳,直接關係到宗族的繁衍與和諧。老生兒、趙氏孤兒中的隱喻與聯想,其根在此。竇娥冤的本事之一東海孝婦傳說,突出的正是一個「孝」字。關漢卿在劇本創作中,又著意突出了竇娥的孝順與善良,這不僅表現在桃杌要對蔡婆婆用刑時,竇娥挺身擔戴罪名,以及赴刑場時著公人走後街,擔心婆婆傷心。實際上她責備婆婆不應輕易再嫁不良之輩,力拒張驢兒挾迫、堅決維護家族財產不受侵犯等,也是孝。前者是對已故公公的孝,後者則是對家族的忠。劇作家正是在竇娥這種尚情無我精神的渲染中,流露出濃重的對傳統文化的追懷與呼喚,就中寄寓了對古老道德文明重新光昌的期望。說到底,張揚的無非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民族意識和文化尋根的情懷。在蝴蝶夢雜劇中,關漢卿的這種情懷似更為濃烈。當王家三兄弟為父復仇,打死惡霸葛彪後,王婆婆明知要吃官司,關鍵時刻,「這正是家貧也顯孝子」(〔天下樂〕)。她告訴三個兒子:「你合死呵今朝便死,雖道是殺人公事,也落個孝順名兒。」(〔醉中天〕)「你為親爺雪恨當如是,便相次赴陰司,也得個孝順名兒。」(〔柳葉兒〕)王婆婆心想,無非一命抵一命,「只不過一人處死,須斷不了王家宗祀,那裏便滅門絕戶了俺一家兒」(〔賺煞〕)。「孝」字在蝴蝶夢中幾乎貫穿了全劇,王婆婆意欲以己出的王三去抵命,亦見出有情無我的家族觀念根深蒂固。值得注意的是,王婆婆的為兒子申辯、探監,王家三兄弟爭相頂罪的描寫,由孝而悌,家族觀念和人倫思想在劇中融會貫通,尤為值得深味。在第二折中,包待制理清了案子的前因後果之後說:「似此三從四德可褒封,貞烈賢達宜請俸。」最後包待制以盜馬賊趙頑驢冒名頂替,償了葛彪之命。王家一門旌表,加官封賜。自然這是一個理想化了的結局,就中寄寓的恰恰是劇作家建立在傳統道德文明基礎上的樂觀精神與堅強信念。這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顯然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此外,學者們一般都認為,葛彪的身分是有影射之義的。他是「權豪勢要」,有的本子又稱其葛皇親,即使是所謂「平人」,也是蒙古平人。他口口聲聲打死人「只當房檐上揭片瓦相似」,其身分地位與「漢兒」不可同日而語。如此,關漢卿在蝴蝶夢中所流露出的民族意識,似亦不言自明了。關劇其他作品,或隱或顯,也都不同程度存在這種情況。
將蝴蝶夢與竇娥冤對讀發明,不難窺見關漢卿對劇作的良苦用心,其劇作中的深層意蘊非他,乃是一種深沉的傳統文化情結以及高屋建瓴的歷史觀照、心靈求索。正如利奧奈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所精闢論述的那樣:「我本人通常將文學情境視為一種文化情境,將文化情境視為精心設置的、重大的倫理問題之爭;這種倫理問題之爭與偶然獲得的『個人形象』有關,而個人存在之意象則與作者的寫作風格有關:在表明這一點之後,我感到我就可以自由地從我認為是最重要的問題開始作者的愛憎,他的意圖,他想要的東西,他想要發生的事。」 倘若我們將竇娥冤的戲劇情境及其戲劇衝突置於元代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中,再從倫理的層面深入發掘,關漢卿的愛憎、意圖以及他想要表達的思想等等,即他的命意題旨,庶幾可捫觸得到。
此外,筆者還注意到,不少的論者在探討竇娥形象時,都注意到了第一折中竇娥一出場所唱的曲詞,以為其中隱含著一個年輕寡婦難以言傳的性苦悶心理。我們不妨來看看這些唱詞:
〔仙呂‧點絳唇〕滿腹閒愁,數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混江龍〕則問那黃昏白晝,兩般兒忘餐廢寢幾時休?大都來昨宵夢裏,和著這今日心頭。催人淚的是錦爛熳花枝橫繡闥,斷人腸的是剔團圞月色掛妝樓。長則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悶沉沉展不徹眉尖皺;越覺的情懷冗冗,心緒悠悠。
接下來的一曲〔油葫蘆〕,也有「嫁的個同住人,他可又拔著短籌;撇的俺婆婦每都把空房守」句,看上去確有被壓抑的怨尤之意。然細細繹之,連著的幾曲要突出的仍然是孝。「我將這婆侍養,我將這服孝守,我言詞須應口」,此劇的情境在此不在彼。若言關漢卿自然流露出對筆下主人公的深切同情可,倘就這幾曲認定是著意要突出竇娥的性壓抑心理則非。不錯,「閒愁」在詞曲中往往有特定指義,這在柳永詞和西廂記中都不難找到佐證。竇娥是一個二十歲的寡婦,其寂寥與孤苦自不待言,劇作家懸想忖度,體味人情事理,替劇中人物設為內心獨白,純屬自然而然。誠如王世貞所言,曲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仿佛如生」(曲藻),如此而已。倘一味粘著於枝節,過度闡釋,難免陷入見木不見林的窘境。況且,在關劇中,同情婦女,特別是關注下層婦女的遭遇運命,乃是一貫的作風。只是在竇娥冤中,劇作家更有遙深的寄託,〔點絳唇〕等曲詞,也只是漢卿人道主義精神的自然流露。當然,大師看上去順情率性之筆,亦非可有可無,更非贅筆,它強化了全劇的悲劇性情調。帕克在他著名的美學原理中,曾以索福克勒斯筆下的安提戈涅為例,說明了類似描寫的意義:「在安提戈涅中,我們始終欽佩女主人公悲劇性的虔誠的勇氣,但是,在她臨終前,悲嘆了她虛擲的青春和美麗的時候,我們才感到這種犧牲需要多麼大的力量。也許有人認為,這種悲嘆是在描寫了堅韌不拔之後來描寫軟弱,因此是一個美中不足之處;我認為,詩句給人的印象恰恰相反,因為力量是用它所戰勝的事物來衡量的。」竇娥的悲嘆與安提戈涅略有不同,是在她捲入冤案、慘遭殺戮之前,然其意義卻大體相同。如此一個連連遭遇不幸的弱女子,黑暗的現實社會都不能容她,其殘酷與惡濁可想而知。竇娥被吞噬的豈止是青春與美麗?
五
竇娥冤雜劇,見於著錄的有:
天一閣本錄鬼簿
太和正音譜
元曲選目
曲海目
重訂曲海目
也是園書目
今樂考證
曲錄
其中天一閣本錄鬼簿作題目「湯風冒雪沒頭鬼」,正名「感天動地竇娥冤」,簡名竇娥冤。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均作正名「感天動地竇娥冤」,餘皆作簡名竇娥冤。
今存版本有:
脈望館古名家雜劇本(即陳與郊本):題目「後嫁婆婆忒心偏,守志烈女意自堅」;正名「湯風冒雪沒頭鬼,感天動地竇娥冤」。
酹江集本(即孟稱舜本):題目「秉鑒持衡廉訪法」;正名「感天動地竇娥冤」。
元曲選本(即臧晉叔本):題目「秉鑒持衡廉訪法」;正名「感天動地竇娥冤」。
本書校勘,以元曲選本為底本,參考了前輩時賢諸多校注整理本,如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王學奇主編元曲選校注本(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吳國欽校注關漢卿全集本(廣東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徐征等主編全元曲本(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等,其中尤以王季思先生全元戲曲本借鑒最多。比勘下來,脈望館古名家雜劇本與元曲選本其實出入不是很大,臧晉叔補充了一些曲詞,平心而論還是補寫得很得體的。故明人所編諸戲曲選集,此本流傳最為廣泛,影響也最大。對於臧晉叔的訂改,晚明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針鋒相對的看法,或頗有微詞甚至一筆抹煞者;或充分肯定臧氏為有功於戲史者。功過是非,各執一端,筆者贊同絕大多數研究者的意見,以為臧氏功大於過,基本上肯定他的改訂。美國學者奚如谷(Stephen West)認為:「這是一種極成功的改寫,他參考了很多城市商業戲院所刻的各種本子,去除了這種商業文化的價值觀念和語言標誌,而代之以自己理想的東西。他在改寫中遵從成體系、完整統一的原則,使劇本意思明確,語言一致。」又指出,改本「優點確實很多,但臧氏畢竟屈從於時代讀者觀念的壓力,把占統治地位文學作品中的理想觀念寫入了劇本」 。這樣的評價大體符合實際,可惜奚氏未弄懂元代士人的普遍社會心理,如我們在上文中揭示的那樣,元劇中宗族觀念、人倫思想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它不是臧氏「自己理想的東西」,而是原本中固有的東西。臧氏所處的時代,晚明人道主義思潮已蔚成風氣,說臧氏「把占統治地位文學作品中的理想觀念寫入了劇本」,似難說得通。另外,將臧氏的「改訂」說成是「改寫」,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按之諸本,不難見出臧氏是尊重原本的,總體上看他是謹行慎為的。其改訂是「善改」,而非「擅改」;是修訂潤飾,而非任情率意。在這個問題上,鄭尚憲先生的意見是富於啟發性的:「綜觀古今中外的戲劇舞臺,文學劇本一絲不變地被用作舞臺腳本的事情從未有過。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對於戲曲劇本,關鍵的問題不在於能否改動,而在於如何改動,即是否尊重了原作,是否保持了原作的基本面貌,是否對原作有所提高,使之更利於演出和流傳。假如是這樣的話,就應該予以肯定」 。不消說,鄭先生是肯定臧本的。其實奚如谷先生只要廓清了劇本中張揚傳統倫理道德理想的特殊社會文化背景,其意見也是可取的。關於臧本的是非功過,諸家意見尚多,恕不一一列舉。這裏只是想說明,我們選擇元曲選本作為底本的根據與理由。
本書校點,多從王季思全元戲曲本,但也有不少地方對比各家,審慎斟酌,擇善而從。如第二折的〔鬥蝦蟆〕曲,全元戲曲本與各家多有不同。因此曲是名曲,王靜安先生曾擊節讚嘆其佳,其斷句想是經再三揣摩的。其中「割捨的」以下諸句,全元戲曲作:
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
王靜安先生宋元戲曲考元劇之文章作:
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
這裏問題主要是,「停置」該如何理解?若訓為入殮,前者文義可通。然「幾件布帛收拾」卻沒頭沒腦,令人費解。案,「停置」又作「置停」,方言中為「置辦」之義。王學奇元曲選校注本注為「購買」,意甚近之。故王靜安先生的斷句可取。「收拾」屬下文,全曲就貫通了。
類似例子還有一些,茲舉一而反三可也。
為了避免繁瑣,本書不出校記,在比勘諸本,擇善而從時,在注釋中加以說明。依於元曲選本者,不再注出。凡異體字,如「吃」作「喫」,「早」作「蚤」等,一般採取徑改的辦法處理,不出注。個別字第一次出現時注明,重複出現時徑改。
注釋部分,我們盡可能在參考已有注本的基礎上,注出些新意,既顧及到語詞出處原委,又力求簡明扼要,力避繁瑣羅列,旁徵博引,務求貫通,以利於讀者閱讀。注書難,注元曲尤難,特別是市井俚詞俗語,切口方言,即便是根據上下文弄懂了意義,卻難徵於辭書文獻。筆者雖已盡力,疏漏與舛誤怕是在所難免,尚祈海內外讀者方家有以教我。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竇娥冤(二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竇娥冤(二版)
《竇娥冤》是元代戲曲家關漢卿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古代經典悲劇。內容敘述一善良女子竇娥的坎坷遭遇,她本與婆婆過著平穩的孀居生活,卻平地風波,遭市井惡棍張驢兒父子糾纏、陷害以致慘受冤獄刑戮。全劇曲詞渾樸自然,生動凝鍊,情節則跌宕起伏,反映了當時社會、吏制的腐敗黑暗。竇娥臨刑前因悲憤而發的三樁誓願,筆墨奇崛,創造全劇的高潮,也使竇娥含冤不屈的形象深植人心,撼動世人,奠定《竇娥冤》一劇光輝的藝術價值。本書校勘以王季思《全元戲曲》為本,同時比對各家的校注,審慎斟酌擇善而從。注釋則顧及語詞出處以及時代用語,務求簡明扼要,以利讀者閱讀。透過此校注本,讀者當能更加深入領會此劇精湛之處。
作者簡介:
作者關漢卿
元祁州(今河北省安國縣)伍仁村人。約生於金哀宗正大二年(一二二五)前後,卒於元成宗大德四年(一三○○)左右。因漢卿入元之後不屑仕進,長期廣泛接觸社會底層,故其雜劇創作題材多樣,往往能深刻反映當時社會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對民生疾苦和社會的不公平多有揭露,對下層婦女的社會地位和命運遭遇,尤為關注,並寄予深切的同情。此外,歷史人物、民間傳說等,也是關劇常見的題材。他的優秀雜劇作品《竇娥冤》、《救風塵》、《單刀會》等,均被後人改編成各種地方戲曲,廣泛流傳。
校注者王星琦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教學視導員,著名書法家、元曲大家。
作者序
引 言 王星琦
一
竇娥冤是元代偉大的戲曲作家關漢卿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古典悲劇中的典範之作。
關於關漢卿的生平事跡,相關的文獻記載零星有一些,然往往語焉不詳,甚至是互相齟齬。前輩與時賢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經考辨求索,反覆推論,可大體上勾勒出這位偉大戲劇家一生戲劇活動的基本情況。
元以後有關關漢卿生平事跡的記載,主要有以下七條:
一、元鍾嗣成錄鬼簿卷上:「關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已齋叟。」(曹楝亭刻本)
(案:天一閣刻本、說集本、孟稱舜刻本「尹」均作「戶」。)
二、熊自得析京志名宦傳:「...
一
竇娥冤是元代偉大的戲曲作家關漢卿的代表作,也是中國古典悲劇中的典範之作。
關於關漢卿的生平事跡,相關的文獻記載零星有一些,然往往語焉不詳,甚至是互相齟齬。前輩與時賢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經考辨求索,反覆推論,可大體上勾勒出這位偉大戲劇家一生戲劇活動的基本情況。
元以後有關關漢卿生平事跡的記載,主要有以下七條:
一、元鍾嗣成錄鬼簿卷上:「關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已齋叟。」(曹楝亭刻本)
(案:天一閣刻本、說集本、孟稱舜刻本「尹」均作「戶」。)
二、熊自得析京志名宦傳:「...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楔子一
第一折七
第二折二一
第三折三七
第四折四七
第一折七
第二折二一
第三折三七
第四折四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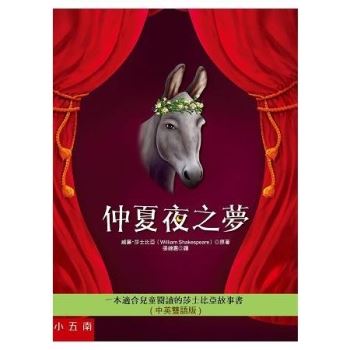




![114年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十四)113年度[教師甄試] 114年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十四)113年度[教師甄試]](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