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頻最新中篇小說作品集結
三段令人低迴不已的失序人生
不論是黑暗或苦難,只能與它共存
活著,就是與命運抗爭的存在方式
《鮫在水中央》由三篇獨立的中篇小說組成,揭露大時代下底層人物的無奈和絕望。面對生命的困頓荒誕,他們試圖與命運對抗,在黑暗中尋求稀微的光。
一個愛好文學、穿著體面的男人,他在山中的湖裡藏匿著一個巨大的祕密,罪行與愧疚隨著時間載沉載浮,他要如何救贖自己,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
――〈鮫在水中央〉
辭去教職轉拍電影的大學教授,輾轉遇見一名神祕女子,在電影的拍攝過程中,一樁殺人事件的真相漸漸浮出水面。
――〈天體之詩〉
他近似病態依賴臥病在床的母親,意外從她口中得知父親的身世之謎後,他在一座廢棄妖嬈的桃園裡,希冀尋獲失去的童年。
――〈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
【各界推薦】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石曉楓 專文導讀
作家 郝譽翔 陳柏言 陳栢青 導演 柯貞年 強力推薦
「在錯謬的現實裡,他們那麼卑微又那麼真誠地尋找存活的縫隙,正是在這些不甘被命運、時代擺布的張力裡,孫頻小說裡的人物不斷演繹著罪疚、願望、彌補、諒解、贖罪與寬宥。」
―― 石曉楓(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本書特色】
1.二○一九年茅盾文學獎新人獎孫頻新作
2.懸疑而張狂的情節──三個關於小人物、廢墟場景、殺人懸案、祕密與謊言的故事,解剖人性最終的善與惡。
3.失序人生底下的文學關懷──面對這些黑暗與罪行,在孫頻森冷、銳利的文字背後,是她對小人物的悲憫與關懷,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
4.值得探討的時代性──人與時代無法脫離,關於那些命運、體制的束縛,社會底層人物該如何安身立命,進而反思時代之於人們的存在意義。
【佳句摘錄】
後來的很多年裡我都不捨得告訴任何人關於這個湖的存在,彷彿這是一個只屬於我和這個湖之間的祕密。我一直記得我第一次跳進這湖水裡游來游去的感覺,像從乾燥陌生的生活裡擠進了一道潮濕的裂縫。
後來我一直相信這片湖就是世間留給我的一道縫隙。──〈鮫在水中央〉
因為時間,因為寂靜,這些祕密已經紛紛變老,已經長出了堅硬的盔甲和滿面的皺紋,卻還在這荒草裡抵禦著四季和流年、冬雪和烈日。──〈天體之詩〉
她面目模糊地躺在那裡,看上去如一條失去了年齡與性別的河,而他孤獨蕭索地等在河邊。她開口了:「我一直都想告訴你什麼叫盤底盛宴,就是你的盤子裡就剩下那麼一點吃的時候,無論那剩在盤子裡的是什麼,都將是你的盛宴,不管剩下的是一顆土豆、一片菜葉、一塊麵包、還是麵包屑。──〈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
作者簡介:
孫頻
1983 年生,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已出版小說集《不速之客》、《疼》、《鹽》、《裂》、《隱形的女人》、《三人成宴》、《松林夜宴圖》等。曾榮獲趙樹理文學獎、紫金.人民文學短篇小說佳獎、《鐘山》之星文學獎年度青年作家獎、百花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石曉楓 專文導讀
作家 郝譽翔 陳柏言 陳栢青 導演 柯貞年 強力推薦
痛並纏綿著—孫頻小說中的創傷與救贖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石曉楓
長期以來,中國當代小說家以王安憶、莫言、閻連科、余華、蘇童等較為臺灣讀者所熟知,而這批五○後、六○後作家確實也把握其經受大時代洗禮的寫作資源,持續活躍文壇且長期處於重要地位。然而近十年來,關於七○後、八○後作家作品的成熟度,也開始受到關注,較早成名的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人之外,近期廣受討論的尚有雙雪濤、胡遷等。而孫頻(一九八三— )在八○後創作行列裡,則是頗具個人風格的一位,前此在臺灣出版的作品僅有短篇小說集《不速之客》,這本《鮫在水中央》為其較新作品,由〈鮫在水中央〉、〈天體之詩〉、〈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三部中篇小說組成。之所以言其風格特殊,如作家所言,她不屬於「歪膩」婉約的創作氣質,展讀數頁,字裡行間迅即閃現出森冷的金屬光芒,廢墟與死亡/失蹤者相伴出現,營造出冷硬派的質地。〈鮫在水中央〉裡廢棄的鉛礦、湖底的屍體,〈天體之詩〉中的工廠廢墟與殺人疑案,乃至〈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裡的廢園老宅,被埋屍桃園中的人與狗、被隱瞞的死亡種種,充斥著詭魅的氛圍與一觸即發的張力。將推理、懸疑手法等融入嚴肅文學創作中,似乎是中國八○後創作特徵之一,孫頻小說的懸疑重點不在情節的推進,而更多取決於充滿畫面感的經營,浩大明月、銀脆花香、葳蕤春草等固然為常見之美好景致,但小說中出現更多的是因得人身餵養而有妖氣的魚兒,花朵開得又妖又香、桃子肥碩圓潤如吸了死人之血的豔異氣息,此中包藏了身世之謎與時間的祕密。而所謂時間的祕密,正是孫頻以懸疑為餌所欲展開的存在思辨,世間真幻如何洞悉?來自時間深處的幻象如何展現其意義?邊緣人物的困境又該如何尋求解脫?不妨以三篇中最見情感與功力的〈天體之詩〉為例,山西省交城縣卻波街為孫頻小說中常見的空間,前此的〈乩身〉、〈卻波街往事〉等,乃至本書另一篇〈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均多所演繹,顯示了家鄉小縣城與創作者血脈相連的意義。至於本篇主要的場景,可以對照七○後作家路內從長篇處女作《少年巴比倫》開始,一系列技校和工廠生活的寫作,這些工廠生活來到八○後雙雪濤(一九八三— )、班宇(一九八六— )以及孫頻筆下,便成了廢棄的場所、沒落的街道,他們更熱衷於演繹父輩下崗的故事。可以說,過去右派被批鬥的血淚史、文革十年的慘痛經歷,在此輩作家筆下,已漸漸轉成更前代的敘事背景,〈鮫在水中央〉裡固然有被劃為右派、被批鬥的范聽寒夫婦,〈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裡固然有被打成右派下鄉改造的宋之儀夫妻,但作家更熱衷著眼於一九九○年代中期,中國由計畫經濟轉入市場經濟,改制後國企工廠的衰落景象與底層工人的掙扎。在此波下崗潮中,有太多如梁海濤般以「買斷工齡」方式結束工人生涯者、有自辦廠子最終失敗如范柳亭的私營企業者,亦有諸多如李小雁般下海的個體戶,或如華建明、伍學斌般誓言死守工廠的老員工,這些在時代洪流中無法順利轉變或找到位置的邊緣人,便在時間夾縫中退無所據地存在著。〈天體之詩〉的敘事者「我」在大學講堂所拋出的質問是:「當宗教信仰不再,人類心靈麻木不仁,如何才能彌補這世界的裂痕。」然而這充滿表演意味的質問,必須等到在拍攝廢棄工廠過程中,遭逢了伍學斌、李小雁等下崗工人,才能產生參差的對照。李小雁的詩是生活的虛擬與表演,然而在殘敗的小鎮月光下,生命是塵埃,世界如幻象,荒謬苦難的現實有如不真實的夢,而夢境或許反而更能允諾最終的真實。〈天體之詩〉演繹了時代、命運與精神的種種失序,正因現實太難以逼視,「我」才需要藉由電影創造幻象,而真實或許正存在於李小雁所創造的詩與夢中。正是在這樣的立足點上,卑微的生命從而有了詩般的存在,關於電影/夢與真實的辯證也產生了詩般的哲思。時代的作用力與邊緣人的處境,是孫頻小說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中身世不明的宋書青,覺得自己是整個社會的一個幻覺;〈天體之詩〉中的車間主任伍學斌、李小雁,焦灼於小人物發聲的艱難;〈鮫在水中央〉裡的梁海濤則如懸絲木偶般在生活中掙扎,操縱他們的究竟是命運還是時代?在錯謬的現實裡,他們那麼卑微又那麼真誠地尋找存活的縫隙,那是讀詩安心、穿戴整齊做人,越是困頓便越是鄭重的體面;那是短暫一生也要自帶莊嚴感的堅持。正是在這些不甘被命運、時代擺布的張力裡,孫頻小說裡的人物不斷演繹著罪疚、願望、彌補、諒解、贖罪與寬宥。黑暗與歡樂苦苦地共長著,但是小人物還是要那麼用力地活著,痛並快樂著、纏綿著,所有種種「不過就是為了鎮壓那一場枯而又榮、榮而又枯的徒勞」,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小說家如冷兵器質地般文字背後的悲憫與關懷。
名人推薦: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石曉楓 專文導讀
作家 郝譽翔 陳柏言 陳栢青 導演 柯貞年 強力推薦
痛並纏綿著—孫頻小說中的創傷與救贖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石曉楓
長期以來,中國當代小說家以王安憶、莫言、閻連科、余華、蘇童等較為臺灣讀者所熟知,而這批五○後、六○後作家確實也把握其經受大時代洗禮的寫作資源,持續活躍文壇且長期處於重要地位。然而近十年來,關於七○後、八○後作家作品的成熟度,也開始受到關注,較早成名的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人之外,近期廣受討論的尚有雙雪濤、胡遷等。而孫頻(一九八三— )在...
作者序
世界上所有的道路孫頻
有時候想想,人生真的是奇妙而莫測,你永遠不知道你所走的道路的盡頭是什麼,甚至不知道下一個轉彎處會是什麼。可是也因此,我們這一生才像一個擺滿了鏡子的空間,才在一個虛虛實實的空間裡,有了無盡的轉折與夢境。那些鏡子裡與夢境裡的空間也許是永遠無法走到的,卻以一種神奇的力量誘惑著我們,同時也消解著人生的種種苦難與黑暗。
我想起自己十年前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一週便可寫完一個中篇,不假思索地寫,寫完也極少修改。現在我用三、四個月甚至半年來寫一個中篇,緩慢得像一只蝸牛。那時候總有人對我說,你寫得太快太多。現在又有人對我說,怎麼一年都沒看到你的小說。可是對我來說,這兩個階段都是對的。那時候一口氣寫很多小說,覺得快樂。現在慢慢吞吞、反反覆覆打磨和擦拭一些細節的時候,也覺得快樂,那種孤獨而自在的快樂,就像一個人在雪夜為自己唱起的聖誕歌,沒有人知道你為什麼快樂。寫作中那些長年累月的孤寂與枯燥都會在瞬間被這些快樂照亮和穿透。除了那些孤獨的快樂,也許每一個在這世上活過的人都會有一些小小的野心與小小的尊嚴,渴望一點存在感,渴望得到一點尊重,渴望人生的一點不虛妄。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所有的信念,除了對文學的熱愛,最重要的便是那種屬於文學的尊嚴感了吧。那就是,一個人願意付出他的全部去寫出好的文學作品。
《鮫在水中央》這篇小說中的山林背景其實並不是我所了解的,我只是為了寫這篇小說,特意進入過那些無人的深山老林。但是我明顯感覺到,在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我對這樣世外的山林或是桃園是充滿著感情的,包括對這虛構山林裡的一草一木、花鳥魚蟲。大約是在心底裡,我依然覺得在這樣徹底而巨大的孤寂中,無異於置之死地而後生,人會獲得另一種意義上的生命,另一條生還的道路。我寫一種與自己完全無關的生活,最初是出於對自己的挑戰,寫著寫著卻再一次把自己變成了主人公,再次把情感投入到每個人物身上,彷彿我自己就是那隱居在深山鉛礦裡半世飄零的男人。
雖然這只是一個虛構的文學人物,我卻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像他這樣的人其實並不少。從一個嶄新的、懷有各種夢想的年輕人,被時代一次一次地裹挾著往前走,雖然他一再抗爭,一再渴求能保全一點原初的生命,甚至幾十年不變地以一種牢固的穿衣方式在捍衛自己的那點尊嚴,哪怕在沒有第二個人的深山老林裡他都從沒有放棄過這種穿衣方式,是因為他明白,一旦放棄,他的精神就垮了,他的存在就會立刻化為虛妄。人與時代的關係是文學中永恆的主題之一,因為人無法脫離時代,卻終究要被新的時代所拋棄,時代的變幻與荒誕,時代對人的成全與戕害,造成了個體的命運與傷痛,而一個個體的傷痛在浩瀚的時間中只是一粒微塵,隨著親人的死去,最後連關於他的記憶都不復存在。所以我想寫出這些長河中的微塵們會為了人的尊嚴做怎樣的抗爭、怎樣的努力。
無論是小說中那駝背的老人,還是隱居在鉛礦裡的男人,或是那童心不泯的黑幫老大,他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發出一點屬於自己的微光,縱然道路不同,命運迥異,卻都有自己對活著的一種追問方式。我行走在那無人的深山裡的時候,覺得這個世界上只有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流溪澗、草木叢林,忽然就在心底對人世間產生了一種遠遠的溫情。我想我小說中的主人公們也是如此,在山林、在鄉野、在這些最偏僻的角落裡進行精神上的自救,也因此有了深山裡廢墟裡的唐詩宋詞。有了那首兇手們共聚之夜,在明月下吟出的「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也是在那樣幽靜的山林行走的時候,我感受到了一種奇特的寬容,對世事的寬容,對自己的寬容,就好像,一切的一切在那一重時空裡都變得不那麼重要了。所以也有了《鮫在水中央》裡的主人公們在知道真相的最後一瞬間裡選擇的寬容和遺忘。這種寬容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其實也是一種救贖。而無論是世外桃源裡近於老莊的超脫,無論是近似於宗教光芒的救贖,無論是以古典的書籍精神來修復自身的傳統儒家之路,都是對這個世界的不棄與和解,而這其實也是世間萬千凡人們的寫照吧。就是無論以什麼樣的方式,所有的人們在最後都會找到一條屬於自己到達彼岸的道路。而作為一個作家在寫作時的道路就是,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包括作者自己,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精神力量。
「鮫」可以理解為水妖、水怪,也可以理解為美麗詭異的人魚。願意從哪個角度來理解,也是世間道路之一種。
世界上所有的道路孫頻
有時候想想,人生真的是奇妙而莫測,你永遠不知道你所走的道路的盡頭是什麼,甚至不知道下一個轉彎處會是什麼。可是也因此,我們這一生才像一個擺滿了鏡子的空間,才在一個虛虛實實的空間裡,有了無盡的轉折與夢境。那些鏡子裡與夢境裡的空間也許是永遠無法走到的,卻以一種神奇的力量誘惑著我們,同時也消解著人生的種種苦難與黑暗。
我想起自己十年前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一週便可寫完一個中篇,不假思索地寫,寫完也極少修改。現在我用三、四個月甚至半年來寫一個中篇,緩慢得像一只蝸牛。那時候總有人對我說,...
目錄
作者序
導讀
鮫在水中央 1
天體之詩 111
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 227
作者序
導讀
鮫在水中央 1
天體之詩 111
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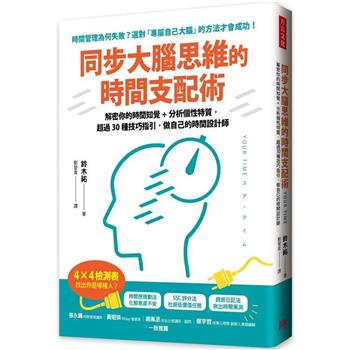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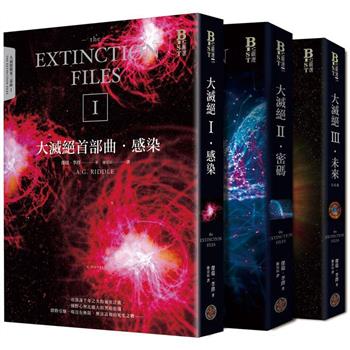










生活在底層的困頓以及內心的不安與掙扎,即便窮困潦倒,但對於做人最基本的渴望、懷抱夢想都是如此遙不可及與奢侈。平凡、安逸的日子是三位主人翁最渴望的生活,在越困苦難耐的時候越是想抓住一點什麼,才能讓自己看起來像個人;又或者懷抱著一絲絲希望、幻想,才有繼續活下去的勇氣。 被劃為右派批鬥或是國營企業突然解散(下崗),從原本較高的社會地位變成一無所有,甚至痛失至親至愛,絕望的心境在作者筆下刻劃得如此真切,隨著劇情的鋪陳,時而欣喜,時而悲慟。 「鮫在水中央」年幼時發現祕境,後來成為藏匿秘密之所在。雖然能置身事外,偶有情緒表露時會擔心被聽出端倪,但隨之而來的卻是若被發現,便可放下心中積壓已久的大石,揣撤不安的心情表現得非常貼切,人的話語不可能永遠無懈可擊,西裝筆挺的外表或許是想提醒自己莫忘初衷,又或者有極大的秘密被隱藏在表象之下? 「天體之詩」放下穩定的工作,轉而追求長久以來的夢想,在夢想追逐中遭遇挫折、散盡盤纏,所幸友人相助,終於找到看似不錯的拍攝題材,卻在鏡頭下發現事件的真相,公開與不公開,成了主角最後的仁慈。 「去往澳大利亞的水手」在男孩身上浮現出孩提時的影子,一個從不願意回想的過往,卻在母親瀕死前得知自己的身世,對於男孩產生了心理投射作用,不斷交疊出既視感,放手與否,變成自我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