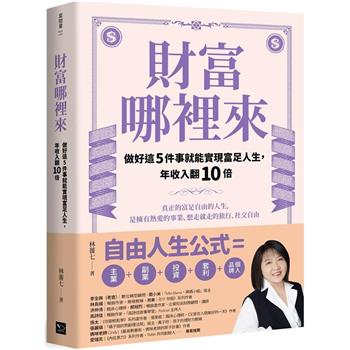自序
錢賓四師辭世已整整一年了,一年前我曾寫了兩篇悼念他的文字—〈猶記風吹水上鱗〉和〈一生為故國招魂〉—先後發表在《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上。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當時曾約我編一部紀念賓四師的專刊,因為賓四師晚年的著作幾乎全是由劉先生經手出版的。原則上我接受了這個任務,然而在實行時卻不得不對原來的計畫加以修改。這一年來,臺灣、香港、和大陸都刊出了不少紀念錢先生的文字,但是我旅居海外,無法進行有系統的收集工作,如果僅就眼前所見,彙集成冊,則不免遺漏過甚。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把我自己以前涉及錢先生的文字合為一編,作為個人紀念錢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獻禮。
這裏所收的文字多數是與錢先生直接相關的,但也有兩三篇僅間接涉及他的學術和思想,應略加說明。〈《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曾刊於臺北的《新史學》(一卷三期,一九九○年九月)和北京的《中國文化》第三期(一九九○年十二月)。此文特別指出錢先生〈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周官著作時代考〉的重大貢獻。前一文尤其曾震撼了當時的學術界,使人從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籠罩中澈底解放了出來。《周禮》決不是劉歆為了助王莽篡位而偽造的「建國大綱」,至此已無疑義,重翻舊案是徒勞無功的事。但是由於今天新一代的學人對清末民初的今古文經學之爭已隔得遠了,對於這個問題的意義恐怕不免也有些看不清了。最近我在《胡適的日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影印本,一九九○年,第十冊)中發現了一則紀事,值得引在這裏。《日記》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條說:
昨今兩日讀錢穆(賓四)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燕京學報》七)及顧頡剛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清華學報》六‧一)。
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他不信《新學偽經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駁之。
顧說一部分作於曾見錢譜之後,而墨守康有為、崔適之說,殊不可曉。
這是〈向歆年譜〉初問世時的反響,是有關現代中國學術史的第一手史料。我在寫關於《周禮》一文時,《胡適的日記》尚未出版,所以現在抄在這裏,以為補充。第二年(民國二十年)北京大學聘錢先生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其淵源即在於此。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原為悼念楊蓮生師而作,因其中有專節論及錢先生,所以也收在這裏。錢、楊兩先生同是我正式受業的老師,不意同年逝世,相去不過兩個多月。從此我竟成韓愈所謂「世無孔子,不在弟子之列」了,思之尤不勝其傷悼。〈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一篇長文雖未正面涉及錢先生,然而卻為他的學術和思想提供了一種時代的背景。錢先生在一九八八年為《國史新論》所寫的〈再版序〉上說:
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亦可謂為余治史之發蹤指示者,則皆當前維新派之意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增訂初版,一九八九年)
這正是我的〈激進與保守〉文中所討論的主題之一。原文是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五周年紀念講座第四講的紀錄(一九八八年),曾刊於《中文大學校刊》附刊十九。此次重印,文字略有改動。
本書所收各文中,最早發表的是〈《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繫年》互校記〉,時在一九五四年。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襲錢先生的著作的事實,是現代學術史上一重極有趣的公案。由於此文未經重印,故流傳不廣。此次收入集中,校勘和考證的部分一仍舊貫,但在行文方面則作了較大的修改。中共官方學術界曾間接反擊此文,採取變被告為原告的策略,反過來誣指《先秦諸子繫年》由抄襲而成,更為學術史添一趣聞。因此我又補寫了一篇跋文,供讀者參考。
〈錢穆與新儒家〉一文近四萬言,最近才寫成,是本書中最長的一篇,此文較去年所寫的兩篇悼念文字為詳實,因之也許可以更進一步說明錢先生的治學精神。但是為了避免引起無謂的爭端,我沒有讓它先在報章雜誌上露面。所以這是第一次刊布的文字。
本書〈附錄〉收入錢先生論學論文的書簡三通,這是從我手頭尚保存著的信中挑選出來的。我因為屢次遷居,師友書簡損失最多。錢先生給我的信也頗多遺失和殘闕,現存的幾十封信是我在錢先生逝世後,翻箱倒篋找到的。〈附錄〉第一、第二通寫於一九六○年,那時錢先生正在耶魯大學任客座教授。這兩封信都是對我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初稿的批評和討論。其時我治國史不過剛剛入門,這兩封信對我有振聾啟聵的震撼力。當時我的計畫是讀完學位後回到新亞去執教,所以主要精神是放在西方歷史和思想方面,如羅馬史、西方古代、中古政治思想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以及歷史哲學等都是我曾正式選修過的課程。我的心裏頗有些焦急,因為我實在騰不出太多的時間來專讀中國書,而中國古籍又是那樣的浩如煙海。我在給錢先生的信中不免透露了這一浮躁的心情。錢先生每以朱子「放寬程限,緊著工夫」的話來勉慰我,叫我不要心慌。這種訓誡真是對症下藥,使我終身受用無窮。錢先生又特別提醒我: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必須在源頭處著力,不能以斷代為限。這句話也是我終身不能忘記的,雖然我至今仍停留在「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階段。錢先生又一再告誡我不可追逐時尚,鬥奇炫博,走上華而不實的斜徑。我自己感覺非常幸運,在我步向學術旅程的關鍵時刻能夠得到這樣一位良師的當頭棒喝。限於才力,我的成績自然遠遠沒有達到錢先生當初對我的期待。但是我後來常常把錢先生的意思──其實也就是中國傳統的為學之方──輾轉說給向我問學的青年朋友們聽。我勉強做到了錢先生所說的「守先待後」。〈附錄〉中的第三封信是一九六六年寫的,那時我剛剛回到哈佛任教,胸中正醞釀著對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種新解釋,而以戴東原與章學誠的對照為其中心線索。因此我寫信向錢先生求教,現在發表出來的便是他的答書。這是我的《論戴震與章學誠》的一個遠源。我自己曾受到錢先生這幾封論學書簡的啟發和激勵,所以現在決定把它們公諸於世,與有志於治中國學術思想史者共享之,並略述其背景如上。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余英時序於美國普林斯頓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三版)的圖書 |
| |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三版) 出版日期:2021-02-19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4 |
Others |
$ 252 |
小說 |
$ 272 |
社會人文 |
$ 288 |
哲學 |
$ 304 |
中文書 |
$ 304 |
中國哲學 |
$ 304 |
Book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三版)
本書為紀念史學大師錢賓四先生逝世週年而作,但其意義並不僅在於感舊傷逝。作者企圖通過對錢先生的學術和思想的研究,勾劃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一個重要側影。錢先生論學具有極其鮮明的觀點,與中國現代學術界的一切流派都有顯著的異同,因此一方面和各流派都有所不合,另一面又和各流派都有很深的交涉。本書特別著重地分析了錢先生和「五四」主流派(以胡適為代表)、馬克思主義派(以郭沫若為代表)以及新儒家(以熊十力為代表)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作者簡介:
余英時
一九三○年生於天津,籍貫安徽潛山。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首屆畢業,哈佛大學史學博士。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曾任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和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曾獲國際多所大學的榮譽和名譽博士學位。二○○六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積人文終身成就獎」(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二○一四年榮獲「唐獎漢學獎」。著有中英文著作數十種。
作者序
自序
錢賓四師辭世已整整一年了,一年前我曾寫了兩篇悼念他的文字—〈猶記風吹水上鱗〉和〈一生為故國招魂〉—先後發表在《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上。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當時曾約我編一部紀念賓四師的專刊,因為賓四師晚年的著作幾乎全是由劉先生經手出版的。原則上我接受了這個任務,然而在實行時卻不得不對原來的計畫加以修改。這一年來,臺灣、香港、和大陸都刊出了不少紀念錢先生的文字,但是我旅居海外,無法進行有系統的收集工作,如果僅就眼前所見,彙集成冊,則不免遺漏過甚。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把我自己以前涉及錢先生的文字合...
錢賓四師辭世已整整一年了,一年前我曾寫了兩篇悼念他的文字—〈猶記風吹水上鱗〉和〈一生為故國招魂〉—先後發表在《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上。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當時曾約我編一部紀念賓四師的專刊,因為賓四師晚年的著作幾乎全是由劉先生經手出版的。原則上我接受了這個任務,然而在實行時卻不得不對原來的計畫加以修改。這一年來,臺灣、香港、和大陸都刊出了不少紀念錢先生的文字,但是我旅居海外,無法進行有系統的收集工作,如果僅就眼前所見,彙集成冊,則不免遺漏過甚。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把我自己以前涉及錢先生的文字合...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
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
錢穆與新儒家
《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繫年》互校記(附〈跋語〉)
《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金春峰《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序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香港中文大學廿五周年紀念講座第四講(一九八八年九月)
《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弁言
壽錢賓四師九十
附錄: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附原文)
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
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
錢穆與新儒家
《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繫年》互校記(附〈跋語〉)
《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金春峰《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序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香港中文大學廿五周年紀念講座第四講(一九八八年九月)
《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弁言
壽錢賓四師九十
附錄: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附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