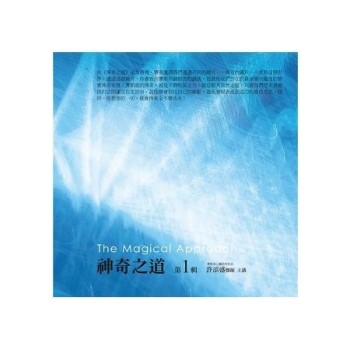本書藉由史上遺跡與藝術作品闡述文明發展的脈絡以及「真、善、美」的義理。書中論述起於史前時代,終於二十世紀,涵蓋上古、古典、中古與現代四大歷程,它顯示人類文明在超越求生圖存的層次(上古)之後,發覺永恆與絕對的文化價值體系(古典),然後陷入退縮、懷疑、否定的「見山不是山」階段(中古),再重新確認與發揚文明的終極意義(現代)。這個發展歷程在民間或世俗社會裡並不具體呈現,但在上層文化的傳承中則清晰可辨,這表示大眾文化的性質永遠是「上古的」,而精英文化的素質則追求「古典」與「現代」的至善精神。至善乃為「真」,它超越「善」與「美」的層次,故最佳的藝術品為超越美感境界,而具有善與真的意涵者。如此可知,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是史上藝術水準最高的表現,因其不僅具備精良的美術創作技巧,而且富有「究天人之際」的意境。至於「現代藝術」則是資質不足者面對當代價值混淆與社會發展危機時的迷情窘態。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歷史與圖像:文明發展軌跡的尋思(增訂三版)的圖書 |
 |
歷史與圖像─文明發展軌跡的尋思(增訂三版) 作者:王世宗 出版社: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1-2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48 |
二手中文書 |
$ 498 |
Books |
$ 498 |
Books |
$ 536 |
社會人文 |
$ 567 |
歷史 |
$ 598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歷史與圖像:文明發展軌跡的尋思(增訂三版)
內容簡介
目錄
自 序
第一章 文明的先兆
第二章 古代文明精神:兩河流域
第三章 古代文明精神:埃及
第四章 從古代到古典:希臘人文主義的興起
第五章 古典文明的傳播與轉變:希臘化時代
第六章 古典文明的傳播與轉變:羅馬帝國
第七章 神人之際:基督教信仰與中古的宇宙觀
第八章 神人之際:基督教信仰與中古的人生觀
第九章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觀點下的天人之際(一)
第十章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觀點下的天人之際(二)
第十一章 宗教改革:基督信仰與人間秩序的調整
第十二章 理性精神的發揚: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
第十三章 法國大革命與自由之權的追求
第十四章 愛國與崇道的矛盾:民族主義的發展及其危機
第十五章 新舊交替:工業革命與近代社會變遷
第十六章 希望與慾望:十九至二十世紀文化氣氛的轉變
第十七章 歷史的終結:現代文明危機及其啟示
參考書目
索 引
第一章 文明的先兆
第二章 古代文明精神:兩河流域
第三章 古代文明精神:埃及
第四章 從古代到古典:希臘人文主義的興起
第五章 古典文明的傳播與轉變:希臘化時代
第六章 古典文明的傳播與轉變:羅馬帝國
第七章 神人之際:基督教信仰與中古的宇宙觀
第八章 神人之際:基督教信仰與中古的人生觀
第九章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觀點下的天人之際(一)
第十章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觀點下的天人之際(二)
第十一章 宗教改革:基督信仰與人間秩序的調整
第十二章 理性精神的發揚: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
第十三章 法國大革命與自由之權的追求
第十四章 愛國與崇道的矛盾:民族主義的發展及其危機
第十五章 新舊交替:工業革命與近代社會變遷
第十六章 希望與慾望:十九至二十世紀文化氣氛的轉變
第十七章 歷史的終結:現代文明危機及其啟示
參考書目
索 引
序
序
這本書不是一部藝術史,也不是一部文化史,而是一部文明史。它探討各式圖像內含的歷史意涵及時代精神,藉以說明文明發展的痕跡與脈絡。
作者撰寫此書主要出於兩個理念,其一是以非文字的史蹟驗證吾人從文獻資料所見之文明歷史取向(參見拙著《古代文明的開展──文化絕對價值的尋求》與《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其二是從藝術創作的評論闡明柏拉圖所指出的「真、善、美」事理,而此二者實為一體,它們都在指示何為真理。
歷史本身即為不同時空的結合體,它充滿著不同的事物,變異是其尋常的現象,因此若歷史變遷並無其目的、而事物的價值無其常理,則歷史只是好古者或念舊者遊戲的墓園,它可能是知識的寶庫,卻也是迷惑求知者的快樂絕境。作者的主張至此已昭然若揭:歷史是文明發展的過程,而文明是真理的追求,雖然真相世人永不能確知。
我們可以否認這個道理,但我們永遠無法否定這個道理。若有人要說這只是一種想像,那他就必須思考一切以現實功效為準據所建立的觀點,有何者堪稱為真、為善、為美、而具有「義當如此」的力量?真正的功利主義者最後只證明「最大的利即是義」,但他們始終不能倡議「最大的義即是利」,因為若然則功利主義便不能以科學的地位立言,而且最大的義竟是無視於利,「義利兩全」之說非愚則誣,這證實「實際的」其實是「有限的」。所有實證主義者皆不能放棄道德詞彙的使用,道理亦類此。當專家強調其知識的權威性時,多不能同時承認其知識的侷限性,卻有延展其權威的傾向,而將「專家」轉化為「領袖」,這也說明務實者究竟不能圓滿,難怪競務虛榮者皆是務實之輩。
在知識而言,現代文化的是非顛倒或是非不明的亂象,是源於「科學掛帥」的結果。以科學為人類社會支配原則的錯誤不在於科學,而在於人。科學是有限的,而人的理想則為無限,科學乃為人而存在,不是人為科學而存在,以科學裁定人事誠可謂削足以適履。人文不是相對於科學,更不是反科學,而是包含科學,且超越科學,雖然如今在專業化體制之下人文學者多對科學所知不深,但人文學的本質是求「物理之上」而非「物理之外」的道理,故而人文學者不能輕視科學,科學家卻可以──正當地──忽視人文。然就現在實際的學術分工情況而論,人文學的知識量確實遠少於科學,在眾多的學門中僅文學、哲學、藝術、與史學屬於人文學,而其餘概屬科學,於是人文學僻處一隅似甚合理,何況現代人文學者的避世性甚強、且以所學合乎科學觀點為榮!歷史學探討一切人事,本應為人文學之首,但它今日卻淪為人文學之末,此即因學史者大多自許「科學化」而僅習事不問道。可知現代科學掛帥是「民主的」,而推翻民主既是無望的也是自私的,故傳道者應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持勇氣與「忍受人間錯誤」的承擔精神。
求知應即求道,而道乃是貫通一切事物之理,故求知者不應在知識領域上有所偏執。然這不意謂所有事物皆為同等重要,事有輕重緩急,道有高低層次,求知者乃「以有涯逐無涯」,須知「質不是量的累積」,方不致玩物喪志,此即是柏拉圖富有文才卻瞧不起詩人的緣故。今日的學者不喜價值判斷,卻不能不行價值判斷或不知不覺中一再為之,他們總以「客觀」的方式表達其「主觀」的意見,而自以為所說為「公論」,殊不知公論不是公眾的主張,而是有識者的卓見,這對一般人而言就是個人的價值觀。
藝術的定義問題便是反映此種矛盾現象的一個實例。若以「價值中立」的「科學式」觀點立論,則所謂藝術乃是一切人為的創作(非人為的創作如山水草木便非藝術品),這是所有不談超越性觀念的文藝學者必然的說法,也就是「客觀的學術論述」;然而一般藝術史學者或藝評家皆不可能以這個準則(廣泛而公平地)討論藝術作品,一方面是因為在此定義下藝術品變成多至無法處理,另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好壞美醜可言的藝術既不值得也不必加以評述。於是當今藝術研究的怪象是,學者經常選擇其心中所認定的美好(上乘)作品為討論對象,卻不能或不願說明這些作品所以為美的絕對道理,或是無法以一貫的審美標準討論所有的作品。任何一部「藝術史」皆以史上少數的傑作為題材,而非均衡地介紹各式藝術品,此種作法其實正是「文明史」而非「文化史」的取向,但事實上現今大部分人文學者皆不接受主張絕對價值的文明觀,這個衝突性──因當事者自覺不深故不可謂為緊張性──顯示「美」的源頭為「真」,此理可以被忽視,但不能被否定,而不從真理評論藝術者均將陷於形式與技法的分析,永不能為個人的審美觀自圓其說。美感確是因人而異,但這是因為各人資質與素養高低不同,而不是表示美無恆常的標準或美感為後天經驗所造就,此義即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總之,藝術若無絕對的優劣,則藝術品就是一切的東西,而藝術學者就是博物家,於是品味一詞理當消滅;若此說為不可,則知藝術實為啟示世人真理存在之理的最普遍奇蹟,如此亦可知,美雖為層次不高的事理,卻是求道者絕不能忽略或無能力評析之事。
這本書的寫作未曾得到外界的支持,它的出版也不為謀取世人的肯定,淑世固然是作者的心願,但是非對錯的申明是我更強的意念。成功不是志士仁人的命運,但挫敗也不是他的習性,在絕對的事理之前君子並無勇氣夠與不夠的問題,他只是忘記害怕和自己的存在,然後才知「知其不可為而為」原不是情感、不是決心、不是能力、不是格調,而是義務。此書不為鼓勵或安慰人心而問世,它是知識的探索和作者盡己的呈現,但願在知行合一的精神中讀者得到他的生命方向和勇往的力量。
|